麻省理工周记(230708)
AI+domain knowledge,可以想想怎么利用这个工具颠覆自己学科的既有认知甚至是研究框架。纯转码是没有意义的,转了也可能很快就会被替代掉。
刚过去的周二是last day of class,PhD office仿佛一下子就被清空了,所有人瞬间各奔东西。周一的时候去校门口的大草坪蹭饭,惊讶的发现竟然只是一个MIT的课程 2.00b Toy Product Design 的final presentation,搞的相当隆重。整个空间改造成了一个直播舞台+游乐场,感叹整个课程的sponser充足的经费。
最靠近穹顶的一小片区域展出了一学期以来学生们的玩具设计的作业,五花八门,说实话我除了拍照之外,一个都没有看懂这些玩具怎么玩的,可能除了那个丢环的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之外,其他的我甚至不觉得是儿童玩具。。。
 在稍微外侧的地方则布置了游乐场设施,两个充气滑梯,甚至还有若干个杂耍的表演。两侧则布置了免费食物区,有各种burger,热狗,薯条,炸鸡块,饼,还有冰淇淋,零食等等。
在稍微外侧的地方则布置了游乐场设施,两个充气滑梯,甚至还有若干个杂耍的表演。两侧则布置了免费食物区,有各种burger,热狗,薯条,炸鸡块,饼,还有冰淇淋,零食等等。
再往外则是一个观众席和直播舞台,每一组课程作业的学生会轮番上台表演,每组presentation的时间限制在2分钟,介绍自己这学期所设计的玩具。看得出来,每一组选手都发挥了很多想象力,而且虽说是presentation,但其实每组都演了一个小品,把自己的玩具融入了实际的生活中。当然虽然有这些形式上、包装上的优点,但指望他们搞出来什么好东西,那我觉得真的是异想天开了。玩具设计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2C的产品设计,或许外界对于MIT的天才学生的期望过高,或许也只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总之这些sponser的钱,可能也就图个乐。
 btw,说到炸鸡,上周还特意去了KFC,炸鸡的分量是真足,不过烤的有点老,口感欠佳,味道我觉得跟国内比还是差点,也难怪在炸鸡内卷的美国,肯德基老爷爷基本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次有机会去别的网红炸鸡店再比较一下。
btw,说到炸鸡,上周还特意去了KFC,炸鸡的分量是真足,不过烤的有点老,口感欠佳,味道我觉得跟国内比还是差点,也难怪在炸鸡内卷的美国,肯德基老爷爷基本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次有机会去别的网红炸鸡店再比较一下。

一晃时间飞快,下周学校举办完毕业典礼,暑假就算正式开始了。
转眼间一届的同学就各自四散开去,由于以后没有像之前research design之类的公共课程,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将变得很短暂。类似的,在每学期上的一些课程中遇到的朋友,也随着课程的结束而不再有很多的联系,人生就是这样,迎来送往,能保持长期联系的好友总是不多的。随着年岁的愈发增长,也更有感触。
最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收集Canvas上残留的各个课程的相关学习资料,比如Advanced Computer Vision的文件里有一整本书的教材,虽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版本,但也近乎一个完整的校对版本。依稀记得自己在开学初的时候还在piazza上提了几个修改建议获得了采纳。然后随着前两天的打分,第一个学年的成绩单也算交了。虽然说实话课程给分还是挺松的,不过上学期的AI那门课,以及这学期的CV,入门ML的课程强度还是并不水,大量的 Problem Set 还是很容易让人做的头皮发麻。外加前前后后一共参加了6次考试,也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过关。考虑到自己打算在明年春季学期把 General Exam 给考了,目测要缓缓,甚至不上这类hardcore的课程了。
 左: Canvas 上的课程教材资料收集; 右: 第一学年成绩单在这之前我突然想到上周本该讲的内容忘记了,补充一下,那便是最后一节C51的课,是关于ethical problem的。感兴趣倒不是这个topic,而是课程上提了好几个经典的例子,回顾和记录一下,算是对相关知识点的查漏补缺了。
左: Canvas 上的课程教材资料收集; 右: 第一学年成绩单在这之前我突然想到上周本该讲的内容忘记了,补充一下,那便是最后一节C51的课,是关于ethical problem的。感兴趣倒不是这个topic,而是课程上提了好几个经典的例子,回顾和记录一下,算是对相关知识点的查漏补缺了。
几个关于历史上关于道德人伦实验的事件
1947 Nuremberg Code (纽伦堡法典)这是一项由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和规定的人体试验时必须遵守的10项标准。注意这和纳粹在30年代发布的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不是一回事。
1950s Thalidomide (反应停事件)这个比较长的单词的医学学名是沙利度胺,别名叫反应停。它是一种供孕妇服用的止吐药。该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多个国家被孕妇使用,最终导致全球一万多名新生儿先天畸形(英文版的link里有图片)
1963 Milgram Experiment (米尔格伦实验)这个好像老高的视频里有讲过。该实验又称为权利服从实验,就是对于权力的服从导致个体即使做了很罪恶的事,也会毫无知觉。最早是由Yale开始做的,后来Stanford搞得更多。说实话这实验挺变态的,让被测试人员去按下按钮去“点击”隔壁房间的“学生”,在绝对的威权命令下,施暴者甚至可以在施暴的过程中笑出声来。不过我记得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按下按钮。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1972 Tuskegee (塔斯基吉梅毒試驗)这个真没听过,是一项由美国CDC在1932年至1972在Alabama开展的一项梅毒治疗实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美國公共衛生局性病部門與塔斯基吉大學(當地歷史悠久之黑人大學)在1932年至1972年間於阿拉巴馬州进行的合作,该合作实验對近399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及201名健康非洲裔男性進行了一系列人体试验[1]。這些實驗參與者皆為生活貧困的阿拉巴馬州梅肯縣佃農。該實驗以提供免费醫療、餐點、喪葬保險等福利来吸引居民參與實驗,也以此目的募集基金。但在經濟大蕭條導致經費補助中斷後,參與者將不再有機會接受任何醫學治療,但是即便如此,研究者仍在未告知參與者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實驗。自始至終,研究者都不曾對罹患梅毒的參與者告知罹患梅毒的實情(而是宣稱患者接受的治療是為了醫治敗血症),也從不曾施予參與者任何有效的治療方式。"
后面的还提到了几个知识点:
Spectrum 10K: 一项在英国发起的关于研究1一万名自闭症患者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宣称为了更好地给予这些患者治疗,但这个项目一经发布就充满争议,人们对于这个研究的leader从头到脚充满了不信任,尤其是对于这些患者的隐私保护充满疑虑。所以最终在一片质疑的声音中项目在21年9月27日被暂停。Google "Project Nightingale" (谷歌的南丁格尔项目): 说白了就是google因为收集了数百万患者的详细健康信息而被调查。hmmm。。。国内貌似也有不少大厂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吧PS:今天去了瓦尔登湖。整个小池塘还挺热闹的,居然小沙滩上挤满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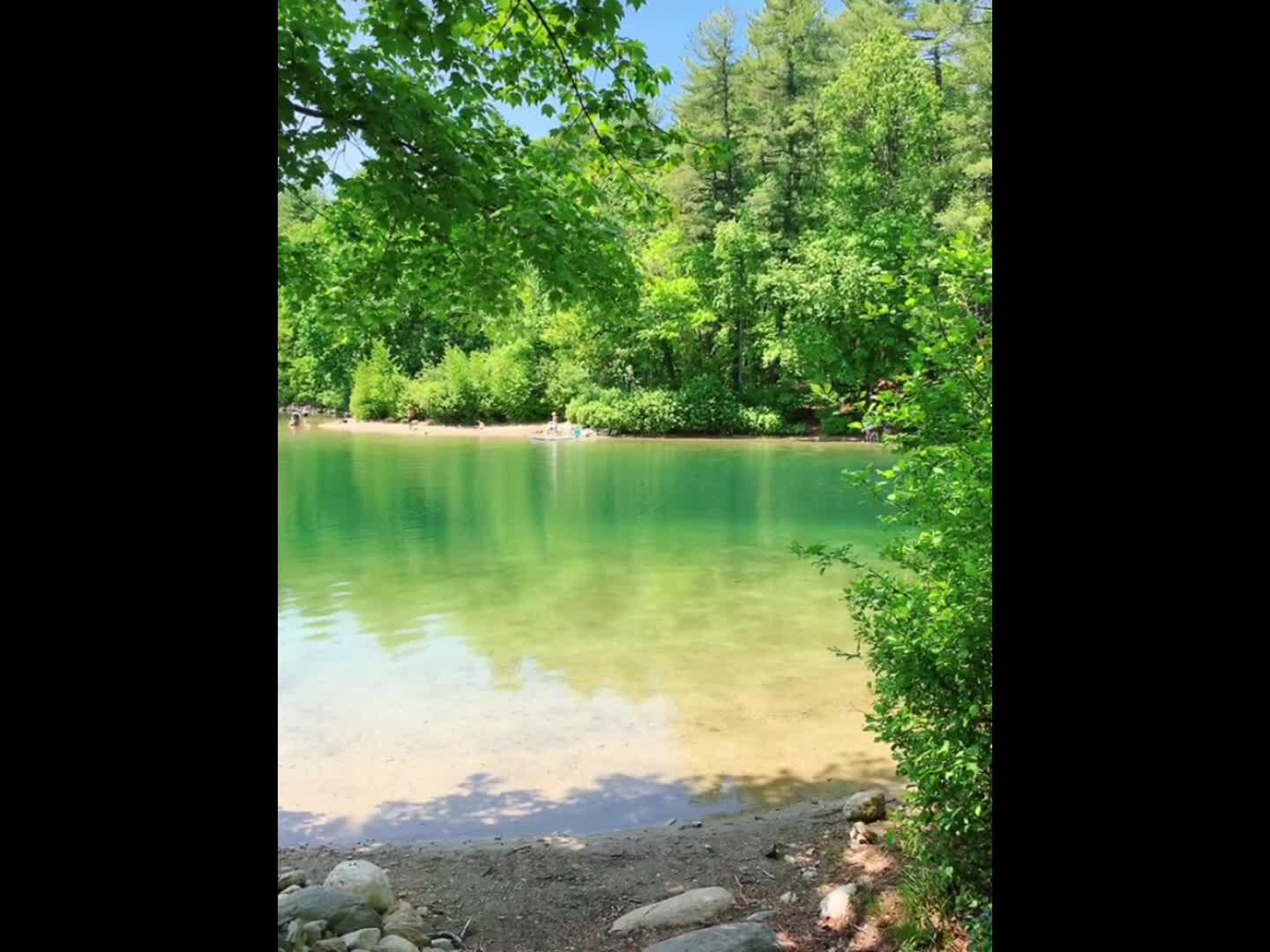 https://www.zhihu.com/video/1646051580183814144
https://www.zhihu.com/video/1646051580183814144
这周的毕业典礼因为天气太热了,也没有打算去蹭票。
进入六月之后,就算正式进入了Summer RA的阶段了。其实自己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很了解自己的所谓“全奖”是怎么一回事,也是这阵子开始慢慢有点搞清楚了。至少DUSP的情况目前来说是这样,如果是Department Funding的PhD的话,从去年开始给5年的package,这个package包含了第一年的fellowship,和四年通过RA+TA换得的学费减免和工资。
但这里的“年”指的是学年,也就是从当年的9月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所以就是cover9个月的时间。所以另外会有四个暑假(如果5年能毕业的话),这四个暑假据目前了解的话,是可以两个暑假RA,一个fieldwork,还有个暑假好像不用干什么。具体来说在暑假开始前,小秘会发布一个list,里面罗列了各个老师准备开展的暑假的课题,然后这些department funding的PhD可以报名参加。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些列表里面的project,几本都是各个导师对照自己学生事先确认会干活之后一个萝卜一个坑设置好的。至于参加的程度如何,个人时间的自由度而言,可否远程等等,就是跟PI商量着来的。在小蜜的官方通知里我明确看到了每周工作时间是20个小时,在一个相对轻松的范畴之内。另外package里面规定每个人要干5个TA+3个RA,普遍的观点来看TA是比较花时间和精力的,而且对于产paper没有什么帮助。或许是一方面系里面比较缺TA,或许也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每个人以后要投身教学行业,总之,我们系这个package算是TA要求比较多的。
 一大溜的Summer RA project list和summer project类似,下学年两个学期的可以TA的课程列表也由系里面发给了我们,让大家自由选择,然后跟老师联系之后安排见面,也算是一个双选会。然后也会有一个长长的课程列表,伴有课程介绍,让大家如果对TA或者RA感兴趣的话就进行选择。不过说实话当我看到list的时候,我发现可以选择的课程并不多,毕竟自己不是个文科生,让我去TA Gateway这种真的是要命了。顺带一提,在我离开MCP的这几年里据说之前有Gateway II的课,今年开始好像内部投票取消了。目测我也就TA一下GIS、QR这类了,毕竟我算是是UIS方向的。
一大溜的Summer RA project list和summer project类似,下学年两个学期的可以TA的课程列表也由系里面发给了我们,让大家自由选择,然后跟老师联系之后安排见面,也算是一个双选会。然后也会有一个长长的课程列表,伴有课程介绍,让大家如果对TA或者RA感兴趣的话就进行选择。不过说实话当我看到list的时候,我发现可以选择的课程并不多,毕竟自己不是个文科生,让我去TA Gateway这种真的是要命了。顺带一提,在我离开MCP的这几年里据说之前有Gateway II的课,今年开始好像内部投票取消了。目测我也就TA一下GIS、QR这类了,毕竟我算是是UIS方向的。
 well,这些课的TA。。。顺带一提,昨天从一个本科高材生了解到,他们的学费有75%是由学校负担的,据说本科生里面给这个待遇(need blind)的比较少,我们还是算比较大方的学校了。今天和一个同学聊,他的funding明年可能要没了,自己在打算non-resident的方式来继续学业,听起来也挺棘手的。总而言之,funding这事儿如果不注意也会有麻烦的地方,一旦没funding了也会挺不安的感觉。看来明年要加把劲多多注意了。不过个人感觉是,这一切的基石都在于paper,没有产出没有发言权,不搞事情,就会把自己搞死,奈何整个世界在卷。。。
well,这些课的TA。。。顺带一提,昨天从一个本科高材生了解到,他们的学费有75%是由学校负担的,据说本科生里面给这个待遇(need blind)的比较少,我们还是算比较大方的学校了。今天和一个同学聊,他的funding明年可能要没了,自己在打算non-resident的方式来继续学业,听起来也挺棘手的。总而言之,funding这事儿如果不注意也会有麻烦的地方,一旦没funding了也会挺不安的感觉。看来明年要加把劲多多注意了。不过个人感觉是,这一切的基石都在于paper,没有产出没有发言权,不搞事情,就会把自己搞死,奈何整个世界在卷。。。
PS: 封面是province town,俗称彩虹小镇,周一去了一趟Cape Cod,路上直接堵死了。。。太折腾了,彩虹小镇,万万没想道时隔9年,自己居然又来了这地方。
 下周去纽约参加好友的婚礼,估计会停更一周。
下周去纽约参加好友的婚礼,估计会停更一周。
上周开车去了纽约参加哥们儿的婚礼,导致一整个周末都在外面浪,而且从波士顿开往纽约(实际是哈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的漫长车程让我不得不停更一周。我哥们儿是个中国人,他的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他们计划在美国和国内各举办一场婚礼。所以我参加的这一场自然是西式婚礼,而且自己竟然以伴郎的身份参加,,而且还是比较传统的东正教的教堂婚礼,还真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体验。正好这里稍微文字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Day 1
首先是伴郎的衣服要提前小半年去尺寸测量,以及预定,以便婚礼前两天自取。所以第一天到纽约的日程是去取衣服。然而老美这边的裁缝店有时候挺离谱,自取的时候经常会拿出并不合身的西装西裤。比如我的那套西装的袖子就太长了,只好让店里的员工赶紧修剪,第二天再去取。当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单身party,本来的计划有两个娱乐活动,但后来因为时间赶不及,只完成了一个活动。然而这个活动居然是axe throwing。。。没错,就是挺暴力的扔斧子 游戏,其实和一般的扔飞镖,射箭馆差不多,只不过投掷物很夸张的改成了沉甸甸的斧子,导致参加娱乐的人甚至在进入游玩的时候都需要签一个免责声明。
 扔斧子,说实话一开始自己都不敢站在同伴的正后方Day 2
扔斧子,说实话一开始自己都不敢站在同伴的正后方Day 2
第二天参加了新郎新娘举办的一个瑜伽课,以及下午进行的彩排。rehearsal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安排了对方一个身高180+的伴娘。。。而且她还跟我说 I'm gonna on high heels tomorrow...事实上当天自己187的身高被完全压制。。。经过了第二天的彩排,才知道其实伴郎在婚礼中的工作主要是站桩。因为自己是groomsman不是bestman,我们一共有1个bestman和5位groomsman。Bestman有递婚戒的工作,而剩余的groomsman只需要在仪式的过程中全程站在后面即可。。。
 Day 3
Day 3
早上整个婚礼开始于酒店,其实和国内的接亲有点像,新郎与新娘需要搞一个外拍,这个过程叫“First Look”,其实就是新郎第一眼见到新娘,然后有个跟拍摄影师会给他俩拍照。这之后便前往教堂,和国内的婚庆公司一开始的要求差不多,新郎和我们在教堂的地下室候着,待宾客把堂内坐的满满当当之后,由女方的父亲搀着新娘缓缓步入。这一过程中,教堂内还有个阿卡贝拉的合唱团在侧旁唱一些充满仪式感的歌曲。
然后我们和新郎才从地下室走出来,来到教堂正中。这之后对我来说便开始了大约半小时-45分钟的一字排开站桩。新婚二人携手并排背对观众,面向一位身着大白袍的神父,及其身后的十字架。整个仪式基本都是由这位白发苍苍的神父主持。他开始不断的吟唱不知道是不是圣经的经文,然后让夫妻双方立下誓言,这一过程相当复杂:首先吟唱的经文很长,他并不是全文背诵,而是照着一本书在念,但速度奇快,有点像钢琴家弹钢琴的看乐谱的那种感觉;其次仪式中还出现了多个环节与道具,比如夫妻双方除了致誓词和带戒指之外,还要跟着神父逆时针绕的小台子三圈、手持蜡烛、头戴皇冠、喝酒(不是交杯酒)等等。整个过程庄重而肃穆,可以面带微笑,但记得有一个要求是不允许在教堂内鼓掌。
结束了教堂婚礼之后,晚上的婚宴却是另一种景象:狂欢,各种跳舞,以及穿插双方父母亲朋的致辞。
总体上来说,整个婚礼的过程和国内的婚庆公司的仪式有点类似,但具体过程和细节也很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女方是东正教的缘故,仪式流程上复杂了许多,但氛围还是不错的。私下里朋友之间总说,婚礼其实是办给父母,亲朋看的,实际上这么一顿折腾下来,我觉得也有办给自己的成分,毕竟这么折腾的一天,纵使再怎么记忆力衰退,都会在脑海中刻下一抹深刻的褶皱,这就是两个人的羁绊。
 站桩站的差点腰椎间盘突出。。。
站桩站的差点腰椎间盘突出。。。
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现自己的知乎人数总算涨到超过了1万了。。。不容易,就慢慢涨吧。。。
下周回国,这篇是走之前写的最后一篇。说来也惭愧,深感暑假偷懒偷的大发了,导致很多的计划都没有完成:
1)First Year Paper的修改没有完成,这是一篇review的文章,核心内容是分析street attributes,这周刚把30篇level 1 的paper又给仔细看了一遍,把他们得出的核心的内容整理了一遍,然后接下来回国可以就着这些整理出来的结论写点内容了。写完到时候看国内是否能远程连GPT,不能的话就回来润色。另外之前手贱把abstract投了出去,然后ACSP给了宣讲,which is a waste of time,但考虑到800刀的 travel grant 羊毛以及地点在迈阿密,还是打算去玩一圈吧,毕竟10年前的迈阿密之行被回国找工作面试给搅黄了,佛州的阳光还没有去沐浴过。
2)第二个没完成的工作是一个scholar的申请。内容是关于AI/ML的,要写一个proposal,也是我自己不擅长的,这两天又开始翻看一些经典著作,然而发现看书没有看paper效率高,自己最近看来看去觉得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William Whyte的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比其他的大部头的书有意思多了。Kevin Lynch的 good city form虽然以前在自己的书单里,但这次打开再看的时候感觉太tm像学科基础教材了,看了两眼又合上了。另外最近还看到一篇奇葩paper: Alfonzo, Mariela A. "To walk or not to walk? The hierarchy of walking needs."Environment and behavior37.6 (2005): 808-836. Google Scholar上居然有779的citation,估计很多的paper都需要引用一下他这总结出来的point,亮瞎了我的双眼,作者甚至也没有从事教职工作。水到一定的程度了,通篇文章无非就是引经据典的介绍了一下walk的五个需求层次,这甚至连整个框架都是照搬马斯洛,概括来说,他们分别是 feasibility -> accessibility -> safety -> comfort -> pleasurbility。。。hmmm,说实话自己看那么多street view analysis相关的文章就已经快无聊疯了,倘若让自己把人生浪费在总结这么sb的内容上,那简直可以去死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人材料的整理,也是无比繁琐。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一直没有弄好,那就是cv课的final project,我在课里面把之前计算的safety score重新搞了一遍。简单来说,就是如何把pairwise labeling的结果处理成评分是有不同的算法的,在Place Pulse1.0里面,采用了Q-score的方法,而到了Place Pulse2.0的时候,作者采用了微软研发的Trueskill算法,两者的算法有一定的不同,我会把GPT的解释丢在文末。总而言之,在照片排序这个要求下,个人觉得Trueskill的方法更合理一些。然而问题在于Place Pulse2.0的数据集的点击量依然不够,他们指出要想计算出合理的trueskill,每张照片至少要被比较24~36次,而2.0的数据集大概低于5次。于是他们作者搞了个trick,train了自动比较的模型,来提高每张图片的被比较次数,最后得出了trueskill的分数(Abhimanyu Dubey, Nikhil Naik, Devi Parikh, Ramesh Raskar, and Ce ?sar A. Hidalgo. Deep learning the city: Quan- tifying urban perception at a global scale)
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在计算安全感评分模型的时候,虽然用了2.0的数据集,但是沿用了原来的Q-score的方案进行计算,有点遗憾的是可能这样没有被强化比较过的数据集是有信息丢失和排序不准的问题的。(Zhang, Fan, et al. "Measuring human perceptions of a large-scale urban region using machine learning."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80 (2018): 148-160.)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原先的模型采用了高低两端的方案来进行binary svm的训练的原因。
于是采用了2.0的trueskill分数之后,我开始了一通操作,用了6种不同的网络,评分上还试验了直接接一个NN来打分,其实只要把loss function改成MSE就行了。话说我有个哥们儿他在面试一个工程师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归和分类的区别在哪里,当时我也不太能get到,现在觉得这么简单都答不出来,确实太说不过去了。

 【 GPT关于两种算法的解释】
【 GPT关于两种算法的解释】
Q Score:Q Score is a measurement developed by Marketing Evaluations, Inc. to evaluate the popularity and marketability of brands, celebrities, athletes, and other public figures.It primarily focuses on measuring a person's familiarity and appeal within a specific target audience.Q Score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field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to gauge the potential success of endorsements and brand partnerships.It considers factors such as awareness, likability, and appeal, and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a person's overall "Q Score."TrueSkill:TrueSkill is a rating system developed by Microsoft Research for assessing the skill level of players in multiplayer games or sports.It is based on Bayesian inference and statistical modeling and aims to estimate a player's skill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matches.TrueSkill takes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outcome of the match, the skill levels of opponents, and th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each player's rating.I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skill and to facilitate matchmaking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这周经历了奔波的行程终于回国了。之前据说中美之间要恢复更多的航线的磋商始终没有进展,从而导致了机票价格始终居高不下。最后在没有特别优惠的行情下,最后选择了一个“长达三天”的回国路线:把目的地从上海改成了香港,然后到香港休息一晚再买张机票回上海的方案。
值得一题的是,在这段冗长的回国旅途中,需要先从波士顿飞伊斯坦布尔中转,然后再飞香港。在土航鸡贼的策略下,似乎去ist转机的逗留时间一般都很长。不知道别的航班如何,总之我的航班中转时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h+。伊斯坦布尔的机场宣传语也挺有意思的 -- "Welcome to the meeting point of the world"。 整个机场的航班排的满满当当,我自己的航班起飞时间安排在了2:25AM,能把航班从凌晨1点到早上天亮每个小时都安排满的情况也是很少见了。
 第一段BOS-IST的行程有9个半小时,第二段IST到HKG则有10个半小时,造成行程如此冗长的原因,或许也有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至少从航行图上来看,很明显航班都绕行了,而这个伊斯坦布尔就扼守在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
第一段BOS-IST的行程有9个半小时,第二段IST到HKG则有10个半小时,造成行程如此冗长的原因,或许也有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至少从航行图上来看,很明显航班都绕行了,而这个伊斯坦布尔就扼守在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
 回国后明显感觉有点不适应炎热的天气以及拥挤的人群。Boston市区的人口才80万,Cambridge也只有60万,而国内的城市的一个区可能就要达到上百万。昨天和朋友去五角场合生汇吃了哥老官,整个商场感觉中央空调坏了,形成了一种在桑拿房吃火锅的独特感受。尽管如此,排队吃火锅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一行人大约也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吃到了火锅。
回国后明显感觉有点不适应炎热的天气以及拥挤的人群。Boston市区的人口才80万,Cambridge也只有60万,而国内的城市的一个区可能就要达到上百万。昨天和朋友去五角场合生汇吃了哥老官,整个商场感觉中央空调坏了,形成了一种在桑拿房吃火锅的独特感受。尽管如此,排队吃火锅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一行人大约也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吃到了火锅。
早上试了一下学校的VPN,虽然相当之卡,但是好歹能连接回自己办公室的服务器、学校的super cloud、以及一些常用的生存工具,比如GPT还算是顺利。希望下周把朋友见完后可以抽时间写点东西。把proposal啥的搞完。
另外和几位老熟人聊的时候说自己拍点视频记录和分享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当网红自己没什么兴趣,但是拍点东西po到B站播放一下啥的,其实也不错,毕竟是一种记录自己这么长一段时间生活的一种记录,比起把这些闲暇时间投入到一些无聊的刷手机的事情上会好很多(其实最近看了一眼自己的screen time,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直线上升,深表担忧)。可能相应的自己会搞个insta 360之类的,方便记录。
本以为这两周回国没啥可记录的,还想着写一些啥水一周,结果这可能是目前最特别的一段经历了。
是的,我前天住进了中山医院,昨天做了一个手术。。。
 故事的起因是两年前的某日,自己偶然发现左侧脸颊上摸起来有个硬块,当时摸了半天觉得这个硬块超级硬,心想莫不是长了肿瘤吧,而且还是在脸上。于是没过多久便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是的我必须点名加粗拉黑他。口腔科门诊医生听了我的描述,然后摸了摸肿块的地方,跟我说这是我的颌骨,他说这是我的颌骨凸出来了。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见我不信,他开始强行给我洗脑——“你是不是最近经常用左侧牙齿咀嚼?”,然后我居然乖乖的自己给这样的一个假设找理由——“好像有可能啊,我前一阵右侧臼齿补了个大窟窿嵌体,导致我可能习惯性的避免用右侧吃饭”。于是乎,这之后的谈话就基于这样一个无厘头的假设之下展开了,随机而来的治疗方案也新鲜出炉:不用治,以后吃饭多用右边吃。去年买了个表。。。
故事的起因是两年前的某日,自己偶然发现左侧脸颊上摸起来有个硬块,当时摸了半天觉得这个硬块超级硬,心想莫不是长了肿瘤吧,而且还是在脸上。于是没过多久便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是的我必须点名加粗拉黑他。口腔科门诊医生听了我的描述,然后摸了摸肿块的地方,跟我说这是我的颌骨,他说这是我的颌骨凸出来了。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见我不信,他开始强行给我洗脑——“你是不是最近经常用左侧牙齿咀嚼?”,然后我居然乖乖的自己给这样的一个假设找理由——“好像有可能啊,我前一阵右侧臼齿补了个大窟窿嵌体,导致我可能习惯性的避免用右侧吃饭”。于是乎,这之后的谈话就基于这样一个无厘头的假设之下展开了,随机而来的治疗方案也新鲜出炉:不用治,以后吃饭多用右边吃。去年买了个表。。。
长期以为它是个骨头的我,除了在过去两年间尽量用右边牙齿吃饭之外,就没有干别的了。时间跳转到上周末,当我兴高采烈回国开吃的时候,我妈看了一眼我问到,“你脸上怎么凸起来了?”,听完这话我照了照镜子,猛然发现这个硬块长大了!而且已经凸出到了肉眼可见的地步。作为一个已经35岁的中年大叔,我深知自己的生长激素已经应该没啥了,骨头怎么可能会长大?况且我一直在用右边牙吃饭,怎么不见凸起?抱着种种怀疑,我晚上拍了个照问了下在做医生的表哥,但是还没讲几句话,表哥就很紧张的跟我说一定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一下。妈的大难临头的赶脚。
周一:于是一大早便去了苏大附一院挂了口腔科,但是由于是临时挂号,只得看了一个普通门诊。医生看了我的情况,用一种充满抱怨的口气跟我说,“你咋挂了一个普通科,我这里可没法给你开肿瘤”。听到结尾两字真的是给我当头一棒,是的,我脸上长了个肿瘤,然后我还一直以为是骨头,抚养了它两年。。。随后只得拍个片子,带着CT往上海找能挂到专家号的医院跑。所幸很及时地挂到了中山医院周四的专家门诊。周一一整晚就很难入眠,心里压力超大,突然觉得自己好傻好天真。我还想到在上个月美国洗牙的时候,自己还跟洗牙的医生开玩笑说你看我这里骨头还凸了。医生摸了摸跟我说你这可能是个tumor,我当时还没怎么当回事,我简直了。
 周二:拿到了CT片子,初步考虑良性病变,总算长舒了一口气。但又开始纠结了,在国内手术,还是回美国接受治疗?这个问题说实话一直困扰我到手术前夜。我并不知道怎样选择才是更正确的,但一想到这么个肿瘤好像最近变大了,然后美国的预约时长可能非常夸张,就觉得能尽早手术还是尽早为妙。
周二:拿到了CT片子,初步考虑良性病变,总算长舒了一口气。但又开始纠结了,在国内手术,还是回美国接受治疗?这个问题说实话一直困扰我到手术前夜。我并不知道怎样选择才是更正确的,但一想到这么个肿瘤好像最近变大了,然后美国的预约时长可能非常夸张,就觉得能尽早手术还是尽早为妙。
周四:周三去看了一趟亲戚,下午便提前一天住到了上海,然后一大早来到了中山医院的门诊。医生是个青年,感觉正值年富力强的手术达人状态。。。在跟他讨论了一阵之后,很快便决定留下来手术,本来安排在下周二手术,但我跟他说自己周三要飞机回美国,于是他说那你要么明天就手术。。。well,就是这么突然,我成了一个加号,第二天我才知道,医生很苦恼的告诉我,今天他有八台手术,而我是第八台。但因为他觉得我手术很简单,自己也吐槽说不想周六加班,所以我就周五慢慢排吧。
周五:因为是个全麻手术,前一日夜里22点后就禁水、禁食了,同时又因为自己排在最后一个,我一直艰难的等到了傍晚才被推进了手术室。麻醉师是个女医生,姓王,我看了一眼手术室的样子,还说应该放一点背景音乐来舒缓病人压力。。。另外我看了一眼一个电子时钟,最后有记忆的时间停留在17点13分,再后面就昏睡过去了。当自己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点半了。被护工送回了病房。
对了补充一句,在结束了美国独立日休假之后,我的医生也终于回复了我,他跟我说,我的治疗费用学校的医保应该会完全cover,不用担心,但另一方面也跟我说美国的医生、治疗、手术这些安排起来会非常缓慢(一天8台手术他们估计绝壁做不出来)所以他基于我的情况给到我的建议最后是让我在这里把手术治疗给完成再回美国,他说post-op是很重要的,需要注意,哪怕因此而推迟回美国。
周六:这篇是周六写的,因为周日想干点正事儿,毕竟明天的体力会比今天好。
下周又可以水一篇了,讲讲术后。。。不知道后面回学校能否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毕竟长了个肿瘤也不是啥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
PS:封面穿上了病号服,7月的上海真tmd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