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盯着昆德拉寻找一个答案
1929年4月1日出生的米兰·昆德拉如今已经九十余岁高龄。每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大家都在预测调侃村上春树是否再一次陪跑,却似乎忘了还有一位特立独行著作等身,一生都在拒绝大众媒体窥探把自己藏起来的作家。九十年代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其他书名独特的书籍进入中国文坛,一瞬间多少青年人手里捧着如同圣典,仿佛不读米兰·昆德拉就不是读书人,关于媚俗的标签贴在每一个鲜活生命之上。

西方文学史上,毛姆本人称自己为“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余华称米兰·昆德拉为三流作家,就连米兰·昆德拉的老家捷克人也不太喜欢昆德拉身上的气息。大众读者喜欢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大多为零度写作,作家在文字中尽量隐藏自己,而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作品中喜欢夹叙夹议,把哲学意味与政治隐喻放置在故事中,这让小说中的主人公面容模糊,但那些深刻的话语和延伸出来的主题让读者用怀疑态度开始对自己既有状态进行思考。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前两章作者引用了尼采与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对生命与存在的含义进行讨论:
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这其中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人存在世间的沉重感如何在选择中变为轻盈,也就是在轮回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去做一些让内心丰盈有价值的事情才能让人生有意义。把这样的哲学体系放置在特殊的环境下,捷克的布拉格,两位主人公托马斯和特蕾莎身上,讲两种爱情或者两种人生态度下展现轻与重的对立与交融。

男欢女爱的故事放在八十年代捷克极端窒息的气氛中,便有了救赎意味。去掉“布拉格之春”的元素,昆德拉更多让主人公生活在真实中,这种文字上的冒险让昆德拉一度离开了捷克,直到三十多年后再次恢复捷克国籍。当代青年曾经在集体层面与个人记忆中找到与作品的共鸣,现代人也同样在阅读昆德拉中找到生命和人性的本质,直面自己所处的世界。
崇尚自由的托马斯遇见了特蕾莎,他目光盯着院子对面的墙,在寻找一个答案。
和特蕾莎在一起好呢,还是一个人好呢?
爱情,是同一个女人有共眠的欲望。
托马斯在不断的相处和内心的疑问中堕入了特蕾莎的灵魂。特蕾莎在不确定的爱情面前有了嫉妒和混乱,昆德拉将这一对放在他分类的第三类人中,这类人必须活在所爱之人的目光下。这些生命的重量在萨宾娜这里是一种媚俗,在她心中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逃离了这些牵绊,也远离了家乡。
从小镇相遇到从布拉格奔赴瑞士再返回布拉格,最终两人回归田园,小说的落脚点放在小狗卡列宁身上,这仿佛是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去构建人物命运的主线变得苍白无所谓。

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是加拿大作家,昆德拉好友弗朗索瓦·里卡尔对此书的评论,这位昆德拉专家认为昆德拉的作品是一种简单柔和的颠覆,他对阅读造成了一种摧毁。读者在日常生活场景的故事中带着怀疑和忧郁进入到文字面具背后的世界,进而造成思想的爆炸。昆德拉将卡列宁这只小狗的垂死微笑写出了明媚和温馨,关于粪便和媚俗的问题,带有作者独有彻底讽刺。
这篇书评打通了昆德拉不同作品之间的壁垒,在对牧歌的批判中展现作者的“撒旦主义”和牧歌图景下的孤独。
阅读昆德拉需要弗朗索瓦·里卡尔这样的引路人,去打开昆德拉关于政治、历史、诗歌、爱情以及关于普遍的人类认知的视角。这样,才能从阅读中进入到作品中,再挖掘出自我,秩序和意识中发现自我是别人,我还没有成为我自己,在活着中自我欺骗。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洪流里,我们还需要昆德拉的自我,没有简单的愤怒,而是抵抗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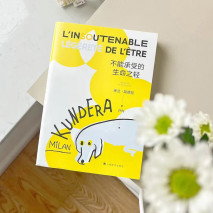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全新版作品)关于爱和信仰三角恋爱爱情斗争和结局的牧歌京东月销量100好评率99%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官方店¥39.7购买举报/反馈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全新版作品)关于爱和信仰三角恋爱爱情斗争和结局的牧歌京东月销量100好评率99%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官方店¥39.7购买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