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古人算出地球直径?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8年译成《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揭秘
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地球的直径是多少?据中国先秦时期典籍记载,“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把这组数据换算成今天的数字,则是地球东西直径13379.52公里,南北直径12423.84公里。经现代科学家测量,地球东西直径约为12756.28公里、南北直径约为12713.52公里,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相差无几。
这是一个令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惊讶的发现,而发现这个计算结果的,是一群俄罗斯汉学家。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于日前顺利结题,在这套六卷十二册的皇皇巨著中,有很多中国学者习焉不察的新发现、新思考,为中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俄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俄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珍贵礼物:
“世界汉学绝无仅有的大作品”
11月中旬,记者带着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好奇,来到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这是一座成立于2018年的研究院,是以儒释道研究为特色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性国际研修平台。据介绍,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将通过发扬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经邦济世、明体达用的“蜀学”传统,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与传承、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成为研究院的重要着力方向,而译介原典则无疑是其中基础且关键的一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进入了四川大学相关研究者的视线。
 刘亚丁教授用俄语作《中国文化》讲座后,莫斯科大学教师表示感谢。
刘亚丁教授用俄语作《中国文化》讲座后,莫斯科大学教师表示感谢。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刘亚丁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的首席专家,据他介绍,《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是一套由几十位俄罗斯汉学家呕心沥血编纂的六卷本中国研究专著。“从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思想,到政治和法律文化、科技、军事思想、艺术,它所展示的学科全面性,使它成为了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绝无仅有的大作品。”刘亚丁表示。
2010年,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年9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副主编卢基扬诺夫一行8人应邀前来参加成立仪式,《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正是他们送给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礼物。“当时我们就跟卢基扬诺夫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刘亚丁说。
 俄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俄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事实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翻译工作,比研究院的成立还要早6年。那时,刘亚丁和四川大学其他俄罗斯相关研究者一道,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写作出版。“从2010年初开始,我就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李志强教授分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俄语教学》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评介《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刘亚丁说。
全新角度:
先秦时代古人算出地球直径?
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成中文,当然不是中俄学者之间的玩笑。之所以如此关注这套书,刘亚丁表示,“是因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适应现代的问题给出了肯定答案。它通过把中国国学的核心问题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相比较,进而发掘出中国国学在人类文化层面的意义,一些新观点值得我国国学研究者关注。”
“俄罗斯汉学在整个世界汉学界中举足轻重,研究中国国情和研究中国精神文化并行,是俄罗斯汉学的基本特征。”刘亚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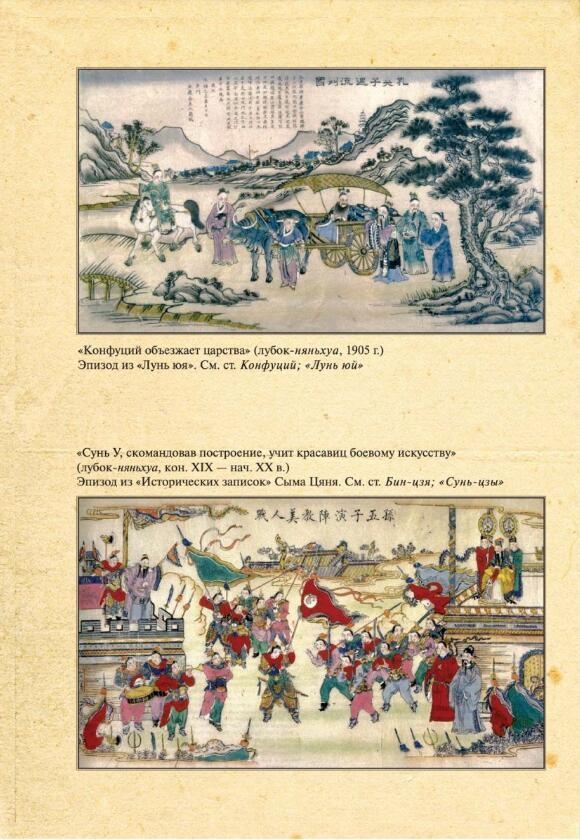 透过俄罗斯汉学家的眼光,《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展现出很多常常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新发现。
透过俄罗斯汉学家的眼光,《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展现出很多常常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新发现。
刘亚丁以《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中的一个细节举例,作者在论及中国先秦的“象数学”时认为,象数学的深处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科学材料,在中国古代典籍《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山海经》中都援引了土地规划者禹的说法:“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作者将这些数字按照周代的里数换算并进行比较后发现,地球东西直径约为12756.28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3379.52公里;地球南北直径约为12713.52公里,上述古籍中为12423.84公里,“这些数字,与地球穿过地心的东西直径、南北直径的公里数惊人地近似。”刘亚丁认为,类似这些早已被古人观察并记录的内容,同时也是值得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课题组开会。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课题组开会。
同样的惊喜还存在于该书的《神话·宗教卷》中。刘亚丁表示,在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对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崇拜,而在《神话·宗教卷》中,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在“关羽”词条的撰写中,首先将中国民间的关羽传说,放置于国际民间文学的视角下,发现民间传说中的关羽“出生时有龙盘旋于屋顶或从龙血中诞生”,儿童时代就“有奇力并好打斗”,曾经“打死横行霸道的官吏”,“这其实与很多民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相似的,但以往我们看待关羽的故事时却没有进行这样的联想。这种梳理让我们看到了‘关羽’传说与国际上其他同类传说的联系。”
深耕翻译:
用脚注指出原作“知识性”硬伤
把俄罗斯人写中国的著作翻译回中文,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轻松容易的工作。
但事实上,正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引述的中国典籍部分,成为了整个翻译工作中的一大难点。“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还无法组成一个既精通俄语,又精通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学术团队。因此学习有关知识就是翻译团队的首要任务。”刘亚丁说。
为了应对翻译时可能遇到的知识性问题,每一卷的编辑人员都会先系统性地学习相应领域的知识。“翻译《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要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熟悉研究,翻译《神话·宗教卷》则要了解《庄子》《淮南子》《道藏》《佛藏》等典籍。”刘亚丁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翻译者在面对具体的词条内容时,可能还需要对单篇内容进行深入了解,“比如翻译《艺术卷》的词条‘图画见闻志’前,就要先研讨《图画见闻志》的中文本,并且最好与俄罗斯作者们使用同一版本中文资料。只有经过这种译前学习,才可能准确理解并写出顺畅无误的翻译文本。”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官网对《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合作签字仪式的报道。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官网对《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合作签字仪式的报道。
一边学习,一边翻译,当千万字的中文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译成时,翻译团队还达成了一项意外的成就。刘亚丁告诉记者,由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毕竟是俄罗斯人来写中国,其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知识结构或者观念意识方面的偏差,“发现原作中知识性‘硬伤’后,翻译团队都会通过脚注的方式来加以指正。这样既对俄罗斯专家的客观立场表示尊重,同时也表达了我们自身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而中译本指出的这些知识性‘硬伤’,其实也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进行修订提供了参照。”
据刘亚丁统计,《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翻译工作,前前后后共有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70余位相关学者参与。除了刘亚丁和李志强两位四川大学的教授分别负责《神话·宗教卷》和《科技·教育卷》的翻译工作外,北京师范大学夏忠宪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文飞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建华教授、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也受邀加入该项目的翻译工作。
2018年,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研究院集合了川大文史哲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他们切磋交流,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工作中信、达、雅的追求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巨大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原来还读过《老子》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们发现,在俄罗斯汉学家们能编写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这样一部巨著的背后,其实是俄罗斯学者、文人数百年来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接受,中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事实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刘亚丁告诉记者,早在1780年,俄罗斯汉学家А·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四书经·哲学家孔子的第一书》就由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这是目前可考的俄罗斯最早出版的《四书》。在为《大学》所写的小序中,列昂季耶夫如此评价这部儒家经典:“学问和律法概念的来龙去脉在这里讲得一清二楚;题名为‘大学’:因为在书中提供了进入幸福之门的路径,它还包含这样的意味,倘若不完善地掌握书中所写的内容,不管是想当圣徒,还是想达致主宰大地,都无从谈起。”随后,《圣彼得堡学报》就此发表书评称:“欧洲人若是忽视中国人的学术,将是非常不公正的。”
 《文学俄罗斯》报就《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专访刘亚丁教授。
《文学俄罗斯》报就《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翻译专访刘亚丁教授。
这种对中国学术的重视,直接影响到后来蜚声世界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写下《安娜·卡列尼娜》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晚年时曾写过一篇名为《老子的学说》的文章,提出“为了让人的生命不是苦,而是乐,人必须学会不为躯体而活着,而要为精神而活着。这就是老子的教诲。”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借一位农民之口说出了“弗卡内奇……为了灵魂活着”。
“在小说里,男主人公列文听到这句话感到狂喜。原来因为找不到精神归宿而几乎自杀的列文,听闻此话当下即悟。”刘亚丁表示,在对这两段文字的俄文原文进行比较后发现,这两段话几乎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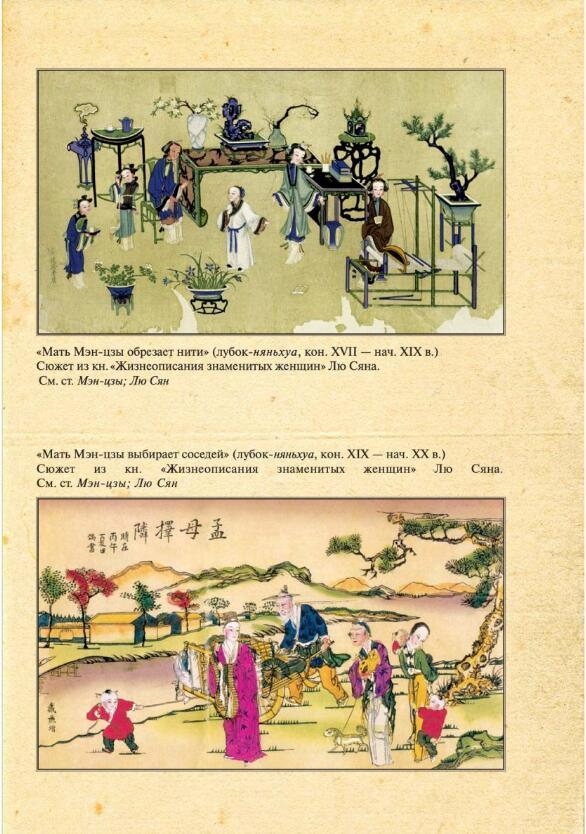 类似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中国的国学经典,俄罗斯一代代汉学家拿了去,俄罗斯的作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放大了它们的影响。”刘亚丁表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推进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又一部重要经典,“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然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汉学家和部分作家起到了桥梁作用。把他们的著作和作品翻译成中文,回馈国人,是颇具意义的工作。”
类似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中国的国学经典,俄罗斯一代代汉学家拿了去,俄罗斯的作家又通过自己的作品放大了它们的影响。”刘亚丁表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推进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又一部重要经典,“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然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汉学家和部分作家起到了桥梁作用。把他们的著作和作品翻译成中文,回馈国人,是颇具意义的工作。”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