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力极差的人如何自救?
表现的症状或后果包括但不限于:1、无法长时间做同一件事情2、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3、情绪管理存在问题,遇到外部影响,情绪波动较大4、常年没有完整阅读过任何一本读物5、由于浅阅读及情绪波动,导致语言表达能力退化,无法将文字顺畅转化为口语进行表达6、精神状态起伏,以致影响身体协调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的起伏7、短时记忆存在问题,在几秒钟之内会忘记之前所要做的事情,想说的话
在今天,迅速迭代的大众文化热潮,总是踩着人们的嗨点前行。穿越、女尊、重生等金手指爽文小说,一度炙手可热的耽改剧,由社交网络席卷大脑的郭语、岚语、“废话文学”、各种时事热梗,票房惊人的战争电影,甚至是东京奥运会期间人手一组的吴京表情包。
我们对文化产品的审视和挑选,进入了更能取悦自己、更直白、更快意的阶段。而我们的生活也在沉入“剩余快感”的无声包裹。

“剩余快感”指向人们内心的“最隐秘情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今天的文化生产表面上被爱情等情感驱动,实际上被剩余快感驱动。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喜欢“享受症状”?为什么剩余快感而不是审美愉悦正在决定文艺消费?今天一些看似荒唐的情形,背后都隐含着有清晰逻辑的理解线索。剩余快感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支配我们的精神。剩余快感的生产,也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生产的真正目的。
周志强教授从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指出在当今资本流行、支配文化市场的时代,文学影视作品往往遮盖了我们的阶级意识和危机意识,使大众沉溺于新媒体和娱乐文化的梦景中,产生了虚假繁荣的想象。
如果大众文化使得人们被傻乐主义、反智主义所围困,那么我们也就丧失了认识真实与现实的能力,因为我们现在往往借助文化符号认识自己与生活。情感越多,真实的经验反而越少。
如何把握我们自我和生活的真实处境?如何使得自己从物化、异化的逻辑中解放出来,超出大众文化的围困?周志强老师从当前流行的网络文学、音乐、热梗等具体现象中逐一解读。
谈剩余快感这个概念之前,我先聊聊最近正在读的一部网络小说,叫作《重生之一代枭龙》。这是一部烂俗但非常爽的小说。
这个小说讲的故事模式大家肯定会比较熟悉:一个叫江志浩的人突然重生到了2000年。在上一世,他的好赌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吃尽了苦头,最终他们自杀身亡;而这一世他就决定从头来过,痛改前非,让家人过上美好生活;“重生”,让他能够知道预知很多人的命运,也因此了解到发财商机,赌石、买古董、股票投资、房地产买卖……让他短短的时间内就财富暴增——这个小说读起来很“爽”。而成了大富豪的江志浩还非常低调,并刚正不阿,有担当有情义,拒绝各种诱惑——小说竟然写出了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

小说的情节是模式化的:总是有骄奢淫逸,看不起穷人的富家子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底和富豪江志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他们见到江志浩,就会轻视他,侮辱他,令他愤怒并进行反击,从而展现自己金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强大势力。简单说,小说故事模式就是“富二代凌辱江志浩,而江志浩惩罚凌辱者”。
我在论文里提到过,《权力巅峰》和《余罪》也是这样的,两个故事都有着欲望狂想的叙事,当我们无力克服强大的资权机制对我们生活的压制时,我们就用想象来取得彻底胜利。表面上,《权力巅峰》讲的是一个无往不胜的官员与各种腐败分子斗争的故事,但是它实际创造了一个有超级能力绝对正确的“极端人物”,而给读者以毁灭一切现实中无力毁灭的强大对象的极端快感。
这类网络官场小说隐含的是一种怨毒和愤恨的文化逻辑,在反抗它描绘的黑恶世界时,又内在羡慕其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样,《余罪》中,这种合理的执政者和纵情的惩戒者二合一,依旧是我们阅读的动力。

电视剧《赘婿》当中同样能看到这类情形:有人欺负赘婿的妻子,赘婿用火枪把他“慢慢”打死。而《重生之一世枭龙》比《赘婿》《余罪》等还要夸张,成为一种“欲望幻想的大爆发”。小说中,江志浩对凌辱他的人进行了无情的屠杀清洗,使别人对他产生无尽的恐惧。血洗、灭门的场景写得非常震撼——这样的场景至少出现了两次。
显然,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所谓道德正义的高大全形象,但小说却并不伸张正义,它被一种诡异快感所驱动:那些在现实生活当中深陷凌辱境地的孱弱者,其实也可以寻找机会,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凌辱那些凌辱者。虽然“江志浩”低调、正直、勇敢而强势,但是,这个人物的塑造,与其说来自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毋宁说来自绝大多数与“财富”无缘的小人物们内心的“无能狂怒”:无数次遭遇嫌弃厌憎后形成的“社会性自卑”。
这部小说没有宣扬正义,或者假装宣扬正义,而是深陷“被凌辱的孱弱者,其实可以凌辱那些凌辱者”的快感幻觉之中。换句话说,希望自己能够像有钱人一样去欺负别人,这种无耻的自卑创造了小说的“爽”。
显然,现在很多文艺作品,总是表面上在讲一种崇高的正义,伟大的道德,实际实现的欲望却是深藏我们内心的那些隐秘快感。我把这种快感称为“剩余快感”。当前琳琅满目,各色各样的电影、电视、小说,甚至我们的生活,都有可能跟这种隐秘的快感紧密相关。

有趣的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可能告诉我们“快感是无耻的”。比如我的同学向我抱怨,自己的孩子都上了研究生,还沉迷电子游戏。甚至我的侄子都认为电子游戏是不好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快感是一种随时可以自我克制的东西,一个有理性的人不能完全按照快感的支配去生活。可时至今日,快感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生产动力。
2020年6月,印度西孟加拉邦纳迪亚地区一个21岁的学生,因政府的禁令无法继续打《绝地求生》,被发现在家里上吊自杀。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她妈妈觉得她爱好电子游戏是耽于享乐,不务正业。直到有一天母女冲突引后妈妈把女儿游戏机砸掉了。女儿在微博上说,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以为是开玩笑,结果发现她真的是把游戏机砸了。这个女孩觉得天昏地暗,在微博写了很长一个事件经过的描述,然后自杀。

快感真的只是一种享受吗?在今天,快感不只是我们的心理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快感也成为了财产。我们因为追求财产而追求快感,我们就会储币。比如,我们购买了大量的游戏,游戏打到某一关,很多时候也是“氪金”的结果;一旦毁掉这个游戏,那么毁掉的就是人们伴随游戏成长的过程、付出的精力以及投入的金钱。所以,快感已经跟我们生命历程、心理成长、财产收益收益紧密相关。
未来虚拟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文学、艺术和生活趋于快感化。只要给身体制造相应的感知设备,提供快感场景,那么,人就会被机器制造出来的快感直接支配。快感也许并不像我们的父母一代所说的那样,是可以靠主观观念或理性就可以克制的东西——它已经客体化了。
我们有必要通过弗洛伊德的两个案例来了解剩余快感。弗洛伊德虽然将它们视为精神病的案子,可是我认为他是遵循精神病学或者医学的态度,但我们如果引入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就会从弗洛伊德的梦境当中,找到比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更多的东西。
第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八岁时在商店遭到性侵,因为年纪小,她并没有什么反应。当她长大意识到这是性侵的时候,她应该恐惧商店而永远不再踏入;然而弗洛伊德发现,这个女孩通过羞耻而得到了快感。一件耻辱的事情,女孩儿本应该是以羞耻心来躲避它,但是,她把这个事情悄悄转换,把被抚摸置换成了店员对她的嘲笑;她将嘲笑视为攻击,把性侵隐藏了起来,于是,女孩身体中隐藏着一个被抚摸所产生的隐秘快感。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可是它就符合我们的精神事实。
乔希·科恩在《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当中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存在着一种“内在他性”,不确切地说,都存在一个不能被你的理性完全控制的“小人”,这个“小人”顽强地追求快感。就像那个女孩她疯狂地追求性的快感,但是她却不得不戴上羞耻的面具。真正让她恐惧商店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羞耻,而是可以通过恐惧商店,默默地享受商店总是跟身体快感紧密相关的情境。这样一个案例,让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深藏了一些被驱逐、被压抑、被禁忌的内心快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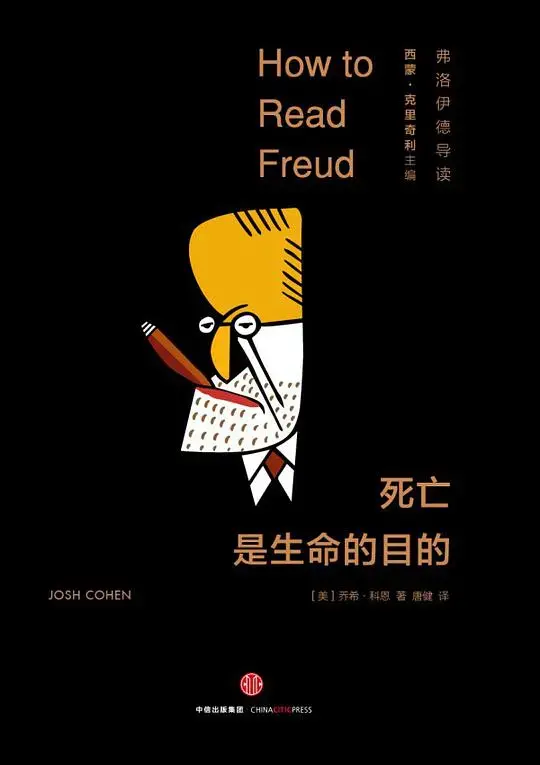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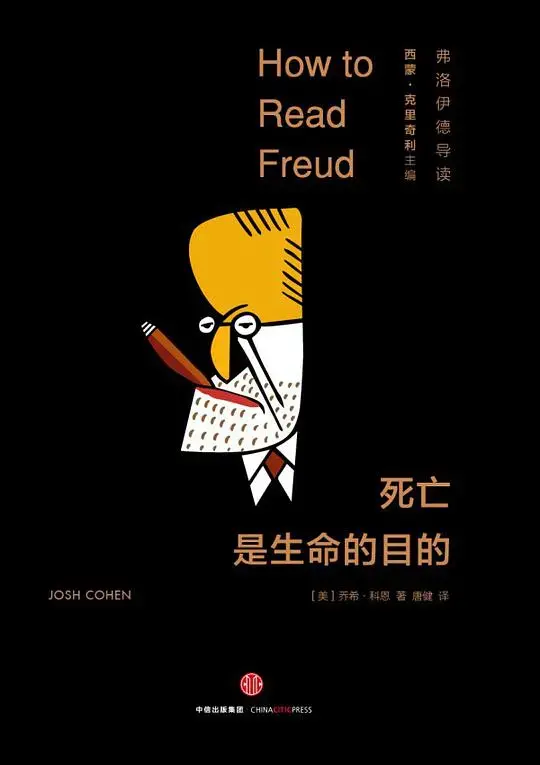
另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则说明,快感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社会化,带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印记。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第二个案例与此有关。一个男人在将要死去的父亲床前陪护,医生嘱咐说,如果陪护不慎,父亲就会死掉。结果,这个男人在床前睡着了,父亲就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死掉了。醒来之后,面对父亲死去的现实,医生告诉他说,这不是他的过错。
但是,这个人从此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寻找同伴,无论是逛商场、上下班还是去洗手间,都要找人陪伴——这个男人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他固执地认为,是自己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他之所以积极地扮演弑父者,疯狂地寻找不在场的证据,是因为他内心隐藏了一个秘密:从7岁的时候就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冲动和愿望,而父亲的死正好实现了这一内心冲动。换言之,父亲死了,这既令他悲痛,也竟然让他满足。
但是,问题的复杂却在于:这个男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导致父亲死亡,却为什么要通过“寻找不在杀人现场”的幻想,积极扮演杀死父亲的角色?因为他只有不断寻找自己不在杀人现场的的证据,才能努力地向自己证明说“我没有杀死父亲”;有趣的是,这也同时暗示自己:父亲的死其实是7岁时被驱逐和压抑的快感的实现——一种剩余快感的实现。所以,这个男人越是努力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他才越能够真正合法地承担导致父亲死亡的角色,作为一个剩余快感的实现者。

我们就把被驱逐、被禁忌、被压抑的愿望实现的过程,称为剩余快感的获得过程。“剩余快感”这个概念不应该仅仅遵循拉康或者齐泽克的意思,还应该回到弗洛伊德那里。它表达了快感的真正位置:在完成了合情合理的安排之外,隐形存在的剩余物。
剩余快感让我们知道,很多文化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有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是深处却蕴含剩余快感的支配性。在话剧《雷雨》当中,周萍和繁漪通奸。一个儿子跟后母通奸,可能打着爱情或激情的旗号,但却是在实施想象性地驱逐父亲的计划——儿子占有父亲的女人,从而占有父亲的位置。这里实现的不正是在想象当中杀死父亲的剩余快感吗?所以,周萍的目的并不是与繁漪的爱情,而是通过占有繁漪,让父亲象征性死亡。

但是,问题更复杂之处在于,周萍和繁漪通奸,又体现了周萍的“卑弱”:周萍充分认识到杀死父亲是完全不能够实现的事情。所以周萍与繁漪通奸既让自己扮演父亲的角色,同时又体现自己不敢对父亲采取直接攻击和对抗的态度。
周萍跟繁漪通奸的行为,在表达新青年弑父愿望的同时,又呈现新青年不可能完全摆脱宗法伦理的生命困境。所以,周萍遵循内心快感的驱动,与繁漪通奸;又因此让自己只能困守快感——快感乃是被理性驱逐的剩余物。
同理,阿多诺曾认为,流行音乐好像给观众带来了快乐,但流行音乐也存在支配性的权力要素。我在很多摇滚乐队的现场看到年轻人在那里随着节奏不断地甩头,当歌手振臂一呼的时候,他们跟着合唱,当歌手把话筒伸到他们面前,他们会替歌手唱那些高潮部分。可是,阿多诺没有认识到的是,乐迷对乐手的服从,表面上是爱乐手,实际却是通过乐手实现自己内心的剩余快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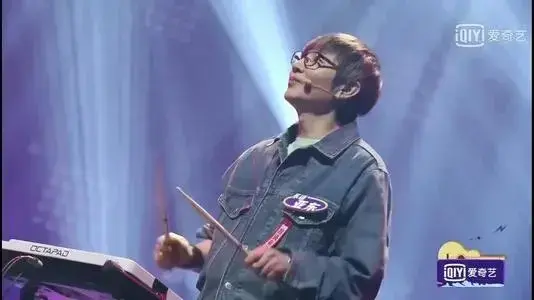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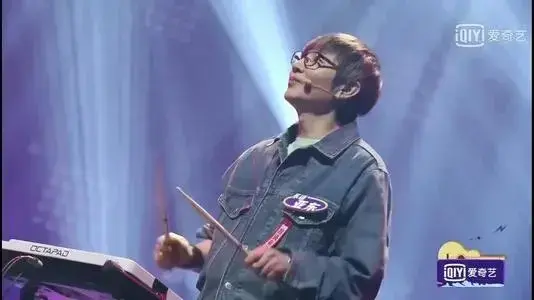
在《乐队的夏天》中,张亚东坚持宣扬音乐理性。他提出观众必须遵守音乐的理性,不能只欣赏乐队的这种“躁”的能力,还要欣赏乐队宁静的能力。然而张亚东不能认识到的是,去看现场的观众期待的,恰恰不是乐队和他一起唱出一首可以直接录成CD的歌曲,而期待的是一个完全不可控的瞬间的爆发,那种真嗓、破音,那种突然之间的狂热,甚至表演性的摔吉他、跳水等,这些是很多粉丝愿意看到的。
换句话说,人们在《乐队的夏天》的现场,真正的要实现的并不是某一首歌毫无走调地演唱,而恰恰是把这种整齐的音乐理性践踏得粉碎的狂欢——尽管这种“践踏”可能是事先设计好的后果。
在这样的乐队现场,只用耳朵能实现的叫做快乐,而用嗓子实现的是享乐。罗兰·巴特把快乐和享乐做了区分,享乐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剩余快感的那种破坏性、冲击性的力量的体现,它是被隐藏的、被禁止的、内在的冲动,在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场景大行其道,自由地挥发激情。
剩余快感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化,在创造着我们都想不到的生命时刻,那么,它是怎样做到的?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当中提出了“疾病获益”概念。他发现,精神病患者会迷恋自己的病症,不愿意变成正常人。弗洛伊德看到了“疾病获益”的第一点,他认为,精神病患者不愿从症状当中醒来,是因为症状对他有好处:精神病的症状是患者的自我保护与自我拯救。在生活当中,如果人们遭遇巨大创伤,就会无法面对,于是就疯掉——而疯狂令人们出离创痛,获得快乐。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用这个理论分析过金庸笔下的萧峰。萧峰武功高强,旷古绝今,这个形象体现了强大的身体狂想。我发现,现当代的中国武侠小说,包括英雄文学、战争文学,都喜欢夸大中国人的身体能量,尤其喜欢强调与外国人进行身体对抗的快乐。如果我们把武侠小说当中所具有的这种身体的狂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性的精神病症,那么,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东亚病夫”这一创伤记忆的自我拯救。当代武侠中的武功狂想,乃是民族曾经孱弱境地的想象性自救。

第二点,所谓“疾病获益”,指的是通过狂想来躲避创伤。只有躲在症状里,人才能够不再被曾经的创伤伤害,因为它让人们把伤害的过程转变成快感享受的过程。
今天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大众文化或者说娱乐文化,不正处在完全沉浸于症状的享乐过程中吗?我把这种状况称为“享乐沉浸”。
费斯克曾经发现,大众文化并不是按照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是按照受支配地位的人的愿望创造的。所以,他认为,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支配性的文化的抵抗,它隐含着解放,可是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种对抗本身是虚无的。
尽管如此,费斯克却向我们呈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发现,游戏厅里面玩游戏的人和在海滩上冲浪的人是不一样的。游戏厅里面玩游戏的人是通过建立人机的关系重新确立一种权力关系,通过跟游戏的交往,取代自己跟现实生活的交往,从而对抗现实中的物质性关系。
海滩上的冲浪者却更为有趣,海滩是一个介于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的界限,海滩上会有牵着狗的裸胸女子,他把它称作dirty,认为狗是介于人和兽之间的符号,而裸胸女子是介于身体的原始状态和文化状态的一个中间状态,因此冲浪者是把海滩这个文本解读为没有所指的文本。换句话说,冲浪者通过冲浪的行动不是要实现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如果我们把费斯克对冲浪者的分析加以引申,它使得我们看到了疾病获益的第三个意义,这是弗洛伊德没有发现、拉康齐泽克也没有意识到,而费斯克完全没有在意的意义,即纯粹的享乐沉浸本身。
纯粹享乐的沉浸,可以让一个人躲在完全不被意义化、不被文化化、不被秩序化、不被规则化的身体当中。简单来说,冲浪者无论做什么,他真正的快乐在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仿佛没有在做什么,他只是冲浪。所以,享乐,或者说沉溺于自己症状的享受,就是能够把自我完全封闭在身体当中的一种行为。
《失恋33天》里面有句话说,今天,谁要是不得个忧郁症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和朋友们打招呼。这句话说出了今天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们通过对症状的沉溺而把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世界中,让自己完全跟那个充满了激励、崇高、前进口号的世界,一个把一切都编织成意义的整体世界截然无关。
网上流行所谓的舔狗,比如有个漫画,舔狗说“我终于忘记她了”另一人说“那很好啊,你喝点水”,舔狗说“她最喜欢喝水了”。人为什么要做舔狗?沉浸在一种“卑恋”的状态当中,把自我卑微化,把个人的情感凝聚在一个带有牺牲感的愿望里;这种典型的舔狗症状,体现出精神异化的状况。

这种舔狗意识,通过损减自己的身体意义,让自己获得悲凉感;一种强烈的沉浸性的存在感。其实,在金庸武侠小说当中,也能看到这一点。杨过断了一只胳膊,张无忌在光明顶上被周芷若刺了一箭,令狐冲在封禅台前被任盈盈刺了一剑: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自残身体,从而引发一种自我爱怜的诡异满足感,这类似于舔狗感受到的隐秘快乐。
网上最近也流行所谓的废话文学,“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上次吃饭还是在上次”“你一定行的,除非不行”。在废话文学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把整个时间都凝固在一个永远毫无意义的、什么都不做的状态当中的情形。废话文学的背后就是冲浪者的活动本身——我在活动,但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我什么都没做,我才能够完整地活动,才能够把运动,把大海,把这些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隔绝起来,封闭在内心的世界当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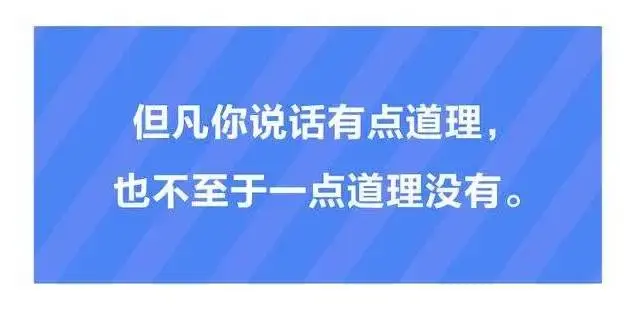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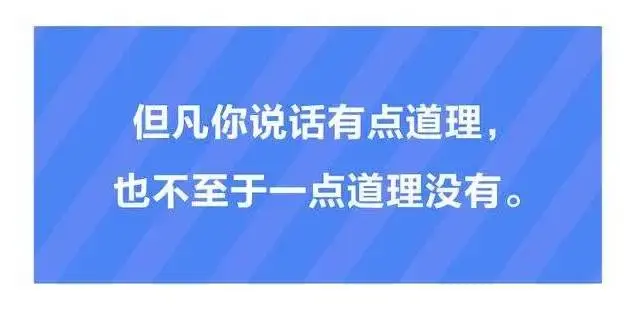
废话文学充满了对有意义的、有秩序的、逻辑化的、确定性的世界全部隔绝的冲动。
恰如剩余价值是资本生产的真正目的,剩余快感的生产,也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生产的真正目的。剩余快感让我们沉溺在精神症状的享乐之中。
这种剩余快感所支配的症状沉溺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看的穿越。穿越作品中,主人公只要掌握一点点现代社会里的有用的东西,类似《庆余年》里的狙击枪或者《风轻尘》里的AK47,当然也包括现代物理知识或医学手段等,有了这些,就可以让整个世界在他面前低头——这恰恰是穿越故事里隐秘的剩余快感的体现。
在很多女性喜欢的耽改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所谓“芭比娃娃情结”:女性所幻想出来的男性之间的爱恋关系,是一种芭比娃娃式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芭比娃娃隐含着这样一种冲动,通过小女孩的面孔和成年人的身体,实现小孩子“无性的性感”愿望。在这里,芭比娃娃指向了一种可爱、纯净、多样而单纯的控制力。

在耽改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男权宰治当中的性困境,用小公主一样的情怀来想象情感规则取代丛林规则的冲动——这也是一种剩余快感的体现:芭比娃娃不仅仅表达了女孩子长大后的理想自我,更隐藏了可以掌控成人世界的隐秘冲动。
周云蓬有一首歌,《不会说话的爱情》。在这首歌里面他唱的是了和自己最爱的人分手的最后时刻。他说,从此以后我们仇深似海,可是分别之前最后时刻,我们还亲昵如火,我们让自己的身体着起火来,拥抱在一起,我们欢愉无限,“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眼泪,都在你的眼里荡开。”周云鹏这最后的欢爱时刻写得如此纯净,但是,越纯美,越优雅,那种仇深似海的悲哀就越强烈。
周云蓬在这首歌里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痛苦悖论——越是向往美好爱情,最后越是剩下纯粹的欲望;越是期望自己的爱情永久,越是能够感受到爱的绝望。反过来,只有当爱情消失的时候,才那样的渴望永久;只有当爱情不可能的时候,才能够深深沉溺在“从此以后仇深似海”的片刻。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看到了剩余快感,那种爱与欲望纠缠在一起所产生的享乐沉溺。

在今天,文学和艺术不单是受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简单的道德情感的支配。他认为,小说就是把曾经让自己感动的东西写进故事中,转而让读者也感动。这显然是不能解释今天的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的。今天的文学不再是象征化、感情化的东西,而是寓言化、症状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支配文学艺术创作的隐秘的力量是剩余快感,而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合理合法的合情性,背后实现的却是隐秘的、被驱逐的剩余性冲动。
当代文艺正从象征型时段走向寓言型时段。每一个作品都隐藏了本身没有陈述的信息;各种压抑性的意义像幽灵一样在银幕与文字中游荡;快感正成为生活财产和生命的动力,沉浸在偏执和分裂之中,才能够得到一些剩余快感。所以在这些看似混乱的文艺现象的背后,存在着非常清晰的文化逻辑和精神意识。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分析、阐释和反思当代文艺新变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寓言论批评”来理解当代文艺和生活的原因所在。我在《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这本书当中想要阐述的恰恰是正是种种“荒谬性合理”的情形。这种荒谬性的合理,在我看来正是当前大众文化快感逻辑的诡异性体现。
在资本盛行的时代,文学表意总是以想象的美好图景代替隐含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总是承诺一个令人神往的未来,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生活在困顿和衰败的挣扎之中;一方面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激发人们瑰丽奇伟的浪漫想象,另一方面总是让人们像机器一样在现实的生活种日复一日地劳作;一方面告诉人们大自然的美丽和爱情的甜蜜,另一方面却永远在物质的层面上走向两极分化。
资本化叙事所讲述的世界的美丽和我们的真实处境是如此的不同:当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办一场婚礼都捉襟见肘的时候,《非诚勿扰2》却办了一场规模如此宏大的离婚典礼;当很多人因为无钱治病而失去生命的时候,《非诚勿扰2》却搞了一个如此温馨的生命告别仪式。

但是,何为我们生活的真实经验呢?所谓的“经验的贫乏”并不是我们生产经验的贫乏,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体系不断生产掩盖现实处境的经验,它不断生产伪经验,所以也充满了对于所谓纯粹经验的强烈追求——它不是对真经验的叙事,它的泪水是建立在物化逻辑之上的。《山楂树之恋》正是一种虚假的、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纯洁,如果没有一个物化的现实图景的话,谁会要那种畸形的“纯”呢?
当前,文学文艺作品中的“生活”与“现实”已然不能等同,描绘生活不代表现实主义。因为今天,生活越来越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现实,本雅明等认为,在资本的逻辑下,我们的生活日益趋于单向度的世俗生活,拜物教的文化在扭曲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缺乏对自身真实处境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有意义想象。
文艺作品中存在着“有生活的假现实”。《乡村爱情故事》系列绝对是“有生活”的电视剧,每个人物活灵活现,细节也贴地气,都是东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场景。可是,看起来打打闹闹的乡村烦恼竟然全是爱情的烦恼,这是一个没有粮价波动或者就医难烦恼的乡村。

有趣的是,这种“有生活的假现实”在畅销作品中屡见不鲜,不论是《何以笙箫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欢乐颂》……这些作品的生活场景、事件和人物情绪,无不栩栩如生;却偏偏不能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处境和困境——写的是生活,得到的是韩剧。
更流行的是“爽生活反现实”。《盗墓笔记》《诛仙》《芈月传》……这些热作,已经构建了自己故事的“异托邦”,自成系列的题材、类型和人物。人们解放了欲望的同时,也就用“梦游”的方式拒绝现实,乃至拒绝意义。它们变成了人们心灵按摩或者精神消遣的方式,于是,“爽”就成了这类作品的核心主旨。
同样也存在着“假生活的真现实”与“无生活有现实”。比如《琅琊榜》算是一个代表者。完全无生活的故事,却不得不依赖对现实政治生态的想象和阐释,其间的尔虞我诈,也就具有对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隐喻性和象征性内涵。

今天的现实主义应该走向寓言现实主义。它不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描绘携带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的现实。面对寓言式的现代文化生产逻辑,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型寓言”与之对抗,即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代替文化生产中的异托邦,用创造新社会的勇气来代替温情浪漫的文化生产的妥协和虚弱,用召唤起来的危机意识来代替被装饰的文化奇观。
-End-
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周志强著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