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像颐和园这样文艺范十足的消磨感情的电影吗?
文艺范十足,涉及时间流逝,空间跨越,感情消磨的题材的?
在颐和园平静的湖面下,存在着无法绕过的漩涡,淹没每一个曾泛舟而行的观影者。
一种海妖的传说是当下最流行的——余虹即是折翼的塞壬:如果在这里存在一种纠缠不清也难以消磨的东西,那便是塞壬的沉默。在这种传说的撰写者看来,塞壬的失语其实就指向了人类文明的最普遍的象征秩序。然而,他们自己不也迷失在另一种海妖的戏谑歌声中,幻想着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刻的主奴关系,成为了那个庸俗道德体系的奴隶吗?

相比撰写神话,小叙事是反叛性的存在,即如读者不必从创作背景、导演团队的意图、专业性镜头语言去构建电影叙事,相比于利用这些外部性语言,我们需要将它与电影叙事隔离开来(正如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这种外部性阻断非但不会将电影叙事封闭于电影黑幕前的时光,而会在黑幕后像呕吐一般全部倾泻在读者的体验与经验中,电影叙述的小叙事正是在如此疯癫的晕厥与惊叫中生成的。恰恰只有在一种流动的、柔性的、不确定的叙事碎片中,我们或许才能接近真实意识的余虹。虽在苦痛与折磨中死亡于电影,生长于上个世纪,却也活于本世纪。

 Bleu, Blanc et Rouge
Bleu, Blanc et Rouge
有一种东西,它会在某个夏天的夜晚像风一样突然袭来,让你猝不及防,无法安宁,与你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能称它为爱情。
像厄运,也像诅咒,一种东西自始至终萦绕于余虹的生活中,这炽烈的情感是内生于她,却又超越于她的存在,它焚烧了每一段她经历过的恋情,却也留下灰烬等待下一次更猛烈的复燃。表面上,这就是“失窃的信”式消失与回归的循环,一如余虹日记中“为何对眼前的一切漠然,而去注目永不可期的事物呢?”菲勒斯中心主义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具有都市色彩的角色扮演以及其中狩猎者与猎物的对立关系,仿佛青涩的与成熟的生活都始终围绕着某种压抑中的永恒,为了猎取它,则在自渎(与幻想)和交媾(与他者)之间徘徊不止。”As a hunter, she has to hunt for it.” 但是这种叙事值得被粉碎,在这种叙事观下,青春、性、激情与生活终将逝去,唯一流转不息的不正是菲勒斯神话吗?即那从始至终存续的秩序:大学之前的乡村宗族伦理——学府中的利维坦——工作单位中冷漠与效率的科层制——公司办公隔间中的泰勒制——婚姻中的奴隶契约,这个秩序正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扼住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意志。在电影叙事中,余虹曾经背离了乡村宗族的伦理(未婚前性行为)、同利维坦绝对意志的抗争(追求自由与理想)、违反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与已婚画家)、违背领导意志(工作)、最后却没有彻底反抗婚姻契约(与周伟重逢后再次分离)。激情在时间流逝中不断消磨直至零碎失形,在她那激情逐渐破碎的生活中,又哪里存在一种未来可期的永恒之物呢?
孤独与流浪亦是如此强烈,如同太阳一般。余虹日记中写道“外面有太阳照耀时/意识里只剩邪恶和憎恨/为了摆脱类似昨夜的这场经历/我愿早早结婚/嫁谁都行”。她在外部太阳的阴影下流露出一种兼并自我厌恶的恐惧,更多的则是一种屈服于苦难却不甘心的怨恨。她忘记了其实她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太阳,是支撑她浪漫地走完过去生活的,也是摧毁了本应存在那里的常规生活叙事(坚硬线)。这一炽热的太阳萦绕于余虹的一生,她所经历的每一段爱恋关系也无不在这内在的生命象征上滑动而过,她所抓取的一切都将在下一次伤痛之前全部融于她炽热的情感中;外面那轮恐怖的血日也萦绕于她,即叛离坚硬线必须付出的代价,她所抗拒的一切都将在下一次千日降临时全部灌注入她的苦痛中。”She is haunting but not hunting.” 这萦绕感若隐若现,如同忽如其来的天灾一般,阵痛随时降临而将身体撕裂,只有永久的麻木,才是躯体在这苦痛与折磨中沉浮的终末归宿。
 A Thousand Suns
A Thousand Suns
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一次彻夜的长谈。但是,我们的关系里拥有不纯之处,它不能以愉快和不愉快而论,我只想生活得强烈一些。
性是常难以启齿的羞耻。在进入电影叙事之前,本人也认为性是天然的纯粹之物,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性化的秩序(主人能指)以及包含这个性化秩序的世界,尤其是在现代世界,性化是无处不在、连绵不绝的象征体,也正是借助它将现代消费社会零碎的符号缝合在权力秩序的网络之上。假如没有这个象征体系,就仿佛不存在性的异化历史了。但是我在电影分裂的小叙事中恰好捕捉到一个真相——即使性化的秩序被消除了,一个被认为是纯粹的、流动的崇高客体,足以诱导我们走向疯狂。当它开始脱离于这个为它赋予意义的象征体系后,代表着我们必须从它的全部幻境中抽离出来,直视那不可理喻的黑洞,即如性快感与性幻想散佚之后人体全部的恶心排泄物都将在现实中返回。
在电影分裂的叙事流中,一种关于性的弥赛亚主义首先被分离出来,一如在余虹日记中“只有在那件事的进行中,你们才懂得我是善良的。我试过多少种办法,可最后还是确定了这个极为特殊、直截了当的方式。我已经一劳永逸的使两个或三个异性了解了我,理解了我的善良和仁慈。”在一个极度压抑且破碎的叙事环境下,宗教仪式是结构缺失且不在场的,但是它依旧值得在宗教意义上对叙事进行截断:在所有关于性交媾的电影叙事中,被提式的狂欢(即性交媾的狂欢)与青春的伤痛是彼此缠绕、无法割舍的,余虹终其电影的一生都在追逐那万众被提之外的提升,一种妄想脱离弥赛亚主义的救赎方式,她最终在那不纯的青春中远离且失落,也从未相信世俗的赎罪券(稳定的关系或婚姻)。在那里除了被提的幻想与过去冗余的伤痛以外其实一无所有,性交媾本身在此处被视作崇高客体,在欲望幻象的不断转换中,在伤痛被诸多幻想遮蔽后,客体的崇高特性才得以构成。当她最终选择栖身于世俗的赎罪券中,那过往历经的一切苦痛,难道不会在某一天全部倾泻而出吗?
“(基督)伤口流出的血落在地上就是肮脏的,不会洗净比它更肮脏的东西。”
在另一个关于裸乳的镜头中(李缇),一种弥赛亚主义在致盲体验中升华到了它的巅峰,它就像是一对注视亵渎者的眼,在这种诡异的神秘氛围中,它唤醒了圣母的诅咒——一个生长于身体内部却僵硬化躯体的奇异法术,一种躯壳的压抑感与毫无征兆的剥离感随之而来。电影分裂的叙事流又抛出另一个诡异的光环——圣母死了。而离经叛道、甚至被冠以玩世不恭之名的余虹,尽管也死于电影(电影自身),但在黑幕之前和黑幕之后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这是弥赛亚主义和兜售救赎券的世俗教会必然否认的,即如圣彼得的否认,上帝的被提永远不会降临,而虚无与亡灵的“被降”悄然而至,一切罪与救赎只不过是电影的黑幕,而黑幕之后一切压抑排斥之物终将回归,如弥赛亚主义的权威一般弑杀一切自称弥赛亚的存在。
圣母已死,弥赛亚主义也将失落。在电影分裂的叙事流中,继承这一失落真相的则是轮回——余虹与周伟的再重逢,却注定又是止步、分别于崇高幻想中。对于余虹来说,周伟已经被刻入诸幻想的轮盘记录上,然后化作凝结体被她的爱欲与情感所吞噬,再也无法找回一个原初的、完整的凝结体了。情感的每一次流动与分流,都是对这一凝结体的撞击、破坏、颠覆、撕裂、粉碎、生成。爱欲就像是在流动平面上保留任意可能性的流水,在每个世界静止的礁石上都涌现出激流,如此难以平静的激流,以至于与她有关系的人、她自己、甚至观影者,都无法逃离这流水中漩涡的引力。我们时常忽视无处不在的漩涡——它是一个在世界中生成的反抗体、包含着极度褶皱的波纹,以为那是一种天然的形态,实则它生成于逃逸的流水,消亡于死去的江河湖泊。漩涡的轮回在于水下不断产生新的空间,漩涡的消亡与新生才能围绕这空间形成。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经历动荡与错愕的时期,粉碎时代的洪流与攻势、粉碎自我的身份与幻想?为更大的漩涡预留出更多的空间,为打破轮回提供微小的可能。
 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
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
我走到游泳池的底下,在深水区和浅水区的交界处,坐下来,
气息在一丝丝耗尽,我对恢复完全没有把握,
我无知觉了。
未燃尽的烟,瘾的余韵,抽干的游泳池,皮肤下悚然不安(Crawling in my skin)。在这个时候一切爱欲都被剥离而去了,剩余的只有一种渗入肌肤的疼痛以及长久折磨中的麻木与彷徨——来自经痛、炎症、药流或自渎(剧本而非电影的桥段)。这并非出于偶然,在过去放纵浪漫与欲望的时刻,余虹对周伟说过“你去做结扎手术……那样就不疼了。”性欲如潮涨潮落般褪去,时隐时现的疼痛却无法期盼尽头的到来,如同农村的牛车一般自愿背负起一种宿命式的教条。在电影分裂的叙事流中,她可能仅在日记中倾诉过伤痛,在日记中承认那爱恋中不纯粹的幻想,但在这压抑与无望中寻求爱欲的自由却总是导向一种断裂与崩溃、一条偏离常规路径的路线。一如爱恋那喀索斯的艾科(Echo),她在爱欲与情感的猛烈回音中放纵浪漫的天性,却也用其电影的一生逃离那致命的回音。
在神话中,那喀索斯恋于自身的镜像,也正如电影叙事中,男性角色总是以叙事棱镜折射的侧面呈现,男性角色都是次要的角色、是依附于大叙事的自恋者(恋父者)。倘若将大叙事拆解,他们在叙事流中成为了机械与人造物,就像结扎削去外部粗糙不堪的皮质,显露内部光滑的神秘器体,除此以外一切皆死物。结扎(circumcise)的第一层含义在于电影叙事自身的解体。在电影叙事的消亡中,我们才得以穿透万象在手术台上剖析那光滑的器物——那充当着幻象再生产的介质。倘若我们没有经历一种后解体时代的生活,我们难以理喻为何人们明知幻象背后是虚无,却仍然愿意于幻境中耗尽生命的信仰与意志。结扎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于一种必须历经痛苦的幻想。这并非是纯粹的失乐园式幻想,而是在痛苦中穿透表层幻象后对幻象回归的期望,一如余虹日记中“眼下越是悲惨,我就越有前途”,在这里不存在一种伊甸园(悲惨的日子将继续),唯有一种微弱却在生活中不断延伸的渴望。但这种希冀不久也将随时代叙事支离破碎。结扎的第三层含义则是苏联叙事彻底解体与后苏联时代的后朋克主义。柏林墙被推倒了,不久之后推倒墙的推动力也将再迎来自身的空洞倒塌,人们试图像过去一样在宏大叙事的手术中弥补幻境,却最终在时代的极乐迪斯科中步入虚无主义。人们自以为稳固的存在根基,记忆与家,正处在剧烈的动摇中,人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中异化成工作机器,就像悬置在怪核时空、失去精神支撑、疲劳无力地维持漫长而不安的余生。在异国他乡,或在陌生的故乡,一切所熟知的生活、家乡、世界都在无声无息地改变面貌,余留不多的记忆也在余生中渐渐遗忘。我们自认为安定的精神世界,被烧出一个洞来,幽深的恐惧从这唐突的空洞中蔓延出来,然后在这焦虑不安中我们发现自己,竟然也可能只是一个空洞。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存在的感知亦被扭曲,一切信仰、坚持与记忆都在崩坏。在余虹与周伟最后一次重逢中,他们在幻想中找到现实中彼此的存在,却也迅速地在幻想燃烧殆尽后逃离彼此,燃烧的灰烬余留了最后的残念,但这些残念也注定随风飘逝。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投影,那炽烈的爱欲与情感既不会滞留在过去的幻想中,也不会困囿于任何一种未来的幻想了,而是同那幻想灭亡后的空洞与虚无所交合在一起。
 Здорово и Вечно(伟大而永恒)
Здорово и Вечно(伟大而永恒)
经痛、炎症、药流与自渎;分手、工作、怀念与交媾。在瘾与疼痛中承受如此之多,以至现实与幻想的边界模糊而失序,幻想入侵了现实,现实也报以穷困与子弹,在幻想消殒后,现实也不过只是眼前苦涩的烟酒生活而已。对她而言,再也没有晦暗能使她看得更清醒,也再没有刺破眼前视野的光芒,只是她自己正是那漫长迷雾中光怪陆离、却逐渐暗淡的变形光线,等待着那些更阴沉的日子。
 雨中匍匐前行
雨中匍匐前行
生活中总缺失一些东西,就像淋过雨后严重起来的慢性病。
一次短暂的自杀念想、几滴苦涩的眼泪、一块不走的钟表、一个亵渎的姿势,在穷途末路之前,常会遇见寥寥数个值得余生追忆的他者。追忆的时光是漫长的,似乎都在烟酒的日子中消弥了,在过时的艺术中失忆了。电影叙事从始至终是温和的,它要么被封闭在实验室里,要么被缝入形形色色的建筑中,但是无数种日常的恐惧敲碎了电影叙事,在此刻所有的镜头都成为了空镜头,所有的画面都成为了黑幕,所有的对话都成为了谵语。在这叙事的粉末中我们语词新作、鼓盆而歌、赖以苟活。
在难以穿透的冰冷寂静中,回忆的时光是痛苦的,我们默默前行的道路遍布着前人的啜泣与伤痕,在轻盈的世界中我们相识,却因沉重的过去而悼念分别。在这片霉菌与鸦鸣四处弥漫的土地上,相比于六十年多前那青春中的动荡,我们是否舍弃了文化与信仰?相比于三十年多前那动荡中的青春,我们是否放弃了自由与理想?即使是在此土地上生长的我们,也常在六十年前与三十年前的过去中误认彼此,为何在这片土地上误认彼此?相比于本世纪那挣扎中的困惑,过去的人是否又丢弃了稳重与未来?这是无解的问题——历史尽然只有一次,人生也尽然只有一次,或许在叙事的粉尘中我们还能发现些许端倪,那些在历史编纂的谎言中封存的话语,但没有期待于任何真相的降临;那些未来得及说出口却死于火焰与瘟疫的话语,但也害怕寒冷与长寿;还有那些失忆者与失语者共同书写的语言。有时过于轻浮,有时也过于守旧;有时热情似火,有时也冷酷如寒夜;有时抑郁,有时也向死而生。在这片继承千年苦难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被埋入夜晚的雪地、肉块与血消融的灰白泥土,在次日的阳光下他们腐败的骨架与罪恶的血液型渗入枯萎的草地,于次年生长的灌木与野草上留下微弱的印记。
 泛舟湖上
泛舟湖上
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
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
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
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氧气》
当青年不再年轻,是电影的叙事流化作生命激流的时刻抛给我们的碎片。在这里,无处不充溢着,青年理想与井然秩序的碰撞与理想破碎之后的伤痛。但是那些关于民主与自由、青春与激情、情爱与沉沦的梦,也许早已在一切变故与惊醒之前预示了其消亡史、然后再编织、再幻灭的轮回宿命。
颐和园,过去的皇家园林,如今的皇家园林博物馆,不正是封建历史中掠夺与压迫的遗产吗?园中泛舟是每一代人的浪漫时光,那些流连忘返的记忆也是无聊、痛苦的余生中聊以慰藉的回忆,可是难道我们不曾注意到这昆明湖底下所埋葬的,是在王朝更替、军阀战争与时代剧变中那些被遗忘之人日夜流淌的血液与眼泪?新一代青年在体制的辐射中成长起来,他们相信新世纪的梦想,带着酒与激情冲向梦想中的未来,却在秩序的铁丝网前失血而亡。颐和园湖中隐匿的骸骨与血块,是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也是每一代人在梦幻的憧憬中不曾熟虑却也终将到来的血腥风暴。骸骨在积叠、血块在融合、湖水在不断上涨,这在现实中重复过无数次,它就与“皇家园林博物馆”一同被缝合入意识形态机器的再生产中——抱着新世纪的梦想,却在机枪、铁丝网与拒马前铩羽而归;点燃蜡烛反抗,不过又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傀儡木偶;倘若尝试拥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激情,在过往的神话中误认彼此,却更不免遭受封锁与绞杀,只剩下一个出路——拥抱体制神话,在那秩序中实现伟大的“编制康米主义”。然而,历史永远未被终结,难道在意识形态机器的垄断与压抑中,体制神话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在那压抑下的黑暗世界不会喷发出无数窒息而剧毒的火山灰,淹没一切井然有序的建筑吗?
颐和园外,何以为食,易子而食,何以为炊,析骸以爨。体制神话远不止依靠它庞大的工业机器,在一种垄断经济、文化与历史,掌控意识形态生产机器,将资本主义分形结构内化的宏大叙事的核辐射下,人们甘愿“为一块牛排出卖巴黎”,为体制神话奉献劳动力与人口后代只为挣取一张体制的入场门票。在这里,没有人会耻笑墨索里尼(投靠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意社背叛者),赖伐尔(曾经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最终为维希效力)与汪精卫(曾经的left-kmt领袖最终却投日),因为体制神话的信众也愿意纳投名状换取体制的圣餐——鼠群与饲鼠人的盛宴。
在一个跨越地平线的视野中,体制神话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老、神秘、邪门的巨屋。这里的仪式已经深刻嵌入当代人的头脑中,倘若离开了圣仪式的庇护我们就会迷茫、失语与流浪,仿佛明天就会过上逃亡的生活。也许在逃亡的日子里,我们才会发现它那错杂的、永无止的根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当青年不再年轻,他们会选择铁丝网还是入场券?恰如在电影叙事流中,一切曾经年轻的激情都将在时间的扭曲中消散——激情之后是什么——是信仰的崩塌,生命的空虚,还是移情于幻想亦或是自我厌恶?那空洞死寂的生活,是悔恨于过早熄灭还是未曾燃烧过?那再度唤醒的激情,是将消逝于今夜还是抹去于黎明?假如这激情在年轻时从未降临,我们还会相识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吗?当青年不再年轻,还会在局外人的艺术中,寻找那些因自由意志而窒息的同类吗?我们不会在电影中消失,也不会在陈述中消失,而是在电影黑幕之后、在翌日的生活中消失,但这一切终将在某个不起眼的时刻归来。
我们曾经的热血与情爱化作遗忘的过去,沉闷地失落在这片土地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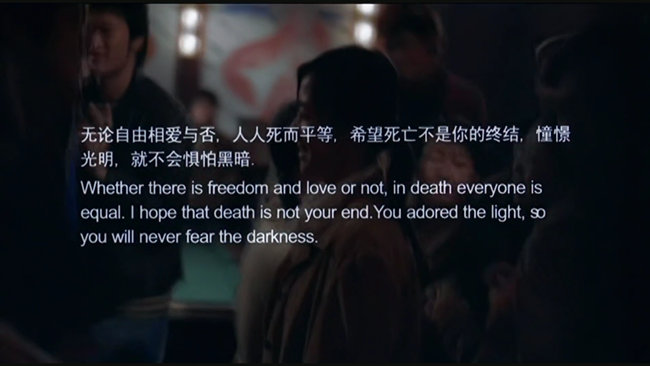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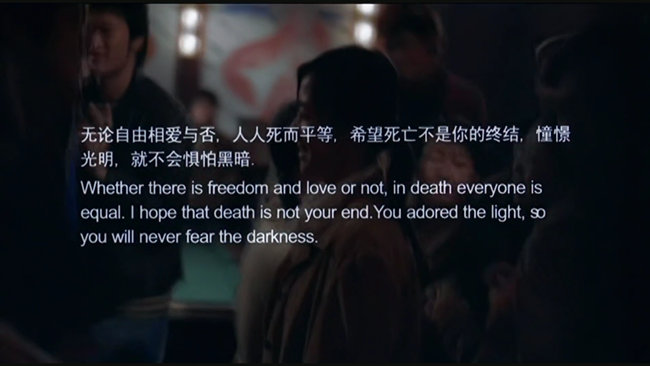 仅认同第二句
仅认同第二句
My Gratitude, Attachment and Appreciation to Ray
2023年1月11日于上海
原文链接:影评|随想于《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