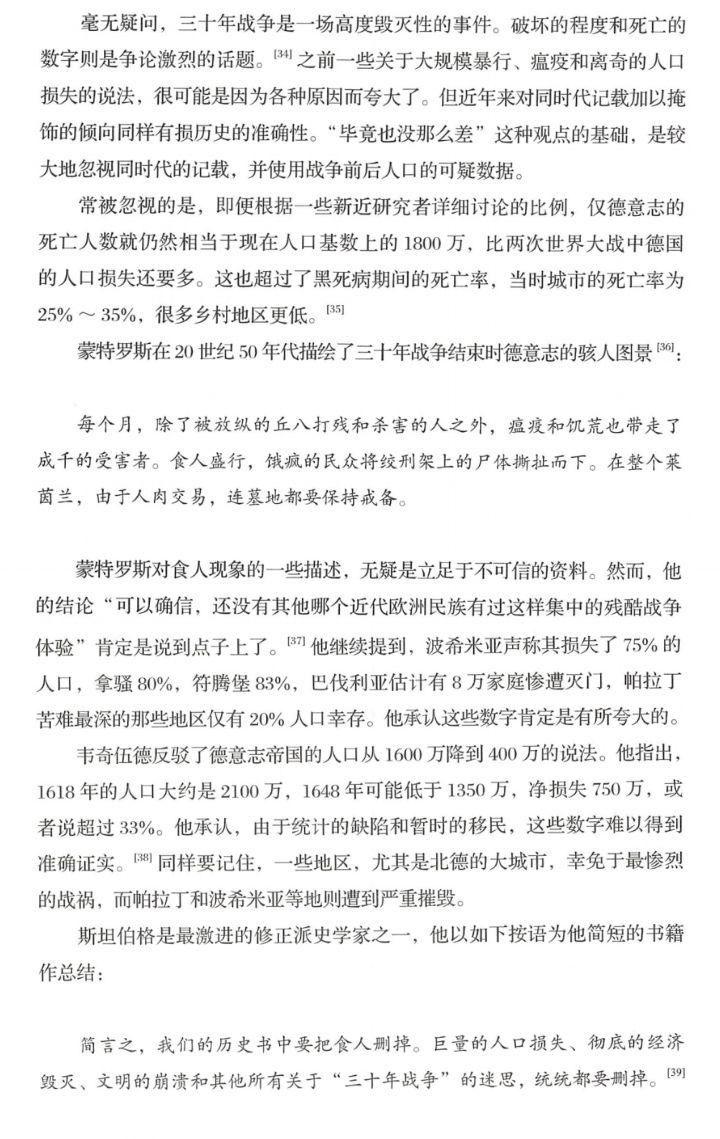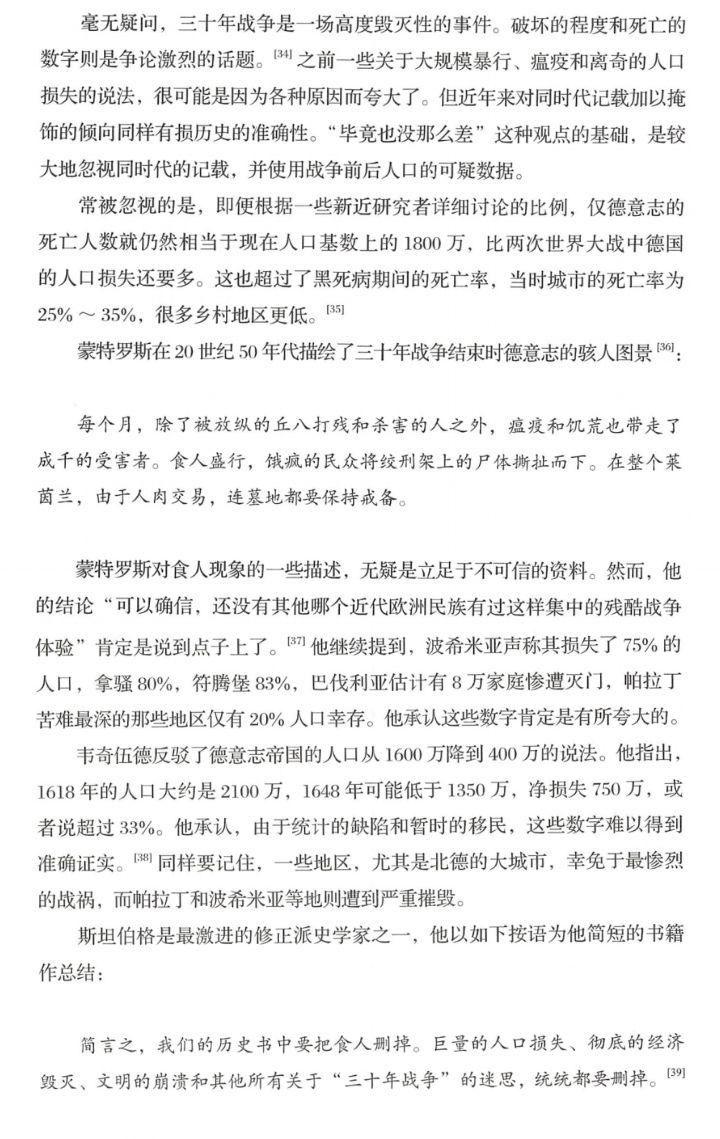欧洲历史上有没有过人吃人的现象?
这个问题不由得想起这件事。
吉本说罗马帝国时期人口超过一亿,可能吗?网友经常能看到反思帖中一个中国和欧洲历史人口对比的图,中国大起大落,欧洲缓慢上升,评论转发区一片哀叹讥嘲汉地是修罗场,出了汉地都是地上人间的言论。
秦朝的民生与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相比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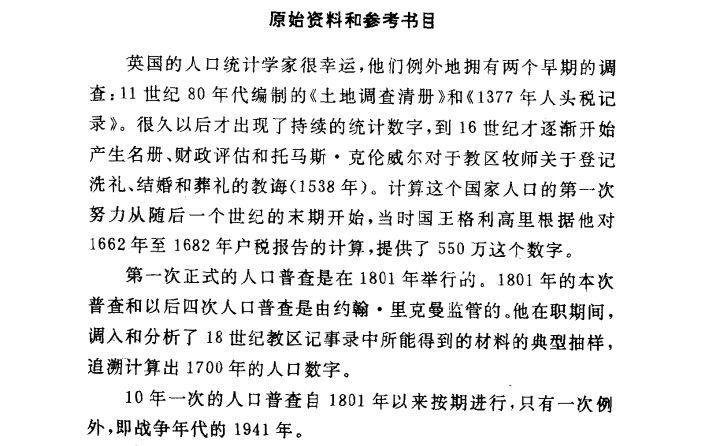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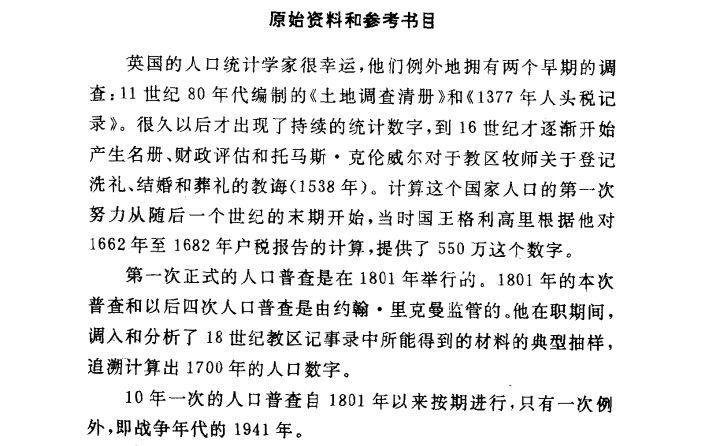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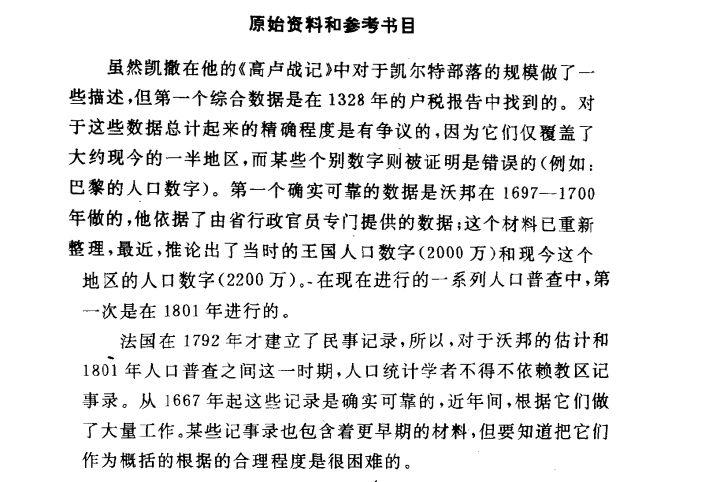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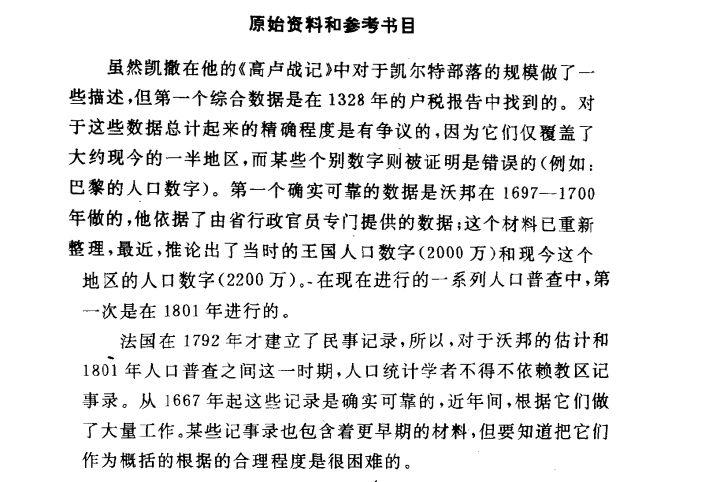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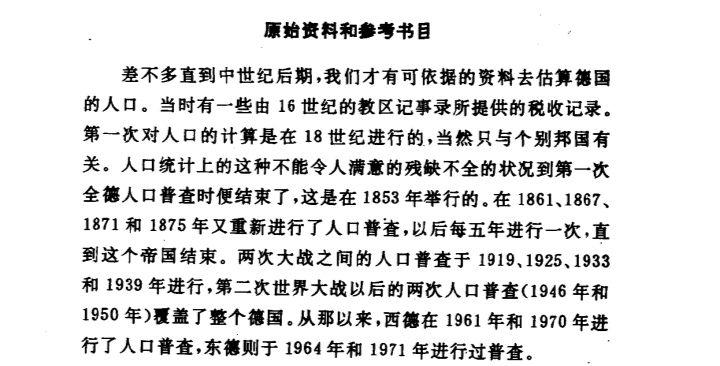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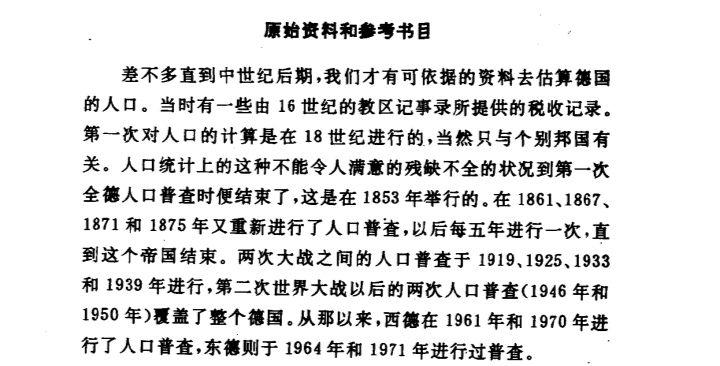 这个理论取自于近代欧洲之前很少有普查全国范围人口土地情况,只有少数几次征服者威廉进行普查,绝大多数欧洲是近代才开始全民普查人口,而中国则战国时期各国就年年进行普查,公元前就留下了全国人口土地情况,年年有官吏进行普查。
这个理论取自于近代欧洲之前很少有普查全国范围人口土地情况,只有少数几次征服者威廉进行普查,绝大多数欧洲是近代才开始全民普查人口,而中国则战国时期各国就年年进行普查,公元前就留下了全国人口土地情况,年年有官吏进行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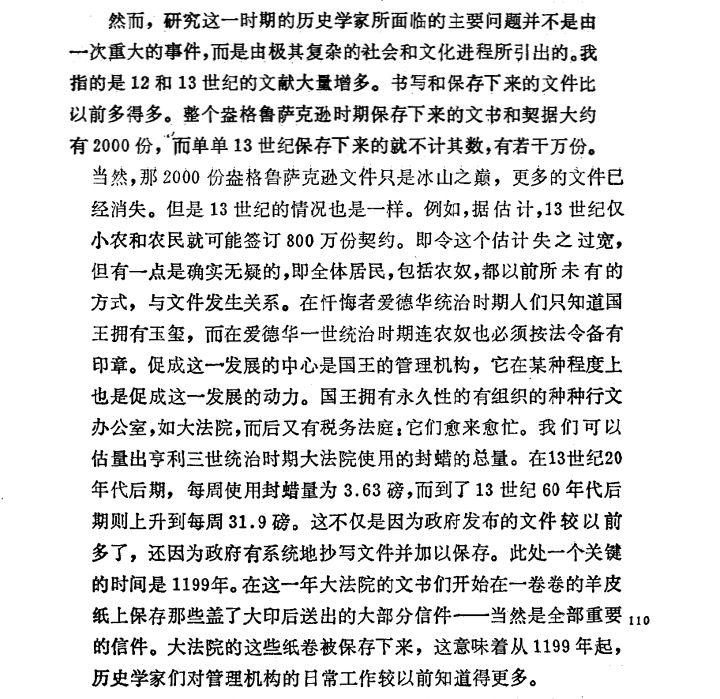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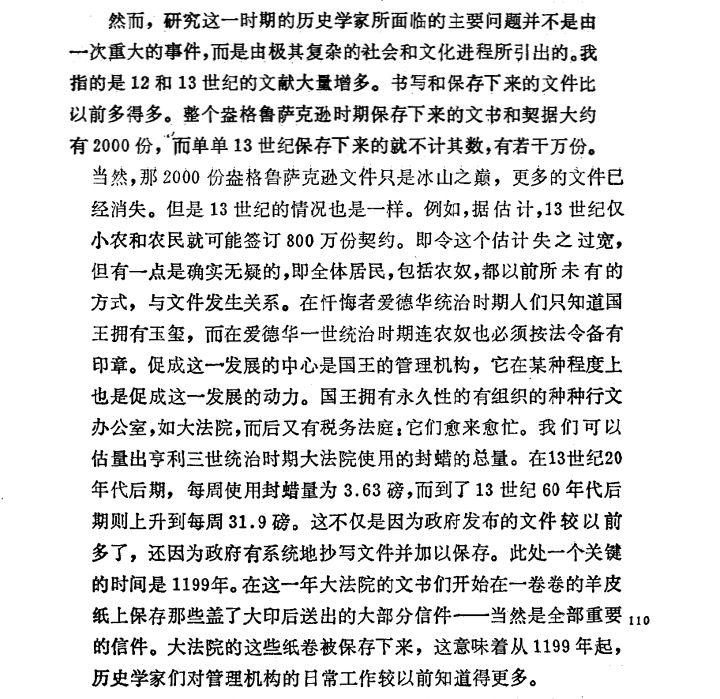 有网友提到中世纪欧洲档案多,没错,但这并不代表会有各地区全国普查人口的档案,因为当时压根就很少统计,基本没有东方式的普查,威廉那次可以,但很遗憾没有一直保持,总欧洲而言,编年记传体史书记载内容详略和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有网友提到中世纪欧洲档案多,没错,但这并不代表会有各地区全国普查人口的档案,因为当时压根就很少统计,基本没有东方式的普查,威廉那次可以,但很遗憾没有一直保持,总欧洲而言,编年记传体史书记载内容详略和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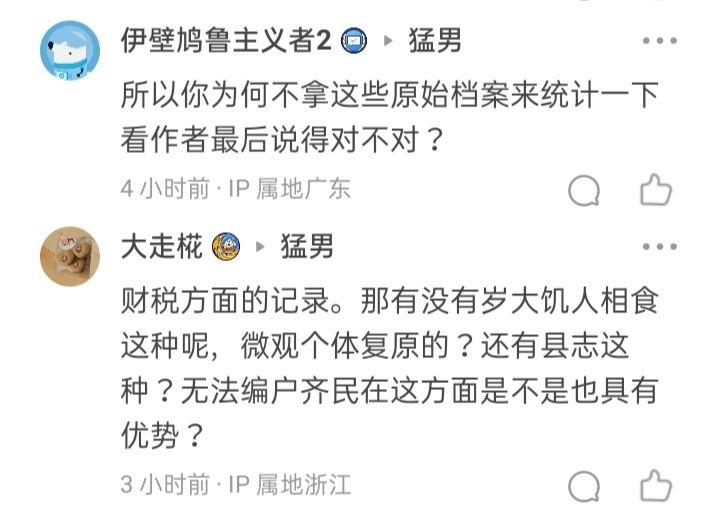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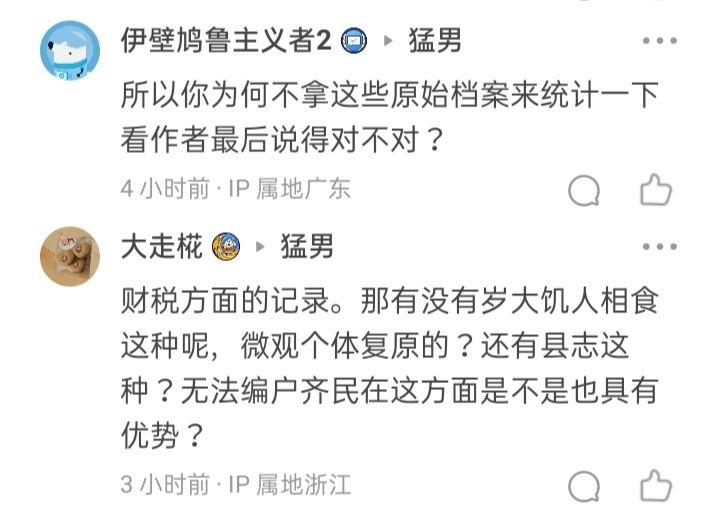 有网友提到要用档案统计,其实也统计不了多少,因为甲虫引用论文的最初来源也不是档案,而是县志,如果去查现存六千多万字的明档也查不出多少食人记载,因为欧洲档案绝大多数记载的是诉讼纠纷契约文书以及官民财产清单贸易等。
有网友提到要用档案统计,其实也统计不了多少,因为甲虫引用论文的最初来源也不是档案,而是县志,如果去查现存六千多万字的明档也查不出多少食人记载,因为欧洲档案绝大多数记载的是诉讼纠纷契约文书以及官民财产清单贸易等。
回到食人记载,比如记载大明食人上千次的资料来自县志记载,我看了几个省部分明清县志,而县志记载分为“某年大饥,人相食”,仅仅简短几句几字,还有一种是某某年灾荒,饿殍遍野,死者上万数万之类段落,但无食人记载,可见随意性,对于食人并不是严格调查后的标记,更像是一种中文特有的衍生虚文。
有记载某县饥荒,有一人杀子相食,发现处死,于是县治安大定,那这县有食人记载,但这能说明有食人记载的县比那死者数万没食人记载的县情况好?
对于县志记载的食人记录,具体时间,范围,强度等都没有记载,我觉得这些食人记载大多数来源可能是某某年饥荒,在某地发生几起个体食人事件被发生处死,但事越传越广,若干年后修县志采访老人说某年县里某处饥荒有吃人的事,于是记载了某某年饥,人相食,今天网民便幻想当时几万几十万人,几百几千上万平方公里同一时间不分地点,一整年都在互相“人相食”,这种看法是很可笑的,除了王朝末期乱世出现大型流寇之外,这种情况几乎很少见,因为还有官府维持秩序,赈济灾民。
将几起可能十起都没有的个体事件认为是普遍的,我看多了都自动忽略,除非以下记载: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熟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引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备陈大饥疏这类亲自调查,惨烈强度,规模都有可靠记载,但食人最多不过数千,甚至一千都没到,绝大多数去抢掠或者饿毙。
欧洲则没有记载“大饥,人相食”的笔法传统,编年记传体史书也少有记载,不过还是有的,当然你如果单查二十四史并明清实录也找不到上千次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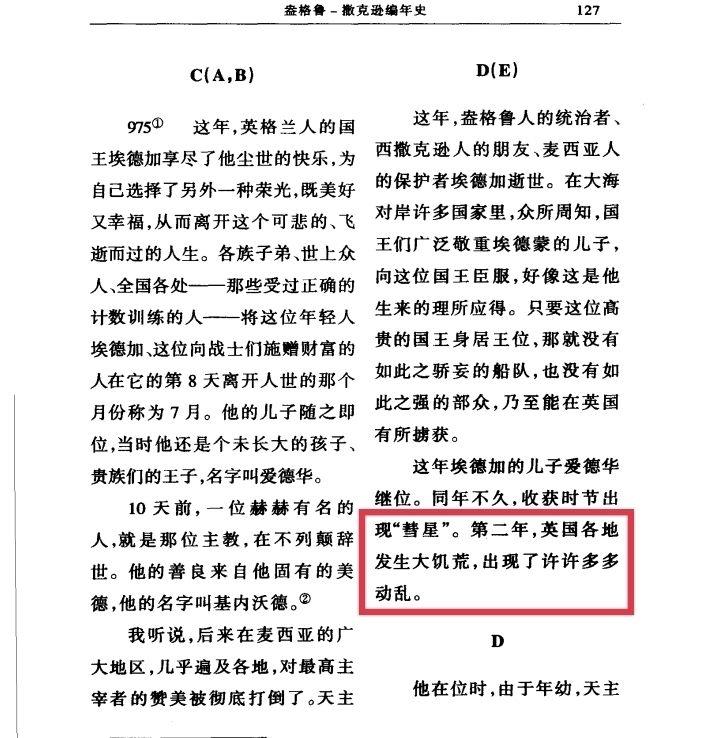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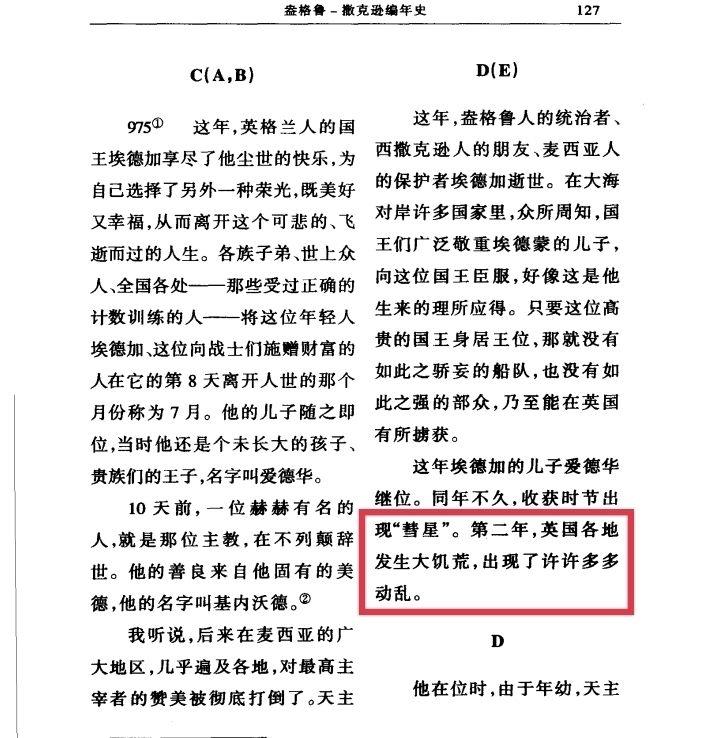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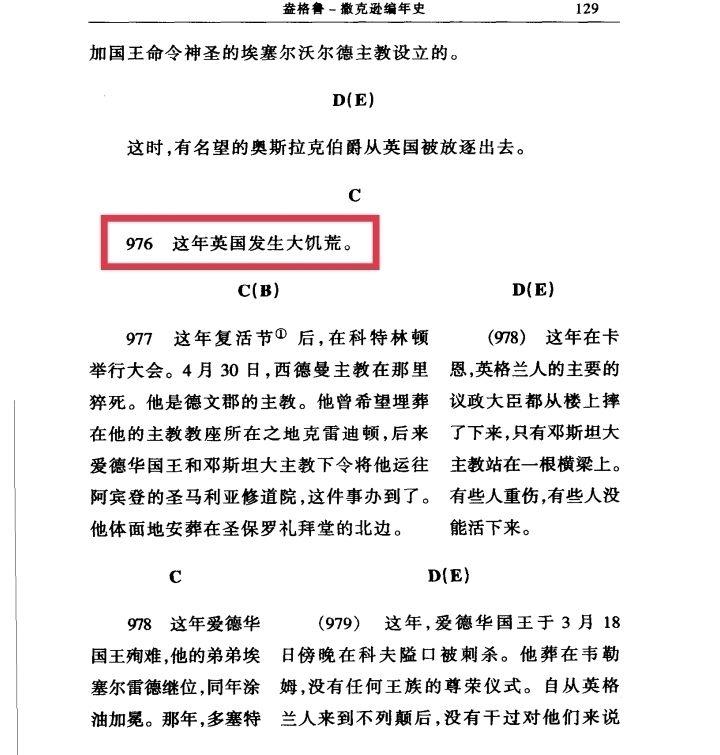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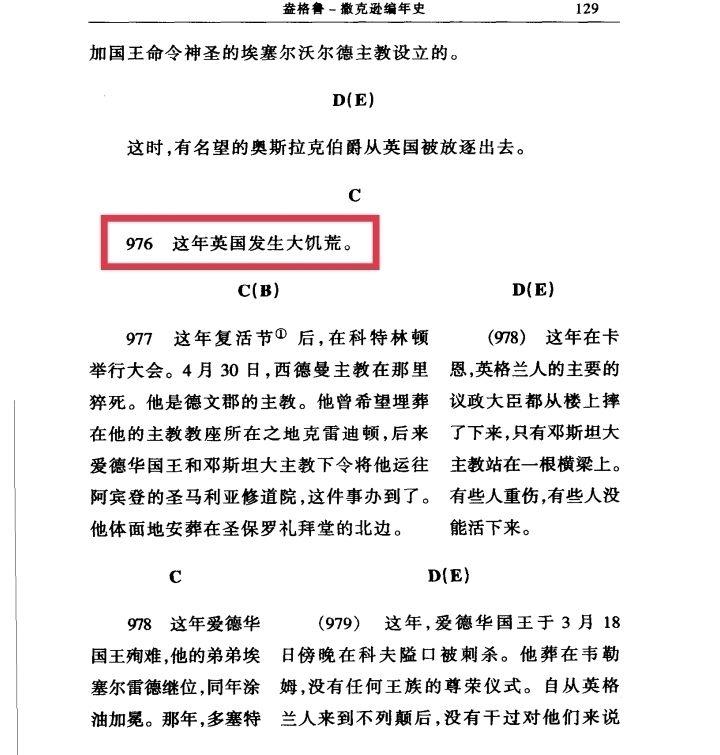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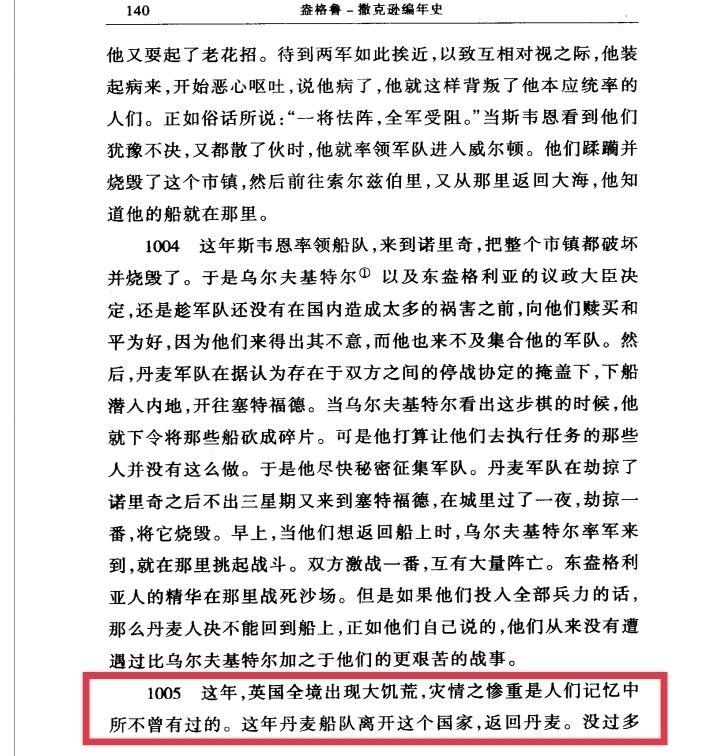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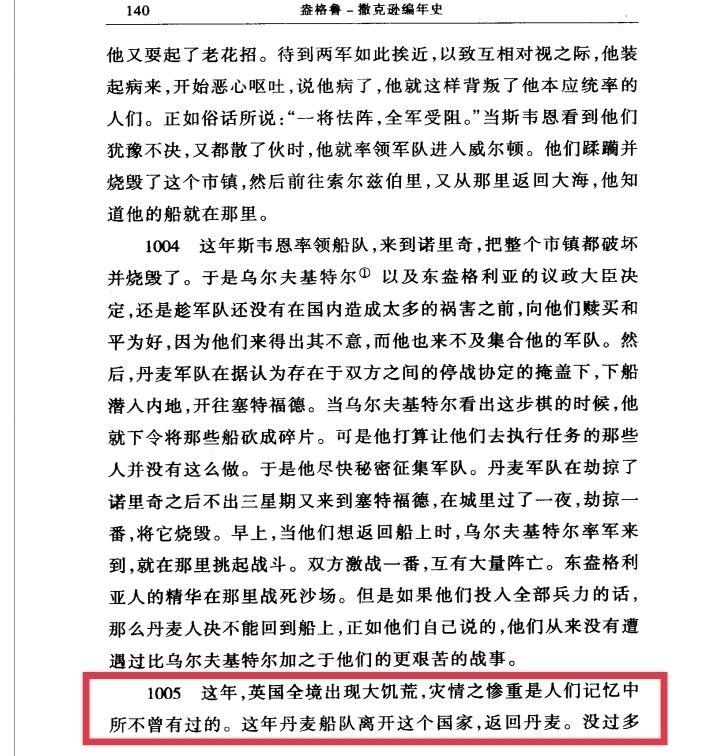 看惯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你,有没有一种冲动,想给加上后缀“人相食”?
看惯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你,有没有一种冲动,想给加上后缀“人相食”?
当然如果不记载或者删了就认为没有,不得不说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