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国维的万字红楼梦评论?
官方说法是开近代批评派先河。请问它的开创性具体表现?
中国古典文学有三方向,分为考据、批评和创作。三项全能,方称一声“中国古典文学学者”。
在这三方向中,不同的学者、专家术业亦有专攻,比如叶嘉莹先生长于古典诗词批评,周汝昌先生深耕红学考据。当然这二位先生的诗词创作水平,或叶之考据、周之批评水准自然不凡。仅以此最大贡献的成就而论,则推叶之批评,周之考证。
静安先生王国维,曾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是三项全能。其中静安先生著力最深者,是考据。其论殷周、释甲骨文、释钟鼎文、考元史、蒙古史皆为开辟新学观点的卓越成就。若论其二,便是批评。静安先生众批评著作中最为世人称道者,便是《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王国维 著
文学批评之风,古已有之。南朝 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便是其中翘楚。诸子却推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之开山,何也?
盖静安先生之《红评》融汇叔本华悲剧哲学与审美观,先介绍哲学观、审美观,再用这二观去验证《红楼梦》之文学精神、美学精神、理论学精神。全文意蕴深长、时有佳句、令人拍案。
古人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静安先生著作之前诸多词说、诗说、戏曲或文学评论(包括《人间词话》)都基于批评者与作品作者之间的独有共鸣,而有分享。此种分享,犹如授人以鱼,读者得尝鱼鲜,却多限于当时所感。
静安之《红评》则不然,开卷《人生及美术之概论》即言其人生观、审美观。但凡认同其哲学观,读者大可运用其审美逻辑品评红楼及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修养及见识。犹如予人以尺,以度玑衡。将文学批评一个“斯人所感”的特定批评感发形式,转变为给予模式方法之“可重复检验实验”。
正因如此相比《诗品》、《文心雕龙》这些“只能意会”的古典批评著作,在阅读静安的《红评》时,论及其哲学理论与理论运用,现代读者更容易找到其逻辑漏洞和生搬痕迹。亦如钱钟书先生、叶嘉莹先生共指出《红评》生搬三重悲剧理论与《红楼梦》所致之硬伤。
静安先生《红评》优劣之处和历史地位,笔者已在此文末引述《叶嘉莹论红楼梦评论》,诚为当世所见、解静安最深、最权威一文。叶先生对静安先生,爱之深矣,责之切也。尤其篇末以心心共鸣,求静安《红评》致误主因,与笔者有戚戚焉。
时人多言,述哲学、审美观者,亦不必为持其哲学、审美观者,更难为任其哲学、审美者。 更多有咪蒙之辈,推波助澜,以淆视听。静安先生二十六岁写就《红评》,如何判断文中叔本华生活之欲哲学与悲剧审美观,是静安先生深以信,毕生以任的思想观点呢?
笔者愿以《红评》文中“天眼”二字窥得一斑。《红评》谓有一处提及“天眼”,而静安晚年得有《浣溪沙》一首,再言此处“天眼”:《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叶嘉莹论《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之写作时代及内容概要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最初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那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时代,比蔡元培所写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蔡氏索隐初版于1917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胡氏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早十九年(俞氏文初版于1923年)。蔡氏之书仍不脱旧红学的附会色彩,以猜谜的方法为牵强附会之说,识者固早以为不可采信。至于胡氏之考证作者及版本,与俞氏之考订后四十回高鹗续书之真伪得失,在考证工作方面,虽有相当之成绩,可是对于以文学批评观点来衡定《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方面,则二者可以说都并没有什么贡献。而早在他们十几年前的静安先生之《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之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之文艺价值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在静安先生此文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文学著作的批评。所以静安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因此,即使此文在见解方面仍有未尽成熟完美之处,可是以其写作之时代论,则仅是这种富有开创意味的精神和眼光,便已足以使其在中国文学批评之拓新的途径上占有不朽之地位了。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在正式讨论这篇论著前,先要说明其写作年代的原故。因为必须如此,才能明白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学批评之拓新方面的意义与价值。根据《静安文集》自序,《红楼梦评论》一文乃是写作于他正在耽读叔本华哲学的年代,所以这篇论著乃是全部以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观点为依据所写的一篇文学批评。为了便于以后的讨论,现在先将全文主旨做一概略之介绍:《红楼梦评论》一文共分五章,首章为《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而由“欲”所产生者,则唯有痛苦,所以“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之本质既为痛苦,而美术之作品则可以“使吾人离生活之欲之痛苦”。至于美之为物虽又可分为优美与壮美之不同,而壮美之“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异”。所以“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这种对人生及美术的看法,是静安先生衡量《红楼梦》的两大重要标准。于是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即举出《红楼梦》之主旨“实示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盖因自杀之人未必尽能战胜生活之欲者”。而出世之解脱则又有二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之解脱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所以《红楼梦》一书之精神主旨乃在写宝玉由“欲”所产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静安先生首先举出叔本华的三种悲剧之说,以为《红楼梦》正属于第三种之悲剧,足以“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所谓三种悲剧之说,据王氏引叔本华之说云:“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之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而悲剧所表现者多为壮美之情,可以“使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最高之悲剧可以“示人生之真相及解脱之不可以已”,《红楼梦》正为此种之悲剧,其“美学上之价值正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于是第四章便继而讨论《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主要在说明“解脱”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然而此一说法,实在极难加以证明,所以静安先生乃设为疑难以自辩答,其大要盖谓世界与人生之存在,并无合理之根据,而当世界尽归于“无”,则可以“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且世界各大宗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主旨,“哲学家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红楼梦》正是“以解脱为理想者”,此即为《红楼梦》在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为余论,主要在说明旧红学家之纷纷在《红楼梦》中寻找本事的考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所以“考证本事”并不重要,而考证“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方为正当之考证途径。所以《红楼梦》一书之价值,并不在其故事之确指何人何事,而在其所表现之美学与伦理学上之价值。《红楼梦评论》一文之长处与缺点之所在从前面所介绍的全文概要来看,做为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著,《红楼梦评论》是有其长处也有其缺点的。先从这篇文章的长处来看,约可简单归纳为以下数点:第一,本文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论基础,仅就此一着眼点而言,姑不论其所依据者为哪一家的哲学或美学,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了。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不仅被人目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一向没有人曾经以如此严肃而正确的眼光,从任何哲学或美学的观点,来探讨过任何一篇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睿智过人的眼光,乃是《红楼梦评论》一文的第一点长处。第二,如我们在前面所言,中国文学批评一向所最为缺乏的便是理论体系,静安先生此文于第一章先立定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于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对此书之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之评价。更于最后一章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新红学研究考证所当采的正确途径,是一篇极有层次及组织的论著,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批评体系之建立,乃是本文的第二点长处。第三,在《余论》一章中,静安先生所提出的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日猜谜式的附会,为以后的考证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途径,这是本文的第三点长处。不过,尽管《红楼梦评论》一文有着以上的许多长处,可是它却无可挽回地有着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以叔本华哲学为解说《红楼梦》之依据。本来,从哲学观点来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着手的途径原是正确的。只不过当批评时,乃是应该从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来探寻作品中的哲学意义,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处,然而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理论,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而静安先生不幸就正犯了此一错误。因此在这篇论著中,虽也有不少精辟的见地,却可惜全为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所限制,因而遂不免有许多立论牵强之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乃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做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依据,甚且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说:“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合之处。首先,《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静安先生指“玉”为“欲”,不仅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猜测勉强立说的通病,而且这种比附也证明了他对于《红楼梦》中宝玉之解脱,与叔本华哲学中绝灭意志之欲的根本歧异之处,未曾有清楚的辨别。叔本华的哲学虽然曾受东方佛教哲学的影响,可是因为东西方心性之不同,所以其间实在是有着许多差别之处的。而最根本的一点差别,则是东方佛教乃是认为人人皆具有可以成佛的灵明之性,这纔才是人性的本质,至于一切欲望烦恼,则是后天的一种污染。所以佛教的说法乃是“自性圆明,本无欠缺”,其得救的方法只是返本归真,“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这与叔本华把宇宙人生一切皆归于意志之表现的说法,实在有很大的不同。《红楼梦》一书中虽表现有佛家出世之想,然而其实却并不同于叔本华之意志哲学。如果“宝玉”在《红楼梦》中果有象喻之意,则其所象喻的毋宁是本可成佛的灵明的本性,而决非意志之欲。如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一节,作者便曾藉着癞头和尚的口中说过:“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而且在书中开端作者也曾叙述这宝玉原是经女娲氏锻炼之后遗在青埂峰下一块未用的灵石,虽曾降世历劫,最后仍复回到青埂峰下。从这些记叙来看,则此“玉”之不同于叔本华的意志之“欲”,岂不显然可见。再则静安先生全以“灭绝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为《红楼梦》一书之主旨所在,如此则宝玉之终于获得解脱,回到青埂峰下,岂不竟大似西方宗教性喜剧,这与全书的追怀悼念的情绪,也显然有所不合。三则静安先生在第四章论及《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时,对于叔本华哲学之以解脱为最高之理想,也曾提出了疑问说:“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其后静安先生在其《静安文集》自序中,也曾提出过他用叔本华哲学来批评《红楼梦》之立论,其中原有疑问,说:“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既然静安先生也已经承认了叔本华之哲学本身就有着矛盾疑问之处,然则静安先生自己竟然想套用叔氏的哲学来评论《红楼梦》,则其不免于牵强附会的误解,当然也就从而可知了。除去以上我们所提出的用叔本华哲学来解说《红楼梦》的基本的错误之外,这篇评论还有着其他一些矛盾疏失之处。其一是静安先生既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建立在与伦理学价值相联络相合一的基础之上,因此当其以“解脱为最高之理想”的伦理学价值发生疑问而动摇之时,他的美学价值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就连带着发生了动摇。何况静安先生于论及《红楼梦》之美学价值时,不过仅举叔本华的三种悲剧为说,而对于西方悲剧之传统,及美学中美(beauty)与崇高(sublime)之理论,也未能有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和发挥。而且,当静安先生写作此文时,对于曹雪芹之家世生平,以及后四十回为高鹗及程伟元之续作的事,也还完全没有认知,因此他在第三章所举出的第九十六回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当然便也决不能做为《红楼梦》一书美学价值之代表。凡此种种当然都足以说明静安先生以西方之哲学及美学来解说和批评《红楼梦》,在理论方面实在有着不少疏失之处。总之,《红楼梦评论》一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其主要之成就,乃在于静安先生所开拓出的一条有理论基础及组织系统的批评途径,而其缺点则在于过份依赖西方已有的成说,竟想要把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完全纳入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的模式之中,而未能就《红楼梦》本身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来建立起自己的批评体系,其成功与失败之处,当然都是值得我们做为借鉴的。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一文致误之主因静安先生之治学,一向原以谨严著称。然而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他却有着许多立论不够周密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点:其一,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而言,在清朝光绪三十年的时代,中国既未曾有过像这样具有理论系统的著作,更未曾有人尝试过把西方的哲学美学用之于中国的文学批评。静安先生此文是在他所拓垦的洪荒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第一个建筑物,所以既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所表现的某些思想有一点暗合之处,便掌握住这一根可以做为栋梁的现成材料,搭盖起他的第一座建筑来,而未暇于其质地及尺寸是否完全适合做详细的考虑。这种由拓荒尝试而造成的失误,当然是使得《红楼梦评论》一文立论不够周密的第一个原因。其二,则是由于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心态,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及《红楼梦》中悲剧的人生经验,都有着许多暗合之处,因此他对于叔本华的哲学和《红楼梦》这部小说,遂不免都有着过多的偏爱。李长之批评《红楼梦评论》一文,便曾特别提出过静安先生对《红楼梦》之强烈的爱好,说:“王国维把《红楼梦》看着是好作品,便比常人所以为的那样好法还更好起来。”于是静安先生遂因自己性格和心态与之相近而产生的一点共鸣,把叔本华的哲学和《红楼梦》的悲剧,都在自己的偏爱的感情下结合起来,而写出了这一篇评论。所以这一篇论文在理论方面虽有许多不够周密之处,可是另一方面,静安先生却恰好藉着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及《红楼梦》的悲剧故事,把他自己对人生的悲苦绝望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性格和心态的因素,实在才是使得静安先生不顾牵强附会而一厢情愿地以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来解释《红楼梦》,大谈其“人生”与“欲”及“痛苦”三者一而已矣,而且以为“解脱之道唯存于出世”的一个最基本的原故。而静安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悲观绝望之心态,便也正是因为他在自己所生活的腐败庸愚争竞屠杀的清末民初的时代中,同样也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原故。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前所发表的《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及《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两篇文稿中,已经对之做过详细的讨论,所以不拟在此更加重述。总之,每一个作者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心态,而每一种感情心态的形成,又都与作者之性格及其所生之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才智杰出之士,虽偶然可以突破环境之限制,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人世更为深广的观察和体会,但终究也仍不会真正超越历史的限度。如果以本文中所谈到的几个作者相比较的话,李后主虽然以其过人之深锐的感受能力,对人世无常之悲苦有着较深广的体认,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只拘限于个人外表情事之叙写的另一个亡国的君主宋徽宗,【按,王国维曾谓宋徽宗之《燕山亭》词,“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可是李后主毕竟是一个久已习惯于唯我独尊之地位的帝王,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他一向所过的奢靡享乐的生活,都是他本分之所应得,他所悲慨的只是这种享乐之生活不能长保的今昔无常的哀感而已;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之胜过李后主的一点,则是他虽然也生长在富贵享乐的环境中,然而他却超越了自己阶层的限制,看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不平。不过在现实生活方面他却又毕竟仍依附于他所归属的官僚腐败的家族之上,并未能配合自己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破,而在生活实践方面也有所突破;至于陶渊明则不仅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自我的觉醒,而且更能在生活实践方面,真正突破了他所厌恶的官僚腐败的社会阶层,而以躬耕的劳动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点。不过,陶渊明所完成的仅是“独善其身”的一种自我操守而已,对于真正有理想有性情之读书人在封建腐败之社会中所感受的困境,并没有什么改革和解决的帮助。因此在陶渊明以后的一千多年的清代,这种没有出路的困窘的心态,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还一直存在于一些不甘心与腐败之官僚社会同流合污的有理想有性情的读书人之中。曹雪芹所写的“枉入红尘”“无才补天”的宝玉,当然就是作者自己心态和感情的反映。关于这一方面,在香港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一书中,周汝昌和冯其庸的一些论文都曾对曹雪芹的时代家世与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关系做过详细的探讨,他们虽偏重强调曹雪芹的反叛性格,然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最后却只能以“悬崖撒手”为结束,则其困窘无出路之心态,实在并未能在现实生活中有所突破,这当然是《红楼梦》一书所受到的历史的局限。至于对《红楼梦》特别赏爱的王静安先生,则最后竟然以自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心态之仍在悲观困窘之中,更复可知。其实静安先生所生之时代,正是中国旧日封建腐败之社会,从崩溃走向新生的一个突破的转折点,不过旧的突破和新的诞生之间,当然会产生极大的矛盾冲突,甚至要经历流血的艰辛和痛苦。静安先生以其沉潜保守而缺乏反叛精神之性格在此激变之时代中,竟然以其深情锐感只体会了新旧冲突间的弊病和痛苦,而未能在艰辛扰乱之时代中,瞻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他的局限实在并不只由于历史的限度,而更有其个人性格之因素在。这一点不仅是造成静安先生个人自沉之悲剧的主因,也是限制了他的文学批评,只能做主观唯心的欣赏和评论,而不能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一些客观因素,对作品中意识心态的主旨有更深入之了解和批判的主要原故。所以静安先生对于《红楼梦》中的悲观绝望之隋,虽有极大极深之感动,然而却未能对书中的主旨做出更为客观正确的分析。如果说《红楼梦》意蕴的丰富正有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妙,则静安先生之“不识庐山真面目”,可以说就正是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故了。从以上的讨论来看,静安先生用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其所以造成了许多疏失错误的结果,原来自有属于静安先生个人之时代及性格的许多因素在,我们当然不可以据此而否定一切用西方理论来评说中国文学的作品和作者。不过从《红楼梦评论》一文之疏失错误,我们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作品来附会某一固定之理论,原来是极应该小心警惕的一件事。李长之就曾批评《红楼梦评论》一文说:“关于作批评,我尤其不赞成王国维的硬扣的态度,……把作品来迁就自己,是难有是处的”。而现在一般文学批评的通病,却正是往往先在自己心中立定一项理论或教条,然后再勉强以作品来相牵附。这种文学批评,较之中国旧传统说诗人的愚执比附之说,从表面上看来虽似乎稍胜一筹,好像既有理论的系统又有进步的思想,然而事实上则东方与西方及古代与现代之间,在思想和感受方面原有着很多差别不同之处,如果完全不顾及作品本身的质素,而一味勉强地牵附,当然不免于错误扭曲的缺失。然则如何撷取西方的理论系统和现代的进步观点,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做出公平正确的评价,这当然是今日从事文学批评者所当深思的课题和所当努力的方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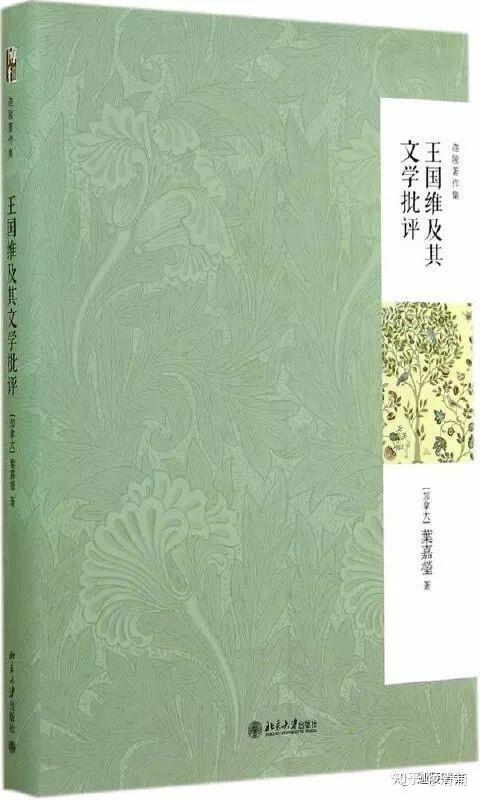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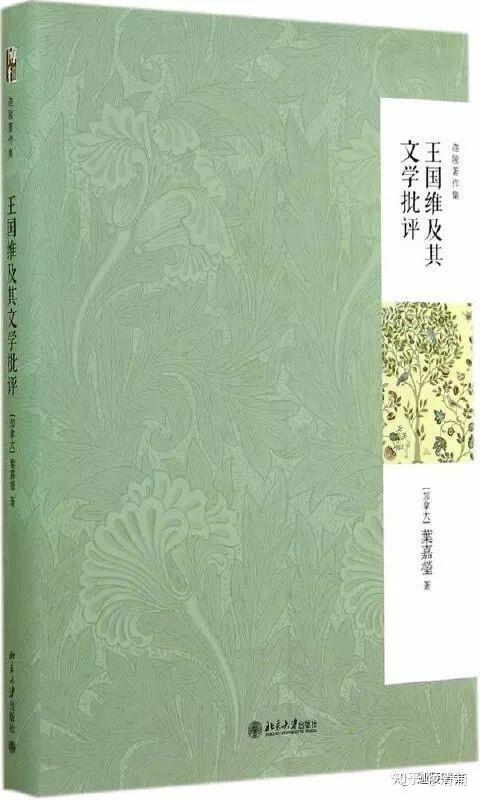
引源: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