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地评价《金瓶梅》?
毛泽东说《红楼梦》与《金瓶梅》都是天下奇书,但《金瓶梅》不尊重女性。
可以更详细更客观地评价一下吗?
谢邀。
先定基调:这是本非常好的小说。
口语对白之活泼灵动,不只是中国,放世界文学史上都是顶尖。
在“时代风俗画”方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小说——对当时风土人情的还原描绘,就《红楼梦》都未必胜过。
叙述精炼明快,语言干净老辣,仅是叙述,只有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堪可比肩。如果要挑剔士大夫文学性,那里面出现过的曲儿,可媲美《红楼梦》里的诗。
此小说最妙的两个:
一是没有脸谱化,没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大家都是俗世男女。这种不带是非、刻意减少评判的劲儿,有福楼拜意味。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就是《红楼梦》做到人物性格如此多面、饱满而不戏曲程式脸谱化。
二是大悲悯心,繁华与落寂之间的大落差,以及对每个小人物命运的关怀,都非常动人——同样是唯有《红楼梦》、《水浒传》可以媲美的。
跟《红楼梦》一比,会更有趣些。《红楼梦》更像《牡丹亭》,而《金瓶梅》更像元杂剧。前者是兼工带写的长卷,后者是工笔+界画式的描摹。
《红楼梦》醇浓虚渺,如烟雨写意,莫可名状,但也有些坏处:这是部太有诗意、意在言外的小说,难译,难理会,尤其对非中文读者来说。
《金瓶梅》却是部更接地气、更一目了然的叙事作品。实际上,在”事无巨细的市井日常风俗画“方面,《金瓶梅》可能是中国史上最出色的作品。它更看得见摸得着,它更接近《人间喜剧》那种”全景式小说“的意味。
看《红楼》看完前八十回再看后四十回,味同嚼蜡,《金瓶梅》自从西门庆死后其实也一泻千里,看得人沮丧,但是比起《红楼》后四十回,失望要少得多,这个叫兰陵笑笑生的作者本来就没有曹雪芹的工整精致较真,哪怕发力最猛的时候,《金瓶梅》也有作者心血来潮随便写的手笔,比如李瓶儿出殡,他写到兴起能写那么长跟主线关系不那么大的东西。
《金瓶梅》这本书,很多人说它坏,无非是色情描写与人性丑陋,说它好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从技术性上分析也非常强大,我个人以为它的好在于,作者有一种对人世的强烈好奇,他不是为了文学创造而写书,他就是对他生存过的这个真实世界觉得非常有趣,故作一番记录,而,碰巧他又是个天才,于是就有了这样独树一帜的《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一直无法考证,只留下“兰陵笑笑生”这个笔名飘然世上,兰陵是地名,笑笑生,仅仅这三个字,就不太可能是后人猜想的王世贞要报复严家故而做书,他似乎没这么严肃。
“好玩”是《金瓶梅》的腔调,从改编《水浒》就看得出来。
《水浒》里光芒万丈的武松到了《金》里还哪有什么英雄气,杀个潘金莲还要勾引人家这种下三滥手段,老实巴交的武大郎到了《金》里也挺下作,而这一切的原因是《水浒》的这些塑造不符合作者的亲身观察,大概他接触的生活里,英雄的另一面有可能是“狗熊”,而看似老实凄惨的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他观察人世观察得细,又非常擅长于描绘。
《水浒》里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的场景:
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变坐笑吟吟的脸儿。
而到了《金瓶梅》里这一幕就变成了:
这人被叉竿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赛鸦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翘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白鲜鲜、黑漆漆,正不知是甚么东西。
这两段的最大对比是《水浒》的描写就是套路,一个妖娆妇人,任凭谁看都是,而到了《金瓶梅》,潘金莲的容貌描绘,是通过西门庆的眼睛来看的,看到的都是“脚”“胸”“腿”以及那个什么,但是这就是男人在看到猎物时候的注意力所在,哪怕现在,男人充满情欲看女人,看到的也就这些东西,若隐若现的春光,长腿细腰大胸等,而不可能是别的。
与其说,这是文学技巧,不如说是作者很懂男性怎么看猎物的心理。
写到这里,很多人又说了,这个作者就是个变态才这么写,纯色情眼光,整本书都是,非也。孙述宇先生就说过一句话,我们看《金瓶梅》,不会怕西门庆这个人,但是看《水浒》,我们倒有点会怕他。
《水浒》里的西门庆事实上写得很套路,就是凶横奸夫,但是《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所作所为常常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如果有此联想,那么这本书就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变态和纯色情读物了”。
我之前举个一个例子,吴月娘跟西门庆说给官哥儿订了一门亲,结果西门庆还嫌弃对方不是正室所生,结果潘金莲插嘴说,哟,说得好像官哥儿是正室生的一样。(官哥儿是李瓶儿生的,也是小妾生的)。然后西门庆恼羞成怒抓过潘金莲就开始揍!多嘴找打,谁让你插嘴了?这儿有你的事吗?要你说话了吗?
换个场景类比,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一个姑娘,自己挣那么几千块一个月长得也就那样,但是相亲回来非常嫌弃对方,说对方家庭条件不好工资低人太矮,还对媒人各种不满,这种类型的你也介绍给我!这时候他父母跟她说,你自己也就这样啊,挑什么呢?这姑娘是不是常见的一蹦三尺高,我说了让你给我找吗?我稀罕吗?
西门庆常年泡妓院,有一回在妓院争风吃醋受了气,踏月回家听到老婆吴月娘在为他祈祷,一时感动坏了,发自内心的想,与其流连外面花草,往后不如回家伴妻眠,当天晚上,跟吴月娘缠绵恩爱的不得了。好了,过几天又恢复原状了,出去勾三搭四了。
这种体会,我想常人都少不了,这次考试没考好,受了打击,发誓好好看书,坚持三五天后,又去玩游戏了。甚至怀疑得了什么大病,发誓一万遍要爱自己,结果虚惊一场,没多少日子,又继续该熬夜熬夜,该混吃混喝继续混吃混喝了。
西门庆常在床笫之间问,你老公厉害还是我厉害?
这些,男人们应该很懂的。
西门庆身上的这些缺点,虚荣心,侥幸心,以及缺少自制,我们都可以随便对号入座,很多人想不接受都难,但是他们会提出来,假如我是西门庆,我不会那么淫乱。
假如你是个像西门庆这么有钱有权势的男人,而且很让女人喜欢,床技也属于高级水平,有得你挑,但凡你愿意,你真的不会做成他那样?有时候,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而且无须信誓旦旦保证,没到那个场景的保证都不可当真,人的情感变化是跟着处境变化而变化的。
《焚香记》里烟花妓女救了落难书生,恩爱三两年,他从没嫌弃她是妓女,等他高中状元,立刻嫌弃,而且回忆起她当年为了他在鸨儿面前鞭子挨都满面羞惭,他连过去的自己都嫌弃,哪里还不嫌弃那个妓女?
《金瓶梅》是一本讽刺小说,而且是非常高级的讽刺小说,能让人笑出声的同时内心充满了自省和恐惧,比如我站在他的位置上,我能比他做得哪怕好一点吗?
讽刺小说有两种,一种充满了优越感,比如钱钟书《围城》,看里面描写苏小姐,我敢说苏小姐的装模作样,一般人都不会想到自己身上去,因为太夸张,太失真了,这种讽刺停留在“一笑而过”以及感慨“钱钟书真是缺德”,仅此而已,格调不高。还有一种便是《金瓶梅》这种,看到人物的软弱虚荣的同时,联想到自己一身冷汗,但是前者更多人爱看,面对真实的自己,是件很艰难的事,而单纯嘲笑别人,就来得容易得多。
很多人不爱《金瓶梅》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以及人真实的来处与去处。
西门庆盛年夭亡后,旁人如何待他,他活着富贵的时候巴结他的朋友伙计女人都散了,也再没人提起他了,书里描写西门家伙计韩道国知道西门庆死讯的场景,如此轻描淡写,却令人发指。
这韩道国正在船头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得快,就过去了。
说话间,船行得快,就过去了,这不就像人的一生嘛,就那一下子,哪怕你万丈荣华,才高八斗,哗的一声,就过去了,转眼的事,一切烟消云散,世上再也没有人说起当年的旧事。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啊。死亡是人的极致恐惧,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不愿意想的,但是看《金瓶梅》规避不了。
《金瓶梅》中事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几乎可以说是古代小说中跟我们普通人最亲近的一本书,像《红楼梦》这种,它的确写得好,但是那些人,就不是我们身边轻易能见到的,跟阶层有关,跟高度理想化了也有关。
写着写着,我想起了个笑话。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小姨把我叫到她做生意的店里玩,说我看你平常开沙龙讲《红楼梦》也讲《金瓶梅》,你讲给我听看看,看我听得懂不?
这时候她店里来了个熟人,那女的就过来聊天,一进门就说她女儿嫁得多好啊,女婿多有本事啊,南京都买了几套房啊,讲个不断,听得人都恍惚了,这时候都快晚上十二点了,小姨只想收档口关门了,这女的还不走,最后又磨了好久,才起身,呐呐的说,那个谁,我手头有点紧啊,你看能不能先借一千块钱我过年,过完正月,我就还你!
后来我跟小姨说,这就是一出活生生的《金瓶梅》啊~
换到《金瓶梅》的场景里去,就是下面这一段了....
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与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晃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帐!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刚说在热闹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众人撮弄了,拴到铺里,明早要解县见官去。你还不早寻人情理会此事?”
韩道国正在店里吹嘘自己多厉害,西门庆多看重自己,混得有多牛逼,自己什么行为端正,立心不苟什么什么,结果有人跑进来通知他,哎呀,你还在这吹牛呢,你老婆和弟弟通奸被抓住了,正在游街.....
=======================================补充更一段=============
其实我没有认真的研究过《金瓶梅》,就随手看看,翻到哪儿是哪儿,但是每次都被作者逗笑。作者的性格在文本里体现一点都不奇怪,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每次结尾处的吐槽,比如曹雪芹借贾母之口挖苦才子佳人淫奔,而《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一种恶作剧一样的搞笑。
比如在书的第二十五章,开头就引用一首词。
蹴罢秋千,起来整顿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戋刂]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个开场词是李清照的,上片写女主人公下了秋千以后的情景,下片写主人公在来客忽至的羞赧情状,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天真纯洁、感情丰富却又矜持的少女形象。
作者一本正经的把这词引用起来,然后接下来就写西门庆的几个老婆去打秋千,打着打着,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就来了,接下来陈敬济就在底下帮几个娘推秋千,直推送得“李瓶儿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红底衣”。而打秋千飞起来了,无疑是个很有性意味的场景,而书里描写陈敬济的神态更令人绝倒。
这敬济老和尚不撞钟--得不的一声,于是拨步撩衣,向前说:“等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莲裙子带住,说道:“五娘站牢,儿子送也。”那秋千飞在半空中,犹若飞仙相似。李瓶儿见秋千起去了,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来送我送儿。”敬济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我慢慢儿的打发将来。这里叫,那里叫,把儿子手脚都弄慌了。”
打个秋千,陈敬济竟然会说出,都别急,等我一个个来,这个暗语就很值得玩味了。书里明写陈敬济跟潘金莲春梅都勾搭上床,以及后期调戏孟玉楼未果,跟宋惠莲搞做一团,一贯正经样的吴月娘,生了孩子后,陈敬济说了句,啊,这孩子像我不像?吴月娘一听晕了过去,这里作者留了个伏笔。
而在陈敬济来之前,吴月娘还说了句很搞笑的话,说她曾见谁家女孩儿打秋千打猛了,把处女膜搞破了,叮嘱大家小心点玩,这个简直太雷了,西门庆几个老婆,无论是潘金莲,还是孟玉楼,还是李瓶儿,里头没一个是处女。
这首词放在这个场景,简直要笑晕,几乎见到作者在书背后的那张微笑的脸,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装逼。
再比如第八回,潘金莲思念西门庆,开场的词。
红曙卷窗纱,睡起半拖罗袂。何似等闲睡起,到日高还未。催花阵阵玉楼风,楼上人难睡。有了人儿一个,在眼前心里。
这种类型的词并不少见,宋词里闺怨的词多了去了,比如,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等,跟上面这首也差不多意味。
问题是接下来的内容又瞎了狗眼,照一般的闺怨词,思念什么呢?思念真情和爱情。而潘金莲思念西门庆干嘛呢?思念他的淫欲无度,书里写潘金莲初次跟西门庆通奸的时候,说是先前霸占她的张大户老儿软鼻涕的有什么用处,武大郎那三寸丁又有何用处,如今跌落到了西门庆手里,哪里不痛快呢?到了给武大郎做法事,两个人还在庙里瞎搞。
在中国文艺作品里经过浪漫化了的抽象的东西,《金瓶梅》作者全部要它还原,对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有一种恶作剧的玩世不恭,类似于我就是拆穿你的孩子气。
很多人拿《红楼梦》跟《金瓶梅》比,其实这是不了解《红楼》,也不了解《金瓶梅》,虽然《红楼》借鉴了《金瓶梅》的部分描写手法,但是两位作者想说得根本不是一个东西。《红楼》还是有些许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而《金瓶梅》的作者,他只对真实的人生有兴趣,根本不打算做什么浪漫理想主义虚构,可能他根本看不上理想主义那一套,看他对《水浒》的改编就知道了。
《红楼》比《金瓶梅》更深入人心的地方在三点。
第一,语言。《金瓶梅》的方言很浓,我可以断定,能看下《金瓶梅》全本书的人,再看《红楼》的语言简直是小CASE。第二,《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让人当做淫秽读物,大大的影响了其客观的文学价值和传播途径。第三,《金瓶梅》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力作,其中描写的真实的人性,很多人根本发自内心的接受不了,而对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充满了留恋。
PS:那《红楼梦》一书真的写得好吗?我的回复《红楼梦》真的很棒吗? - 何日君回来的回答 - 知乎
==============================第三次补充====================
针对评论里某些只能看到金瓶梅丑陋的人....我有话说...
有些人认知范围里的丑和美都很单调,绝对化,但凡涉及一点深刻复杂的东西,他就理解不了并对此进行抨击。
我记得韩寒说过《大话西游》拍的好是因为朱茵的一滴泪,假如是周星驰的一滴泪就只有搞笑了。然而,周星驰其实流过一滴泪,在电影《审死官》里。这一滴眼泪,就可见周星驰的牛逼。
这滴眼泪是怎么来的呢?是影片前面周星驰贪财接了个案子,故意害人,打赢官司收了钱后流出的一滴眼泪。
这滴眼泪,当然是嘲讽,但是为周星驰后面为正义救人而打官司埋下伏笔,这个坏人才有了转化为好人的可能,不是天生是恶人,只是顶不住钱财诱惑而已。
因为有了这滴眼泪,人性的复杂就出来了。


再比如电影《甜蜜蜜》,黎小军跟李翘几次做爱的镜头,都是切换镜头,这分钟的黎小军在碎碎念,小婷,你好,我正要给你回信,下一个镜头便滚到李翘床上睡觉去了,假如没有这挂念未婚妻的镜头切换,黎小军就是个死渣男,不具备人的属性。
人,并不是简单的美与丑,真与假的呆板组合,而是在欲望的浮浮沉沉里的千姿百态共同组成了真实的人类。
《金瓶梅》就是这种深刻人性文学作品的典范。
最典型的是宋惠莲。
宋惠莲先是嫁蒋聪,蒋聪给人杀了后,改嫁来旺儿,跟了来旺儿又跟西门庆勾搭。这个妇人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
潘金莲怂恿西门庆害来旺儿,发配徐州,宋惠莲不让,最后闹着上吊,第一次没死,竟然还上吊了第二次,死了。
宋惠莲肯定不是爱来旺儿,更不是忠贞,连西门庆都认为她闹着要死是吓唬人,这个小淫妇哪里会为来旺儿死?
孙述宇先生说得好,宋惠莲选择死,一是跟潘金莲斗输了,彻底知道自己在西门家的地位了,二的的确确是为了来旺儿死的,哪怕不是爱他,就是底层的人对同样底层的人一种同情和痛惜感,她心里还有正义在,故而决然选死。
书里有这样的描写:
这妇人不听万事皆休,听了此言,关闭了房间,放声大哭道:“我的人!你在他家干坏了甚么事来?被人纸棺材暗算计了你!你做奴才一场,好衣服没曾挣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当把你远离他乡,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晓得?”哭了一回,取一条长手巾拴在卧房门枢上,悬梁自缢。
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死,须不知好多一世忠贞的女人都不如这淫妇决心大呢!
这就是《金瓶梅》的艺术,你能说它是丑恶的吗?
我喜欢《金瓶梅》是因为我理解它描述的世界,宋惠莲这种人我生活中见到过。
我们县城厂里有个女人出去打工,工厂流水线辛苦做事,挣那么两三千块寄回家,留下老公一个人在老家当老师。这男的老婆不在旁边,忍不住偷吃,很快跟个年轻的女人勾搭上了。
等他老婆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本来一直是个暴躁脾气,没出这个事前,就骂老公跟骂孙子一样的骂,这下暴怒,要离婚,赶他走,这男的最开始还不愿意离婚,到处请人给老婆做工作,这女的坚决不肯,把老公衣服全部烧光,把他全家祖宗十八代挂上嘴骂,这男的要回来睡,她就把他的床竖起来,不让他在客厅睡。最后这男的被逼急了,就索性不回家了。
这么过了十几年,老公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又有了孩子,这女的没结婚了,独自带着女儿,后来查出来了得了胃癌,孩子在外面读大学,父母都垂垂老了,没人照顾,这男的就跟现在的妻子商量好了,就搬到前妻这儿日夜不停的来照顾,这女的得病痛苦加极度怨恨,每天恶骂这个男的,骂的整个厂里都知道,这个男的就任凭她骂。
后来这女的落气前一天,痛的床上打滚,前夫就找医生来跟她打针,医生就说这个血管死了,针也打不进去了。这女的抱着前夫哭,说让他送她去医院,救她一条命,这个男的就哭着说,医院说救不了,你就安心去,孩子我照顾,会热热闹闹出嫁的,她没有妈妈了,还有爸爸和阿姨,有姨妈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热闹的。
这女的最后说,想吃个梨子,这男的去切梨子,女的拿着梨子跟他说,今天跟你半世夫妻到头,永远分离了,从前的事,你的错,我原谅你了,我的错,也请你多担待些。
我朋友,也就是他们的女儿后来红着眼睛跟我说,那个生死离别的场景真是,肝肠痛断,过了十年二十年再提,还是泣不成声。
普通的人们,很难做到白璧无瑕。
漫长的一生里,凡人总有些不好处,也总有些好处,千日不好也总有一日好。多多担待以及珍惜,这句话原是这个意思。
人之所谓成熟,很大程度上,是更真切的体会到了这个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的世界。
有的人因为运气特别好,终生不染尘埃,爹妈保护好了爱人孩子接棒,故有善良秉性,而有些人,看透了人心,还是有慈悲心,这种善良秉性,更是难得。
前人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
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
微信公众号:何日君回来
真没觉得不尊重女性……我反而觉得这书对女性的态度是很多现代人也没有的。
举个例子。
第十二回里,西门庆贪恋妓女李桂姐,住在院儿里久不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不久便与小厮琴童勾搭上了,偷了情,是真偷——“知道西门庆不来家,把两个丫头打发睡了,推往花园中游玩,将琴童叫进房与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上房门,褪衣解带,两个就干做一处。”“自此为始,每夜妇人便叫琴童进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发出来。”
某次被起夜的丫鬟秋菊发现,便传到了与金莲有仇的孙雪娥和李娇儿耳里,两人便在西门庆归家之日跑去告状。
西门庆知道后自然大怒,把小厮狠打了一顿逐出府内,勒令金莲脱了衣服跪着拿鞭子抽了一顿,之后因小厮与金莲都抵死不认,“又见妇人脱的光赤条条,花朵儿般身子,娇啼嫩语,跪在地下,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也就作罢了。
金莲这一番受辱,究其原因,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是完全活该的,甚至我一个现代人在看这段的时候,因为个人不待见潘金莲,看见西门庆轻易就放过了她还隐隐有点失望。
而作者在写完这一段之后,又加了两句评语。
我以为会是说金莲自作自受,或者批评她如何淫荡之类。
但书中写的是——“潘金莲平日被西门庆宠的狂了,今日讨这场羞辱在身上。正是: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补充:刚查了一下发现这句是引用了白居易的诗,不过我的重点倒不在这诗是写的还是引用的,重点在它出现的位置和所评之事。
近期又读了一遍金瓶梅,然后带来了很多思考,兰陵笑笑生下笔直接深刻,把人性热乎乎血淋淋的抛开直接丢给我们看自是一点,但是今天想说的是人物和情节的设置。堪称小说创造的一绝
首先想说的是小潘和春梅,对了后面还添加了惠莲
我们看,小潘的背景,出身贫寒,颇有姿色,被卖到在大户之家做丫头,主子那排人教她学弹唱,然后被主子收了,这前期被作者一笔带过的经历,是不是活脱脱一个西门府的春梅?
在看看春梅,因为大户人家一些不可说之事,被主母容不下,踢出来嫁人,是不是跟小潘的开头完全重合?
然后无一例外的,这俩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淫妇,做丫头的时候跟主子通奸,嫁人后老公活着的时候跟人通奸,老公死了之后做了寡妇继续跟人通奸,而且都跟本书的男主西门庆和陈经济发生过肉体关系,对还有仔细看惠莲出身也是一样的。
拍案叫绝的是,兰陵笑笑生,在每个他们的人生转折,都给出了不同的走向,就如一面镜子,照出来了彼此人生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可是最后不管这几个人的经历多么不尽相同,结果却都是一样的殊途同归
小潘被张大户收用了,因此淫情,主母容不下,最后被踢出来嫁人去了
春梅被西门庆收用了,月娘也对此没有问题,她成功地留在了西门家,仗着西门庆的宠爱,春梅也有过风光的日子,可是西门庆一死,她还是因为淫情为主母所不容,最后被踢出来嫁人去了
小潘被赶出来之后嫁给了武大郎,说自己一块好羊肉,掉到了狗嘴里,迫切想要找个配得上自己的男人,于是他先勾引武松,后通奸西门庆。
春梅被赶出来之后嫁给了周守备,算是好归宿了吧,可是她还是要先勾引李安,后通奸周义
小潘在西门庆府上,为了西门庆的宠爱和孩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她求神,喝尿,床上百般迎合奉承,拉拢春梅、以及前期的宋六儿,迫害李瓶儿母子,可是好像不管怎么折腾就是逃不开所求皆不得的结果,刘婆子他老公做法,还叫西门庆收用了春梅,可是没有多久李瓶儿就怀了孩子,完完全全成了西门庆心尖尖儿上的人,她设法折腾死李瓶儿母子,两次小月后小潘跟王姑子求来胞衣,没想到西门庆的死期早于第二个壬子日。这中间,她由于寂寞通奸一个眉清目秀的十几岁少年郎(琴童),半是感情半是欲望的通奸于陈经济
春梅在守备府上,轻松得到了小潘想要的一切,啥都没有干,守备喜欢她尊重她,她要干啥守备也都依着(参照打孙学娥那段),嫁过去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甚至连小潘都没有敢想的正房奶奶身份也有了。可是她还是半是感情半是欲望的通奸陈经济,出于寂寞和一个十几岁眉清目秀的少年有一腿(周义)
小潘在西门府跟两个奸夫通奸皆被丫头告发,前一次挨了打,后一次被主母容不下,赶出来了,不能继续守寡,然后辗转嫁给武松,被武松剖腹挖心不得好死
春梅在周府跟两个奸夫通奸丫头见了奸情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自己已经是了主母,不存在容不下的问题,可以继续守寡,可是最后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一样的没得好死
另外一个宋六被赶出来后,辗转嫁的既不是小潘这种一块好羊肉掉到狗嘴里里的武大郎,也不是如春梅这样毫无选择的被卖,而是跟她情投意合相当登对的来旺儿,相对于小潘的狠毒和春梅的目下无人,惠莲可能反而善良一些,可是最后呢,比她俩谁死的都早,还搭上了家人
然后都理出来对比来看,叫人唏嘘,我们终于明白如小潘,春梅以及惠莲这样的出身贫寒,颇有姿色且欲望强烈的女性,在那个社会,不管人生如何兜兜转转,在那个社会的状态下,不得好死是逃不开的命运,每每思考至此,总要一边叫着兰陵笑笑生下笔过狠,一边感慨他的悲悯之心
然后还有一处对比,便是春梅和西门庆
其实仔细看大轮廓,春梅简直就是一个女版的西门庆
西门庆发家于娶亲,孟玉楼,李瓶儿两个寡妇嫁进来带过来的财富叫他有了向上走的资本
春梅发达于嫁人,嫁了周守备生了儿子守备原配在一死她便顺利成长的成了堂堂守备夫人
西门庆发达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自己纵情声色,着实一段好时光
春梅发达后也是随着周守备几次升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自己纵情声色,着实一段好时光
他俩都死于淫,而且死状都极其相似
西门庆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将出来,犹水银之淀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咽不及,只顾流将出来。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
春梅不料他搂着周义在床上,一泄之后,鼻口皆出凉气,淫津流下一洼口,就鸣呼哀哉
最神奇的是,笑笑生在春梅淫情上着笔不多,却安排她在本书最荒淫的场景处处在场做见证人,前有葡萄架,后有3P, 而这些事情闹出来的后果春梅也一次没落下的全部参与,比如说葡萄架下小潘差点丧命,比如说西门庆濒死,比如说小潘打胎。可是当她有朝一日翻身做主,有能力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丝毫没有被之前看过的血淋淋的事实所震慑而有所收敛,而是如西门庆一般,纵情声色之中,成了欲望的奴隶,最后沿着西门庆的轨迹,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把自己作死
笑笑生写金瓶梅,说到以淫止淫,但是其实,笑笑生更清楚,这以淫止淫并起不到什么作用,芸芸众生,恐怕大多都是庞春梅,虽然前面有着血淋淋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当拥有了能满足欲望的权利的时候,还是将这一切抛之脑后,奋不顾身一头扎进自己的欲望之中,最后反而被自己的欲望所支配,然后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西门庆的故事,人啊,哪儿有什么前进,不过是在轮回罢了
好懒,今天不想写了,有人看的花在更新,想写写小潘和陈经济,小潘与武松还有王六和小叔
公众号,岁月冢,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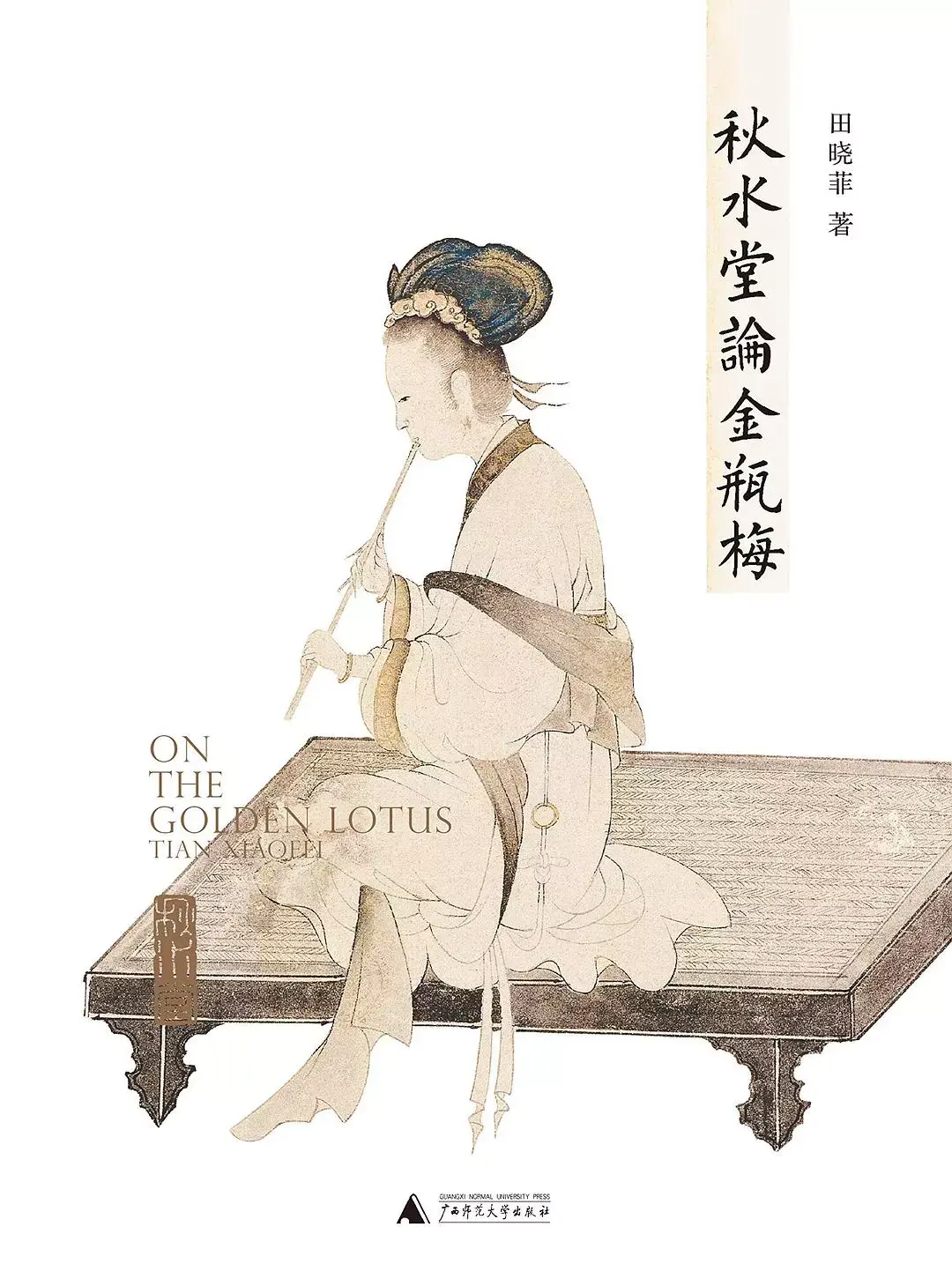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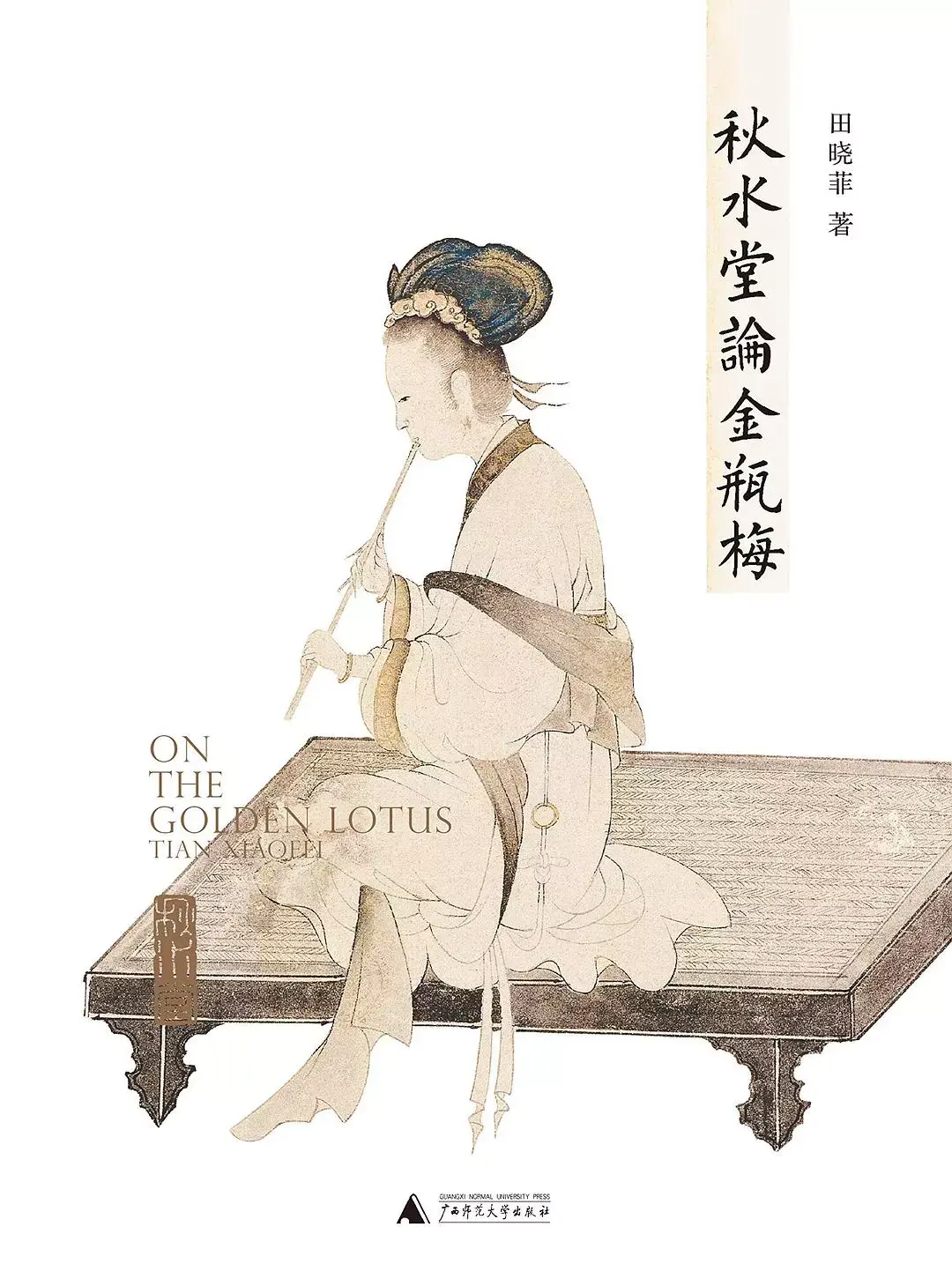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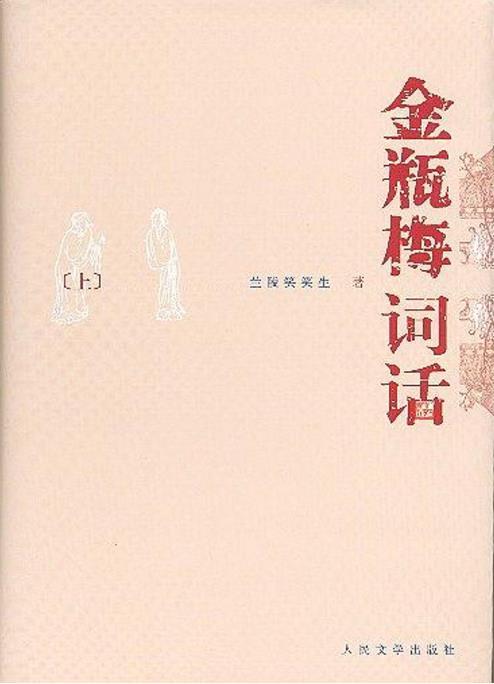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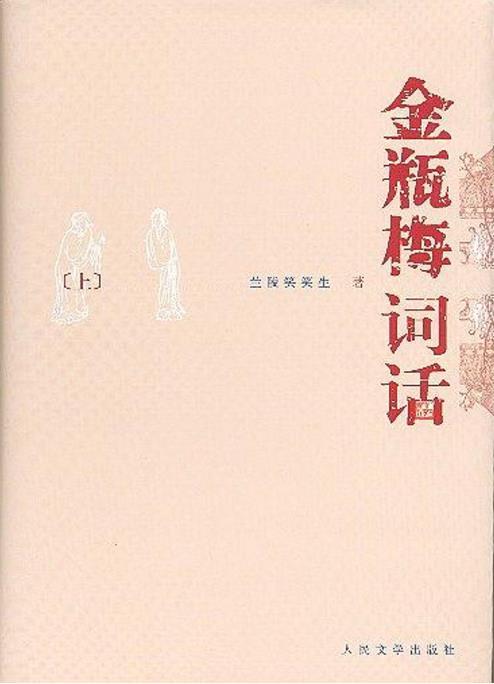
刚刚写完一部书的感觉,好像失恋:不甘心这么就完了,怎奈万般不由人。
《金瓶梅》里面卜龟儿卦的老婆子,对李瓶儿说:奶奶尽好匹红罗,只可惜尺头短些。这样婉转的比喻,我很是喜欢。但是红罗无休无尽,也未免惹人嫌,除非家里是开布店的,像孟玉楼的第一任丈夫那样。
《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男男女女,林林总总,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写得花团锦簇的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我知道倘使在现实世界里面和他们遇见,打起交道来,我是一定要吃亏的。现在,他们被局限在书里,在我从小便熟悉的文字里,我可以爱得安心。
而且,现实生活诱人归诱人,却是混乱无序、万分无奈的。我并非悲观主义者,我其实相信只要人诚心地、坚持地祈求,神是会得赐予的;然而,我也知道,那得到的方式、过程与结果,却往往是“出乎意表之外”的。
但是在小说里就不同。一部好的小说,从开头第一个字到结尾最后一个字,都犹如一匹红罗上的花样,是精心安排的。《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结局再凄厉,也有一种对称的、均匀的美感,好比观看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缎子上的花枝,因为是绣出来的,折枝也罢,缠枝也罢,总之是美丽的,使人伤感,却不悲痛的。
我从来不愿意买花插瓶,家里有鲜花的时候,往往是朋友送的(虽然看了下面文字的朋友,大概也断不肯再送我花了吧)。因为,姹紫嫣红的时候,固然是热闹惬意的,但是枯萎凋谢的时候,却拿它怎么办呢?学林黛玉葬花罢,也太肉麻了些,说来惭愧,只有把它扔进垃圾桶了事。我因此不愿买它,不愿插它,不愿想它凋残之后的命运——古诗不是说“化做春泥更护花”么,但这也是只限于文字的美,因为现实中的春泥,是令人难堪的。
像金莲死于武松的刀下,瓶儿死于缠绵的恶疾,两个美色佳人,死得如此血腥恶秽,就是在文字中看到,也是惊心动魄的,更哪堪在现实中亲眼目睹呢。
我常常记得,读大学的时候,一位教中国文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皱着眉头,待笑不笑,用了十分悲哀无奈的调子,对我们说:《金瓶梅》,是镇日家锁在柜子里面的,因为,孩子还小啊。话甫出口,全体学生哄堂大笑了。
那时,我早已看过《红楼梦》不知多少遍,却没有好好地看过一遍《金瓶梅》。不是家里没有或者父母把它锁起来(何况我是最善于找到父母藏起来的书柜钥匙的),而是根本懒得看:打开一翻,真个满纸“老婆舌头”而已,而那些被人们神秘化的记述做爱的段落,没有一点点罗曼蒂克,在一个追求浪漫、充满理想的少年人眼中,无异罗刹海市——虽然,不是《金瓶梅》,而是有些人对待它的态度,令我觉得真正的污秽和厌倦。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也已接近而立之年,也成了大学老师了。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备课、做自己的专业研究之余,我打开一套绣像本《金瓶梅》消遣,却没有想到,从此,我爱上金瓶。
金瓶是“成人小说”。三X级的,这没有错。亦有很多性虐狂描写。但我说金瓶乃“成人小说”,却并不是因为它描写做爱之坦率,而是因为它要求我们慈悲。
这种慈悲,一心追求纯洁与完美的少男少女是很难理解,或者几乎不可能想象的,因为慈悲的对象,不是浪漫如曼弗雷德(拜仑笔下的悲剧英雄)的人物,而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陈敬济,甚至,那委琐吝啬的吴月娘。唐璜那样的浪子,还有其颓废的魅力,而西门庆,只是一个靠了做生意起家、官商勾结类型的俗人而已。
现下的金瓶版本,多是洁本,想是为了“孩子还小”起见,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大众读者。然而用禅宗的眼光看来,那心中有洁污之分别者,还是被所谓的污秽所束缚的。其实一部金瓶,不过饮食男女,人类从古到今,日夜所从事着的。这又有什么污秽可言呢。
如果抛掉自欺,哪一个女人,没有一点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孟玉楼或者庞春梅的影子?而今的时代,原也不少西门庆——得了利还想要权与名,被嘲为粗俗,但也不乏实在与(在女人面前与眼里)憨傻的男人;更不少陈敬济,那生长在父母宠爱之内、锦绣丛中,混帐而其实天真的青年。
人们往往不喜欢金瓶后半部,觉得西门庆死了,小说变得苍白,似乎作者忽然失去了兴趣,过于匆忙地收尾。其实我想,真正的缘故,大概还是很少人耐得住小说后半扑面而来的灰尘与凄凉。小说有七十回,都是发生在西门庆的宅院之内,一个受到保护的天地;从七十九回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广大而灰暗的世界,有的是乞丐头、泼皮、道士、役夫、私窠子。小说中写李瓶儿做爱喜欢“倒插花”,然而倒插在瓶中的花,它岂不是白白地娇艳芬芳了吗?瓶儿的先夫名叫花子虚,花既然是“虚”,瓶儿终究还是空空如也。《金瓶梅》的作者,很喜欢弄这些文字的花巧,他写一部花好月圆的书,最后才给我们看原来无过是些镜花水月而已。
又有人说:《金瓶梅》没有情,只有欲;没有精神,只有肉体。这是很大的误解。是的,《金瓶梅》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反省自己的自知自觉,这没有错;但是,小说人物缺乏自省,不等于作者缺乏自省,不等于文本没有传达自省的信息。《金瓶梅》的肉体与灵魂,不是基督教的,而是佛教的。《金瓶梅》的作者是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够成为菩萨。
据说,观音大士曾经化身为一个美妓,凡有来客,无不接纳,而一切男子,与她交接之后,欲心顿歇。一日无疾而终,里人为之买棺下葬。有一胡僧路过坟墓,合掌道:“善哉。善哉。”旁人见了笑道:“师父错了,这里埋的是一个娼妓呢。”胡僧道:“你们哪里知道,这是观音见世人欲心太重,化身度世的。倘若不信,可以开棺验看。”人们打开坟墓,发现尸骨已节节化为黄金。从此起庙礼拜,称之为“黄金锁子骨菩萨”。
这个故事,我一直很喜欢。其实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救度世人,看来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能依靠美色与魔术。取得世人的虔信,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有把尸骨化作黄金。财与色,是绣像本《金瓶梅》最叹息于世人的地方,而就连观音大士,也只好仍然从财与色入手而已。
不过这个故事只提到超度男子,没有提到超度女人。欲心太重的女人怎么办呢,难道只好永远沉沦,或者祈祷来世化为男身么?这是我喜爱《金瓶梅》——特别是绣像本《金瓶梅》——的又一重原因:它描写欲心强烈的男子,也描写欲心强烈的女人,而且,它对这样的女人,也是很慈悲的。我请读者不要被皮相所蒙蔽,以为作者安排金莲被杀,瓶儿病死,春梅淫亡,是对这些女子做文字的惩罚:我们要看他笔下流露的深深的哀怜。
屡屡提到绣像本(也就是所谓的张竹坡评点本),是因为它与另一版本词话本,在美学原则和思想框架方面,十分不同。我写这部书,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版本的比较。但是,最初促使我动笔的,只是喜欢:就像恋爱中的人,或者一个母亲,喜欢絮絮地谈论自己的爱人,或者孩子,多么的好,多么的可爱。不过,被迫聆听的朋友,未免要心烦;写书就没有这一层顾忌:读者看厌了,可以随时把书放下,不必怕得罪了人。
另一件事,想在此提到的,是《金瓶梅》所写到的山东临清,那正是我的原籍。明朝的时候,临清“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是有名繁华的大码头。研究者们有人认为《金瓶梅》使用的是齐鲁方言,有人认为不是,个个证据凿凿,却也不能一一细辨。我只想说,我的父母,一鲁一豫,家乡相距不远,他们虽然因为从小远离家乡,都只讲得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但是时时会说出一些词语来,我向来以为是无字可书,也只隐约知道大意的,却往往在读《金瓶梅》时骤然看到,隔着迢迢时空,好像在茫茫人海中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令我又惊又喜一番。望着墙壁上祖父祖母的遗像,我常常想回临清,祭扫先人的坟墓,无奈还一直不能如愿。爱屋及乌,把追慕故乡的心意,曲曲折折地表达在对这部以山东清河与临清为背景的明代巨著的论说里。这是我想告诉本书读者的,区区的一点私心。
我祖籍不是天津,也不生在天津,但是,我长在天津。记得小时刚刚搬到天津,我总是称自己为哈尔滨人。现在,身居异国,真没有想到一住就是十二年。古人有诗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思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浮屠桑下不肯三宿,唯恐产生眷恋,我虽喜爱释教,却不是比丘尼,更何况天津是我从小生长了这么多年的城市呢。每次回家,我都喜欢感到踏在天津的土地上,喜欢打起乡谈,和出租车司机们攀话,喜欢听街头小贩们贫嘴和“嚼性”(又是只知有音而不知如何书写的方言)。感谢王华编辑,使这部关于金瓶的书,能够在天津出版,使我天津的父老可以先睹为快。人的故乡,不是只有一个的。
谢谢我亲爱的父亲与母亲,对我的爱与支持。感谢我深爱的丈夫宇文所安: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他听我激动地讲说,和我热切地讨论,最后,又为这部书写序。没有所安,是不可能有这部书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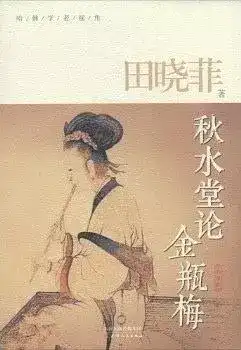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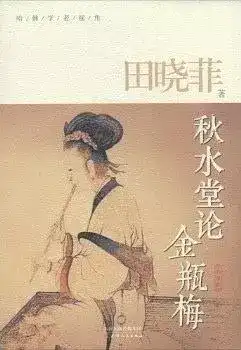
在旧人看新历之际,这部旧书也喜得新版。想2001年1月开始动笔写作此书,距今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当年逐日逐回评点金瓶,自娱自乐,百天足成百回之数,原未把它当成一部书来写。时至今日,因审阅再版校样而重读全书,觉得这真是自己写得最放荡自恣的文字,留下了许多自我沉湎的痕迹。多年来承编辑谬赏、读者厚爱,感愧交心。
审阅中,有时欣慰,有时惊讶,有时觉得书中一些观点,还可以剖析得更深入或全面。但我无法重新来过,也不想重新来过。时过境迁,无论工拙,这都是一本今天的我已经再写不来的书——对书、对作者来说,这都是好事。
又想到这些年来,凡涉及文章学术,哪怕多么德高望重的前辈,我都固执己见,从未因其年长位尊而假以词色。这样的性情态度,在重视爵齿而且小视女性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学术圈里,诚为一弊。曾蒙良朋相劝,无奈本性难移。因此,在这里,特别想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教授(1933—2016)。我们素不相识,但2006年3月14日,突然收到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Dear Tian Xiaofei,
I have just finished reading your book on Jin Ping Mei, and wante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was impressed by it.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differ on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text, I found your exegesis, chapter by chapter, utterly fascinating. What you have to say about the author's artistry 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rhetorical devices by which he achieves his effects is consistently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ing. I enjoyed it more than any other book I have read on the subject. In conclusion, let me say that I hope you will consider bringing out an English version, since 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valuable companion to anyone reading my translation.
Yours admiringly, David T. Roy
“此致 田晓菲:
我刚刚读了你评《金瓶梅》的书,想告诉你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对这部小说两个版本之优劣你我观点并不一致,但我觉得你的逐回评析非常动人。你对于作者的写作艺术以及他借以达到其效果的精湛修辞技巧的分析,总是富有洞见、烛照幽微。阅读此书给我带来的乐趣,胜于我读过的任何其他相同主题的著作。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我希望你考虑出一部英文版,因为我认为它对任何阅读我的译著的读者都会是宝贵的姊妹篇。
心怀赞赏的 芮效卫。”
芮教授穷三十余年时间精力,翻译并研究《金瓶梅》词话本,我却是绣像本的热烈拥护者,更在此书中几次明确提到和他意见不同。芮教授不但不以为忤,还给一个比他年轻近四十岁的作者写来这样一封信。在此抄录书信全文,是因为电子邮件远比竹木纸帛更为脆弱,故希望借此书一角,保存这一令我感动的文本,也让读者看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坦荡胸怀。此书新版,谨献给对芮效卫教授的记忆,对他诚恳亮直的风范表示敬意和怀念。只是自惟这样微末而又迟到的手势,不能烛照幽冥,其于亡者何有?天地悠悠,天寒地冻,良独怆然。
感谢理想国张旖旎编辑倾心支持、高晓松先生主动作序、以及许多年来许多读者的热情关爱。我不过是一个拨云探月人而已。一切的好,都须归于这部世界小说史上犹如沧海明月一般横空出世的奇书。
秋水堂主人2019年1月识于马省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