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大鹏导演的电影《吉祥如意》?
一位喜剧片导演突发奇想,回到东北农村老家,希望将一家人如何过年拍成一部文艺电影,结果遭遇一系列意外。因拍电影而聚齐的家庭成员们,完成了最后的聚会。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在疫情后诞生的国产新片,它在上周日(7月26日)于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因为只有一场放映,看过的人并不多,一天后,电影仍在小范围内被大家议论着,豆瓣98人打分,其中29人打五星,62人打四星,7人打三星,暂无两星或一星(截止7月27日晚18:00)。

一个年度十佳无疑,甚至有冲击三佳片潜力的华语电影。
故事呢,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一个纪录片形式的剧情片,讲述一位北漂女人丽丽(刘陆 饰)时隔多年回到东北农村老家过年,面对自己身患脑炎后遗症的父亲(王吉祥 饰,现实中导演的三舅),以及庞大家族在长辈突然去世后的现实纷争。除女主角外,全部由真实人物出演。人物性格极简又极端,高潮场面一度激烈到无法收场。
而后半部分,突然转换为一部纯纪录片,呈现的是前半部分剧情片的拍摄过程。主角,从残障老父与女演员扮演的女儿,转为本片导演、现实中的女主演以及女主角的原型真身,三个人互相“试探”,让之前的剧情片被重新解读。真假虚实里,能看到与我们生存状态相似的中国式情感困境。
至亲的长辈真实地离去,不可逆转,女演员竟无声承担着本该由原型人物承担的痛苦,荒诞又不违背逻辑。
仅仅简单描述这种故事结构,就能感到这部片子,这电影有智力的成分,更有当事人敢于暴露自己伦理疑点的勇气,以及一个人类,即导演本人,用影像与不幸命运的扭打。
电影里的情感,高度浓烈,近年来从未见过,以拍摄时间轴来看,它的理念又要早于同类电影《摄影机不要停》一到两年。
前半部分,导演耗时一年多剪成48分钟短片,已在金马奖斩获最佳荣誉。
剩下累计80多小时素材量,导演继续苦(哭)剪两年,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真实摄影机拍摄的真实的死亡,甚至需要看心理医生以调适自己,才最终完成这部75分钟的长片。
听完这番描述,你会说,这导演是一行为艺术家吧?这是一实验电影吧?
短片,叫《吉祥》,也就是导演他三舅的名字;长片,多两个字,叫《吉祥如意》,这是导演12年前北漂时代带回村里的春联。

而导演,叫大鹏。
等一下,董成鹏大鹏?
对,就是《屌丝男士》《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的导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为他披上“投机分子”、“耍小聪明”、“说话也不逗笑了”标签的大鹏。
做这场采访,果然有人在我微博下留言——“大鹏也把你唬住了?”“他利用反投机又投机了一回。”
那说真的,看这部电影之前,你很难相信,大鹏是一个这样的导演。
就算看了,你也很难在短时间里理解,大鹏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导演。
即便我从不轻信那些标签,我也感到自己一直“误会”了大鹏。
电影,好像并不是他成名路上的驿站那么简单。
第一导演在《吉祥如意》上影节放映当日,听到了大鹏在电话那头努力镇定情绪的声音。
整整一个小时,这是大鹏完成这部电影后,第一次敞开心扉,从头至尾,坦诚创作。
“当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亲人,向前爬,向前爬,我当时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打击,但同时因为剧组正在拍摄,你作为导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溃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种压抑,无法发泄,这件事让我非常受困。”
“你问我有没有内伤?有,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金马奖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妈哭得跟王八犊子似的。到现在咱俩对话的此时此刻,我也没有真正过了这个坎儿。”
这里隐藏着一片惊人的情感沼泽。
就算你绑着绳索,靠近了,也可能深陷其中。
【本文涉及剧透,追求观影体验者,建议等未来影片正式上映后再看本专访,到时候找不到本文也无关系,现在,这篇专访必须出现,必须存在】
 大鹏(左)
大鹏(左)
这是我为《吉祥如意》这部电影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也是我第一次分享这部电影的创作。此前,我和剧组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因为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电影的周期可能会拉得比较长,所以大家不对外提及这部电影。
这一弄就是四年,我们从头说。
2016年,我决定要做这个事的时候,电影的结构就是被确定了的,我是非常明确地要做一个你现在看到的《吉祥如意》。
它有两个剧组,一个剧组要拍《吉祥》,另外一个剧组拍我怎么拍《吉祥》,也就是《如意》。
两个组的导演都是我,加上刘陆,一共39个人,其中5个人是司机,所以实际投入拍摄是34人。这34个人,分成两个组,一组拍一个片,这两个组是独立的、不同的摄影团队和录音团队。
一开始,主角就是我姥姥。
甚至这个电影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姥姥》,我们现场的场记板,还有档案,写的都是《姥姥》剧组。一直到《吉祥如意》明天要在上影节首映了,我们这个习惯可能都没改掉,微信群还是叫“《姥姥》摄制组”。

前几天上影节入围的消息给到我,我就在原先摄制组群发了这个消息,那个群里39个成员一个人没走,我还挺感动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要去拍我的姥姥,也许会让你有些意外的是,最一开始,刘陆演的是我。
 刘陆
刘陆
我跟刘陆说,我跟我姥姥的情感非常深厚,这一次我想回家过年,就想拍一下我姥姥她怎么在年三十过春节的故事。
因为我不希望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纪录片,如果是纪录片,那应该是我跟我姥姥过春节的故事,所以我一开始确定它的格式,它就是一部用纪录片语法来拍摄的剧情片。
我说刘陆你来演我,演一个从大城市北漂回到了东北农村老家的一个外孙女。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男性而是一个女性呢?
因为我希望能够探讨的议题就是,我姥姥这样一个在农村照顾她傻儿子一辈子的一个女性,和一个跟她隔着辈份,从小被她拉扯大,同时又北漂,有很多压力的女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话。这是我最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的初衷。
刘陆她很负责,她说我没有相关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没这么拍过电影。也许我们的眼界比较狭窄,至少在我们的目力范围之内,很少有人这么做。
她问我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是浸入式地进入到这个家庭,成为我,你去替我跟我姥姥相处。所以刘陆比我们早到了农村,然后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而那个时候,所有剧组成员正在集安筹备《缝纫机乐队》的拍摄。计划中,拍摄《姥姥》是从小年那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三,拍摄周期10天。
没想到的是,当剧组抵达现场的时候,姥姥突然病重,陷入昏迷。
也就是说,刘陆,其实替我见到我姥姥最后一面。
但我没有见到。

 大鹏在片场
大鹏在片场
我觉得我们拍了一场天意,发生什么就拍什么,只是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内容。
那天腊月二十三,全剧组都在这了,所有的人、器材,都在现场。
我坐在昏迷的姥姥旁边,很无助、很难过、真的很痛苦,我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如果天意是我回到家,看到我姥姥躺在床上,那我也想把这个事情继续进行下去。
我就从医院出门走到楼下这段时间,做了这个决定——现在,我回剧组,大家一起来开一个会,我们改变方案,刘陆,也会有她新的角色。
我们转而去捕捉另外一个事,也就是姥姥的三儿子,我的三舅。

 三舅
三舅
那么这个时候刘陆还演我,这组关系就不成立了,因为三舅和我的关系,并不像姥姥和我的关系一样那么有故事可以发生,所以我就跟刘陆商量,我突然想起来,三舅有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女儿,叫丽丽,但是她已经离开这个家庭很长时间了,她十年没有回来这个地方,正好因为她回不来,没有这个人,那你就把她的位置补上。
你,来变成她。
这绝对是一次意外,我们不得不做出的调整。
剧组当时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对于观众来讲,拍摄前更改拍摄对象对观众最终观看没有实际影响。我很感激我的剧组,虽然我们拍的这个东西有一些实验性,大家没见过,我们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去应对,但是剧组都相信我,都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当我提出新的变化时,大家都在想怎么去执行。
另外,我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来源于我对这个家庭的了解。因为我每次回家,我看我姥姥的时候,都会听到类似的讨论,也就是说,姥姥跟三舅关系这么粘合,那随着姥姥年纪越来越大,三舅怎么办呢?他到底是去敬老院,还是待在某一个兄弟姐妹的家里?又或者是被他的女儿丽丽接到大城市?
大家其实关于三舅的讨论,我是目睹过很多次的。我们极有可能会拍摄到一家人有关于三舅未来去向的某一种讨论。
三舅这个人,从小是整个家族里条件最好的,姥姥把大部分的钱用来供他上大学,他也不负重望,找了一个好工作,一个油田的保卫科科长。
在他是油田保卫科科长的时候,我们其他人还都在农村种地,他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遇到了不幸,成为我们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反复看他,发现他像一个诗人。
他不是主动想要写诗,因为他的心智让他不停地重复着一些看上去毫无意义和关联符号性的内容,比如说“文武香贵,一二四五”,“我18岁当兵走了,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明天找妈”……他反反复复在低吟的这些密码,其实都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他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但是他被困住了,被困在他的那个身体里了,他每天都在重新拾起记忆,每天早上起来依然要找妈妈,都要再接受一次失去母亲的这个痛苦信息,就像第一次听到一样。
我曾看过他的辉煌,但现在,这是他的循环。
那从我个人来讲,这些年能够出钱,能够出力,能够帮忙解决的问题,我都冲锋在前了。可是,那个三舅回不来了。
我心疼他。
我迅速做出决定,第二天,开机。
谁知道,突然,三舅的女儿丽丽就回来了。
首先,丽丽突然出现在现场,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我尝试着去思考了一下她的心态。当我们决定开始拍三舅,让刘陆扮演丽丽的时候,刘陆提出来,她要知道丽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日常接触到丽丽的一些侧面。因为丽丽在北京,我也在北京,有时候我们会见面,会聊天,我大概知道她生存的状况。
在这一层面,我当然希望电影能够拍得更充分一些,所以我就让刘陆和丽丽通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导致王丽丽她意识到,好像家里在拍电影,好像有人在演我。
于是从她的心理角度出发,要回去看一下你们拍成什么样。
王丽丽会不会被别人用其它的角度去评判?我要说,我对她没有任何一点偏见。我们年纪相仿,都是北漂,电影里展现的只是一个生活的侧面,而在生活当中,她还有更多的侧面。
比如我看到的王丽丽,她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她每一天都努力地在北京找到她自己的位置。自己带着一个已经6岁的孩子,而她的母亲又查出了比较严重的病,需要大量的医药费,一直跟她住在北京,虽然居住条件也不太好。她又不敢把她回到东北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她母亲。
这个人物太复杂,她为什么会回到东北呢?她有没有对三舅或其他家人的亏欠?或者她另有一种什么样的推动力,促使她真的十年没有回到的家,今年就回来了呢?
我没有办法替她做这个答案。
但从我的观察来看,我是很感激她的,因为她非常信任我这个弟弟,她同意让我去捕捉她,她没有在镜头前抗拒任何一个不真实!甚至,在她看完了整个成片,她跟我交流最多的是——原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就是四年以前,我们在一个非常极端的事件当中,那个冲击实在太大了!所以你会在电影中看到,家里的人都在为老人过世而准备着,但是我和丽丽就像没有办法走进那个门,真的没有办法,我的脚是挪不动那个步的,我相信她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情绪,实在太复杂了,那个情感,实在太浓烈了。
《吉祥如意》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作,它除了电影本体之外,它同时又是所有被捕捉到的这些人的一段亲身经历。
就说刘陆,首先刘陆对这种创作形式很支持,同时她是有一点兴奋的。因为我跟她乃至整个剧组讲,你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别人的话不会像你们演戏一样再重新来,同时你的对手戏演员他们根本不是演员,他们不会迎来送往,你们只有一次。
拍年夜饭那场戏的时候,摄影师拍到手抖!刘陆为什么突然从片场逃出去了?她害怕了,非常害怕,她并不是执行完一个表演,给自己的一个演出画句号——她是不演了,演不下去了。

 刘陆
刘陆
你会清楚地看到,刘陆在《吉祥》的部分里表演的节奏与其他的——我们就叫做演员好了,事实上是我的家人——有一些差别。
这个时候观众会问,为什么这个女孩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在《吉祥》,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如意》,我就告诉你那个答案——没关系,你刚才看到的一切,就是因为刘陆是个演员,而其他人就是当事人。
因为《如意》破掉了《吉祥》前面的这层顾虑,同时又保留了观众发现这层关系的解谜感,带着这个疑惑往下看,为什么是一个演员呢,那真的那个呢?
我发现,等真的那个人回来了之后,刘陆替代她,承担了家庭矛盾,承担了这场洗礼!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时,真正的丽丽在对待这些事的时候,不是那样的情绪!原来三舅对她的反应,不是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三舅对刘陆的反应。结果是所有的观众和刘陆,承担了那个戏剧功能,我们一起演了一个假的丽丽。
这就是刘陆在《吉祥》的部分“演得不好”的意义。


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我都在做《吉祥如意》,我已经度过了四个春节,你一定是要非常非常有欲望,想要去表达,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用这么长的周期与这个内容相处。
这么说吧,在整个拍摄期间,我是剧组和家人两边的桥梁,我自己的情绪会带动两边的情绪。家人们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去拍摄,剧组也希望我能够在每一个转变的时候,最快速地做最合适的决定。
我的精神压力好大,非常的大。但是没有出口,没有办法与人去分享。
当我跪在地上,跟随着其他亲人,向前爬,向前爬,我当时更多的是恍惚。姥姥的去世,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打击,但同时因为剧组正在拍摄,你作为导演,你不能将你自己的崩溃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那种压抑,无法发泄,这件事让我非常受困。
你问我有没有内伤?有,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之前非常爱笑,但有一段时间,网上很多人讨论,说大鹏怎么最近不高兴了?我出席活动,或者拍了很多照片,都不怎么笑了,说话也不逗了,节奏也变缓了,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苗头,我自己没有主动想过这个变化的原因。
现在回想,就因为我始终没有完成《吉祥如意》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还没有结束!残酷的是,我在最一开始,就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计划,我们要拍这样一个片子,然后拍完第一步就是要把短片做出来,第二步是要把这个短片如何拍的,加在它的后面。短片做出来,其实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我全部都在剪辑。
我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会打开手边的这台电脑,把素材硬盘接上,开始《吉祥如意》的剪辑。《吉祥如意》只是《如意》的部分就有80个小时,我不停地看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有的时候我就崩溃了,我没有办法突然又看到我姥姥过世的瞬间,看到那一场葬礼,看到家人的争吵。
但你要不停地看,不停地看……
越看我越没有办法那么快地把这个电影做出来,可能今晚上正剪得好好的,突然看到三舅在我姥过世的时候哭,那我就跟他哭了一晚上。然后我干脆就整个这一个礼拜我就把素材放在那了,就放在那了。
当我以为我调整好了自己,可以再去面对这个素材,一碰,还是剪不下去,这个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通过语言能让你理解。
你知道我在拿金马奖的时候,上台获奖感言,最后说了一句:“这个奖献给我的姥姥,我真的很想你。”然后我就不由自主地向天空看了一下。那句话我没有想过要说,其实搞得台下所有人都很懵,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就是在拍这个戏的几个月之前,我们回到集安去做《缝纫机乐队》里大吉他雕塑,堪景的那几天,我开了一百多公里,上我姥姥家去看她,那时候她身体挺好的,还给我做吃的,我们俩在一起聊得特别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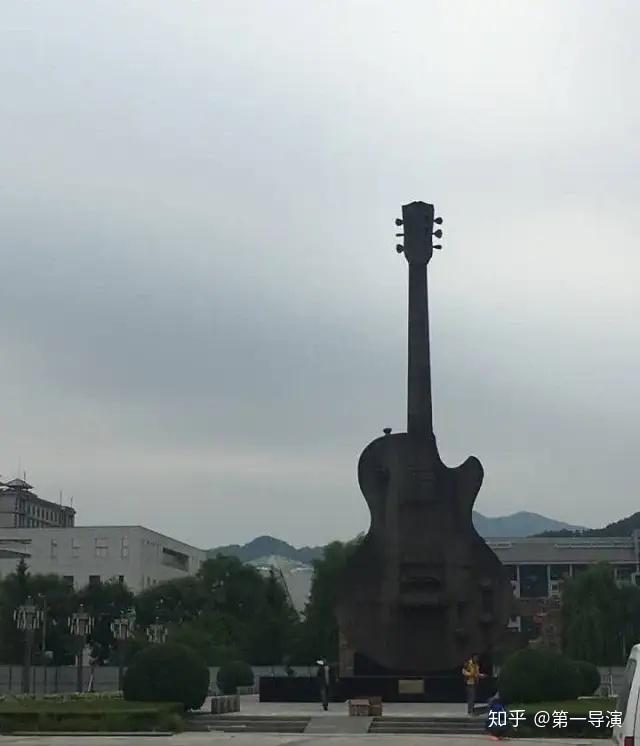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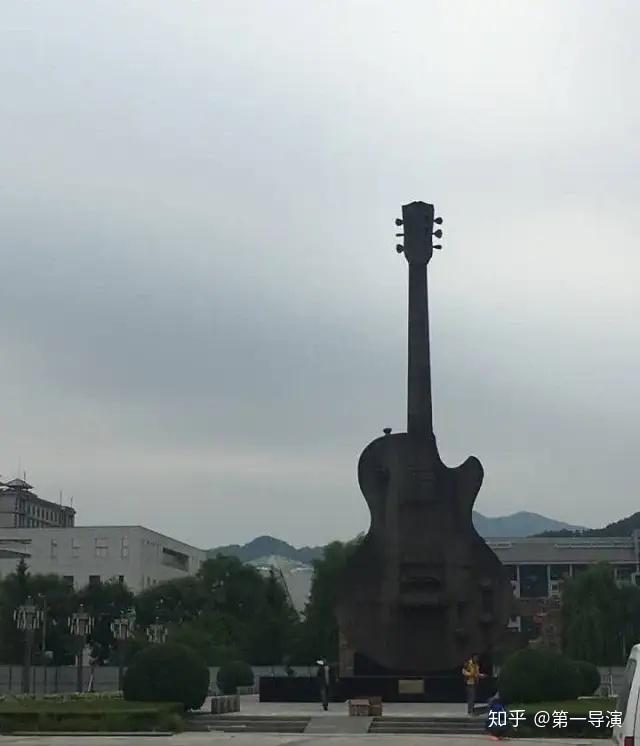
我姥姥送我出来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我本来想跟我姥姥说一些肉麻的话,“我想你啊姥姥”,但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村里的孩子,拿着手机跟我照相拍视频,我姥姥在旁边看着也挺乐呵的,这大孙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
匆匆的告别,一群人的阻隔之下,我就上了那辆车,车往前走,我就往后看,我就看着我姥拄着拐杖在村口,越来越小。
但“我想你啊姥姥”,这句话,我就没说出来。
我想去拍我姥姥啊,我那么爱她啊,我想要跟她一起过年啊,结果怎么就遇到这么大的事,我接受不了啊,然后我就拍了这么一个东西,还得了奖,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我姥姥好好的!!在姥姥最需要我在的时候,我却是一个剧组的导演,我并没有是那个家庭的孩子,我觉得我失去了那个机会,那个机会我这辈子都失去了。

 大鹏在片场
大鹏在片场
金马奖那晚回到酒店,我他妈哭得跟王八犊子似的。到现在咱俩对话的此时此刻,我也没有真正过了这个坎儿。
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你知道心理医生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其实你是跟你姥姥没有完成一次真正的告别。
医生说,等你电影做完了,公映了,大家也看了,这事算有个句号了,你就去你姥姥的墓碑前,你和她好好说说话,你把你委屈和你对姥姥的亏欠都说出来,哪怕你哭一场。
也许那样我才能过了这道坎儿。
你问我最初构建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野心”。“野心”是一个很危险的词汇,我只能说我对我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我知道观众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我的判断是,即便是对我最高严格的人,可能都没有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但我不能把它称之为“野心”,我只是希望不停地保持新鲜的创作,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想要去证明什么,这样的用词都透露了一个重点,叫“改变”,就是你想主动去改变,但是对我来讲,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在不停地尝试而已,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去让谁看到我的改变。
它不能够是带有目的性的。
还有人问我结构上有没有受到《灾难艺术家》《摄影机不要停》和《幸福的拉扎罗》的影响?我想说,这些电影我们都可以去比较去讨论,但是《吉祥如意》的创作是在2016年,当时的构思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它没有受过任何的借鉴。但这个话,我又怕说出来别人觉得我很狂妄,我真的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的电影往往还没推出,或者还没上映,就已经有既定的评价了。
我在想可能也会有人来问我,就是如果姥姥没有遭遇意外,丽丽也没有回来,这一切的如果都发生了的话,那这个电影它会是一个什么样?我想得很清楚,现在的《吉祥如意》,当然不是我一开始要拍的那部《吉祥如意》,甚至我都不希望现在《吉祥如意》呈现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但是,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 我对我自己的导演的能力是有信心的,即使没有发生这一连串的意外,我相信我原计划要拍摄的那部《姥姥》,依然值得大家去喜欢,我肯定可以完成它,而且完成得非常好。
拍电影是很长很长的事,我今年才38岁,对于一个导演,这个年纪往往也只是他刚刚起步。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更多一手影人深度专访欢迎关注。

 ▲搁当时,我们可能没人能想到这是一部上院线的片子。
▲搁当时,我们可能没人能想到这是一部上院线的片子。
鹏哥说:“我们去拍一场天意。”
那么我们这39人的团队,在2017年春节来到吉林省/集安市/花甸镇/柞树村,也是这场天意的一部分。我是电影《吉祥》的剧照,《吉祥》也是我迄今唯一做过的剧照项目,关于影片的人物关系、创作背景之类,高赞们已经拆解得很清晰了,不赘述了。但是我们现在回溯的这一切,看似路径清晰,可在拍摄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像是在迷雾中找出路,在走一步看一步,既没有退路,也看不清前路。
最近有点忙,一次可能更不完,我边整理边更新吧。就着图片,讲讲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儿天意。
我当时在一家投行的品牌战略咨询部门供职,虽然负责视觉,却跟剧照八竿子打不着,也从没做过相关拍摄,能最终进组要感谢:1.老友引荐,2.导演信任,3.老板给假,三者缺一不可。
2017年元旦,一位在大鹏工作室的好友,找我推荐剧照摄影师,因我曾负责图虫社区的运营,所以认识一些拍摄不同题材的摄影师朋友。当时他描述中的这部影片,就带有强烈的纪录片和实验特点,“没有故事大纲”,“主要是抓拍,捕捉式的”“也不知道能拍成啥样”,所以想找一位纪实风格的,有独立创作能力的摄影师来做剧照。问了一圈没有十分匹配的人选,尤其是在过年这个时间段,找人更难。反倒是我自己对这个项目十分中意,首先会有一定自由发挥的空间,其次拍摄周期不长,又恰好与春节长假重叠,也便于找老板“通融”。机不可失,干他一票。于是马上准备了作品集发送过去,次日得到确认后,就跟老板请了假,同时跟父母说明了过年无法回家。
5日,主创去工作室开会,汪士卿老师带着纪录片组已经开始在拍摄了,会上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导演当时讲了两组拍摄的安排,具体我现在已经都不记得了,反正对于影片的概念层面是清晰的,操作层面是懵逼的。不过我这部分相对简单,就是凭感觉放开了拍就好,随后大家签了份保密协议,等待择日出发。
接下来我们这39人的微信群陆续就拉好了。其中5人是司机,剩下34人分为两组,一组拍故事,另一组拍大家如何拍故事,两组都是独立的摄影和录音团队。根据微信群名,才知道了片名是《姥姥》。
 ▲这个群名至今没有改过,人数也没有减少
▲这个群名至今没有改过,人数也没有减少
 ▲在拍摄时用的片名也是《姥姥》
▲在拍摄时用的片名也是《姥姥》
柞树村还是挺远的,我们要先从北京坐火车到通化,再坐剧组的车到花甸镇,团队在花甸镇里的宾馆住下,因为柞树村里没有地方能住下这么多人。从花甸开车到村里差不多还有一小时路程,都是山里的冰雪路,坐在车里看着都提心吊胆的。

路上有听到议论说姥姥病重,原来的计划要调整,但是没想到最终到达村里时,姥姥已经住院了,可能有生命危险那种。那时候才意识到这个“调整”的幅度可能有多大。我们要拍摄的核心人物姥姥不能参演,这意味着原本就少得可怜的“拍摄计划”也完全泡汤了,试想我自己若负责这个项目肯定二话不说原地爆炸,然而导演要面对的不仅是拍摄的调整还有姥姥病危所带来的打击,大家都为他和姥姥捏一把汗,当时也没人知道接下来此行的最终结果如何,即便到此为止了应该也不会意外吧。
导演到达花甸后,晚上的会开得极其沉闷:
这时候没人能帮得了他,同时所有人又在等待着他拿主意。导演一根接一根的吸着烟,我们没有人说话。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撕扯,也好像听到一句:“不能让大伙过年白折腾一趟哈…”。到现在我也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去平衡这些困难完成拍摄的,也从未敢问。——刘陆老师的回忆
终于等到了导演的决定:拍三舅。对于继续拍摄来说,这个人物的转换并不意外,因为即便按照原计划来拍摄姥姥,三舅的赡养问题也是姥姥最关心的,年夜饭讨论的核心,一家人的矛盾所在,本来也会是影片的重头戏。姥姥的去世只不过是意外拿掉了家里人摊牌的最后一道缓冲,让三舅这个问题,必须在此时此刻放在台面上。
从那一天起,白天导演带着大家拍摄,晚上闷在会议室里面做粗剪,开会的时候看粗剪片子,确定第二天的拍摄。
事实上后来导演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做粗剪。比如...
 ▲在柞树村的麻将桌上,周围村民正打得热火朝天。
▲在柞树村的麻将桌上,周围村民正打得热火朝天。
显然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帮他完成这个故事线,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一边处理着家里的糟心事,同时还要指挥大家把这件糟心事记录好,还要一有时间就反复看、反复分析这个事,并且从一个现实的家庭角色中抽离出来把这件糟心事一镜一镜码好,还要盘算着明天要怎么拍能把糟心事表现好。在现场我看到的是他在这几种状态间无缝切换,但谁都清楚,这不会是看起来那么轻松。
 ▲大家只能过来看看,没人能真正帮得上忙。
▲大家只能过来看看,没人能真正帮得上忙。
三舅看起来是拍摄中的不确定因素,实际我觉得他是最确定的,确定到在什么要时间做什么,都像是程序写好的一样,不必担心他会恐惧镜头、掩饰情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情绪从头至尾都是片中最纯粹的。
 ▲姥姥家外景,三舅每次抽烟,就出门上街走一个L形路线,抽完就回屋
▲姥姥家外景,三舅每次抽烟,就出门上街走一个L形路线,抽完就回屋
 ▲单从三舅抽烟的姿态来讲,感觉不出来他有什么异样
▲单从三舅抽烟的姿态来讲,感觉不出来他有什么异样
至于三舅究竟明不明白2017年春节发生的这一切?
我认为是的!









待我抽空继续更吧。
1.
那顿晚饭,是《吉祥如意》的戏眼。
姥姥去世,让这顿本该在年三十吃的晚饭,推迟到了姥姥葬礼结束之后。
原本是一场难得的合家欢聚,变成了三舅归属问题的讨论会。
三舅原来在辽河油田当保卫科长,四个兄弟姐妹都曾获得过他的帮助。
这个为家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后来得了一场病,智力仅维持在几岁水平,一直由姥姥照顾。
姥姥去世后,三舅的未来就成了一个迄需解决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在深不可测的人性面前,一部青春片其实也可以拍摄成恐怖片。一部讲述亲情的电影,也可以拍成战争片。
那么这顿晚饭,就是战场上的正面交锋。
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电影不同,《吉祥如意》里没有形状清晰的敌人。
在争论过程中,最重的一句话是二大爷说的,“那还能把他杀了,还是咋地”。
可过程一直刀光剑影、招招见血。
兄弟姐妹四人,但凡有任何一个人想真的收留三舅,都不会出现这场讨论。
每个人都用阳光明媚的语言去掩饰翻滚在心底的想法,用火花四溅但毫无附着之处的情绪,去勉力缝合传统中那个叫一奶同胞的亲情。
“不管老人留下这么个麻烦也好,还是怎么的,你们毕竟是一奶同胞。”
“就是一个人帮四个人,我觉得挺难帮的,四个人照顾一个人我觉得还可以吧。"
"咱妈后事花的这些钱,连咱妈住院,全是由我,你知不知道?"
“我没花,你伺候的?”
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剧作家都无法创作出的情节,是任何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无法完成的表演。
好像战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侧面的战壕里,可对面并没有明确的敌人,也全是无效的攻击。
最后的结果也是,三舅由兄弟姐妹四人轮流照顾。
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不同,艺术需要起承转合,生活总是杂乱无章。
在艺术的语境里,善恶截然分明,而在生活中,善恶互为一体,只是某一时某一事上的选择。
艺术需要一个结果,生活里往往没有结果就是结果。
艺术需要合理,生活则不。
所以,影片里那些镜头一掠而过的部分,比故意捕捉的部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解读性。
比如,姥姥去世时,有人喊“三舅哭了”。
比如,演员刘陆问自己饰演的丽丽,“为什么十年不回家?”
比如,丽丽的突然出现。
比如,没有经过任何美术置景过的姥姥家。
2.
提到《吉祥如意》,就绕不开影片的结构问题。
《吉祥》和《如意》两部分,既相互并列又互为一体。在《吉祥》里提问,在《如意》里解答。
影片有三个细节可以摆放在一起。
三舅总叨咕的文武香贵,是四个兄弟姐妹的名,也就是说老王家,在他们这一辈,算上他,一共兄弟姐妹五人。
到三舅的下一代,就只有一个独生子女丽丽。
影片最后,一家人照全家福的时候,背后的房子上写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变化天翻地覆。
在思想上,一个西方人活了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可用于发酵的时间容器,也不过仅仅是四十年。
相比于贯穿在传统里的诸多规矩,自由获得了更大的生长空间。
几乎所有的自由,最先出现的时候,都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终于等到了一个允许破坏,也有耐心等待建立的时代。
但也不得不面对的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拥塞在一个物理的时间和空间里。
几种思维的横截面,平时以北京和集安为分界点,有意无意地彼此逃避,保持各自的相安无事。
可一旦通过春节,进入到同一时空,摩擦与撞击所产生的火花,就变得异常灼热。
这种灼热,曾经体现在对婚姻的态度上,也最终体现在对赡养的态度上。
这种水与火的冲突,因为都知道只有七天的有效期,就都默契地借用亲情去遮挡,以维持表面上的其乐融融。
《吉祥如意》拍摄出了那种表象上的吉祥,也拍出了吉祥下面每个人的不如意。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余光里,三舅的未来还能交给兄弟姐妹们去轮番照顾。
可随着一种社会结构的瓦解,一个新的社会性问题就摆在每一个观看者的面前,那么独生子女一代的未来呢?
3.
导演大鹏找刘陆饰演十年没有回家的三舅的女儿丽丽,但在拍摄中途,丽丽回来了。
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挽着父亲出门散步。
和二大娘谈论父亲的一些生活细节。
和导演大鹏说,那个饰演她的演员还挺像她的。
那顿晚饭,家里人因为照顾父亲的问题而发生争吵时,饰演她的演员情绪崩溃,她坐在一旁玩手机。
大鹏说,后来看片,到这一幕的时候,丽丽做出的还是相同的动作,又拿出了手机。
这个世界很大,可她也只能逃到手机里了。
其实,无论是导演大鹏还是这位丽丽,都是家乡的闯入者,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和家乡土地已经迥异了的气质。
同时,他们也是家乡的出走者,只要一触动那个开关,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会和这块土地再一次发生他们都不太敢面对的关系。
他们成为了客人,可归根结底还是主人。
他们一直想要改变,并以为已经改变了的东西,最终发现,还在血液里流淌。
在影片里,母亲说了一句话,“树倒猢狲散,老人就是这个家的凝聚力,老人走了,以后这样的聚会大概不会有了。”
出走的一代人,和家乡的维系越来越微弱。
家乡还是家乡,但已经成为出生地,或者户口本上的籍贯地。
一代人正在丢失自己的故乡。
所以,对于同一件事物,《吉祥》是用一代人的目光去注视,《如意》是另一代人的目光注视。
在《吉祥》里,上一代人在依稀的传统亲情的推搡下,三舅获得了亲戚们的照顾,问题暂时获得了解决。
在《如意》里,无论是大鹏还是丽丽,都束手无策,丽丽只能躲进互联网里,大鹏只能一次次流泪。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三舅,在一场关于自己未来的讨论里,当事人失去了发言权,成为一个缺席者,一个旁观者。
即便是这部《吉祥如意》,也是用尺寸有限的理性对无边无沿的感性,进行的一场强行解析。
《吉祥如意》最令人敬畏的就是它的勇敢,因为勇敢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残酷,因为残酷而温情。
弥漫着动物世界里本能的追逃,也散发出人类优良传统最后的微光。
除了勇敢,大鹏对《吉祥如意》最大的贡献就是不作为。
他没有用艺术的手段去篡改生活,生活则赠与了他一个最伟大的剧作家所能给与的一切。
《吉祥如意》将一个时代的裂缝,推到了一个极端。在现实面前,亲情冷酷到残忍,但最终敲断骨头还连着筋。
甚至,亲情的温度本来就是绽放在残忍现实里的花朵。
从这个角度来说,《吉祥如意》弥散着一种简单的复杂,一种浅显的深刻,一种冷酷的暖意,一种善良的残忍。【本文源自公众号 阿郎看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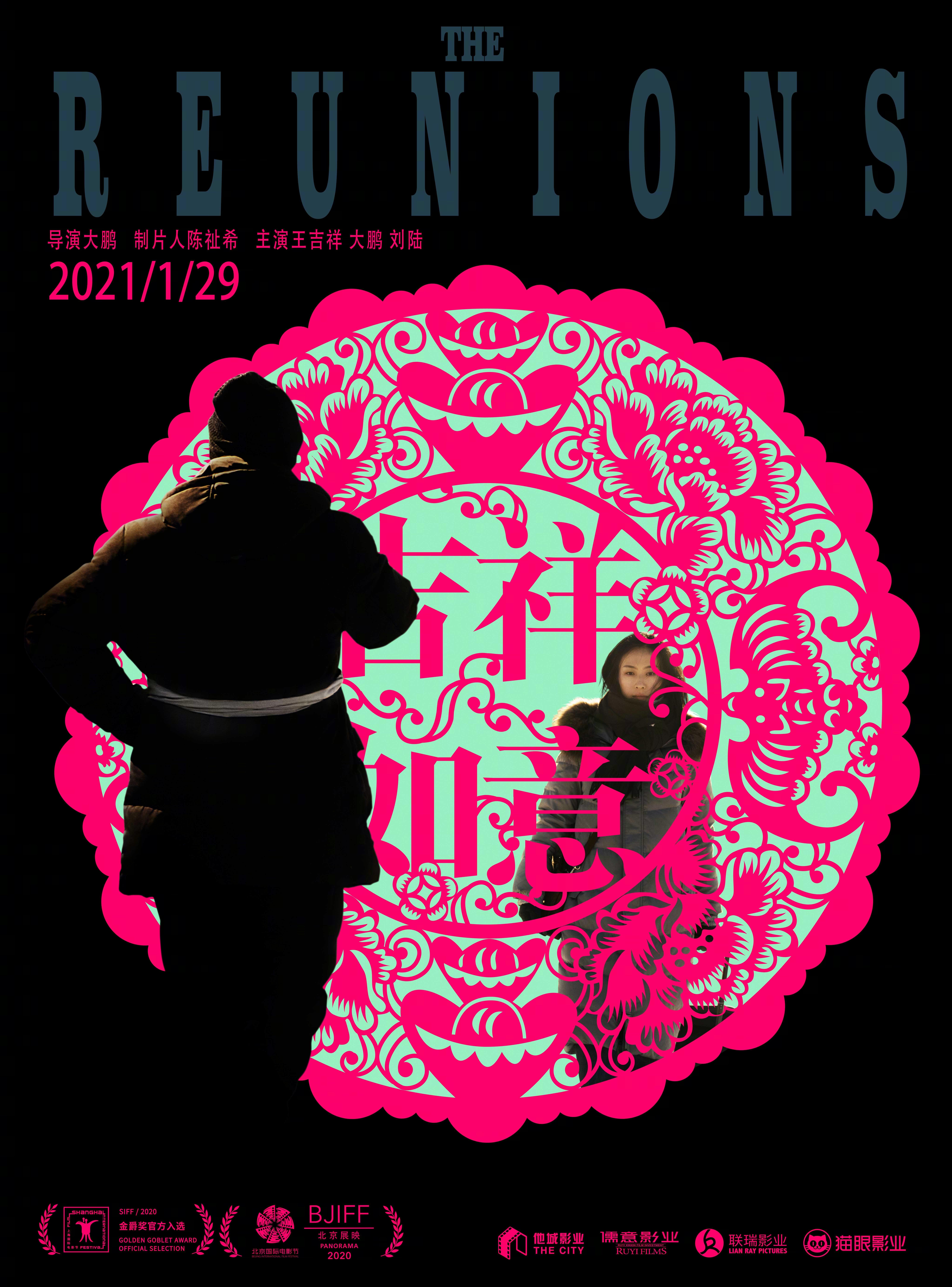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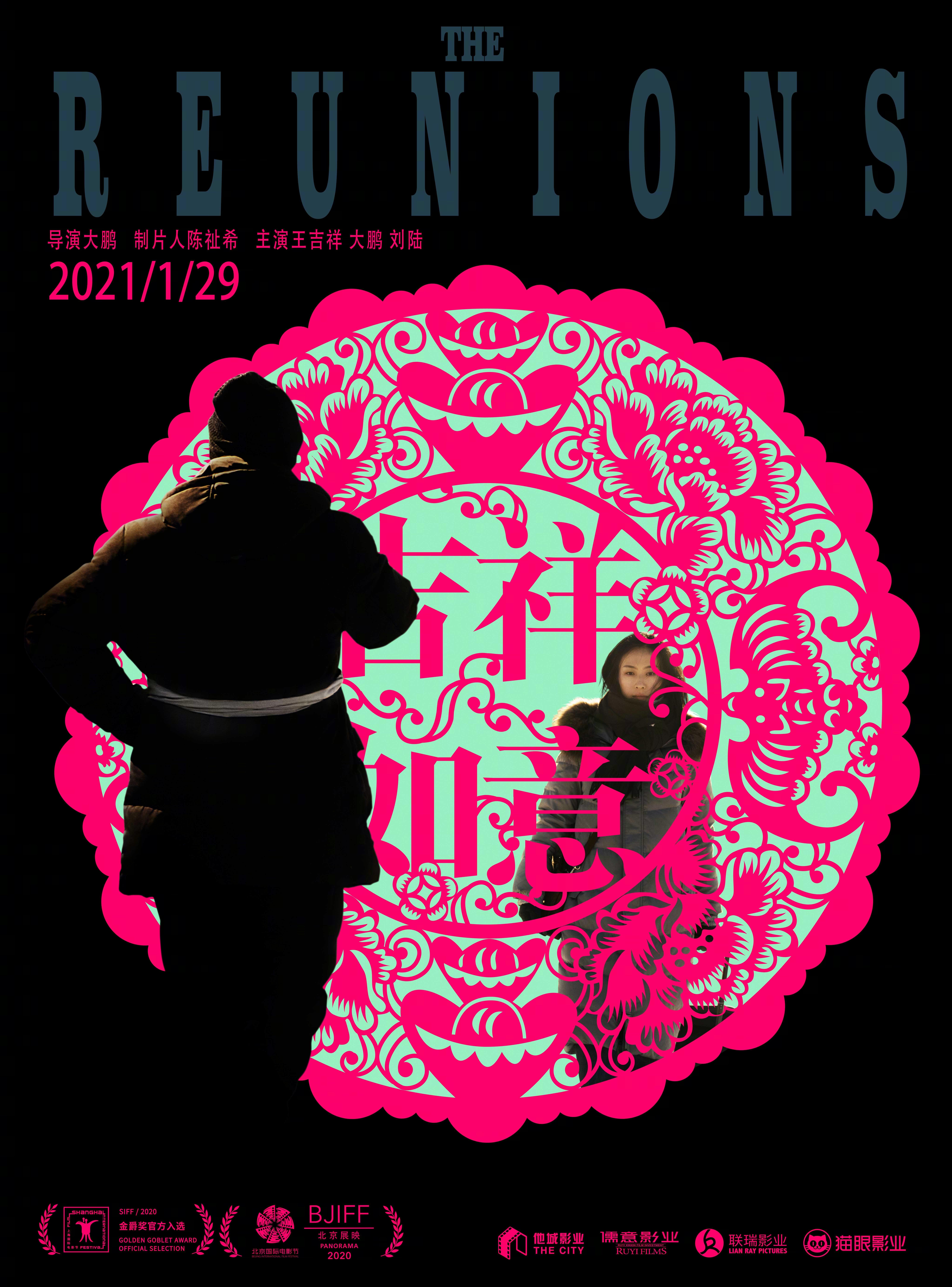
2017年春节,导演大鹏回到东北农村老家,想要拍一部关于姥姥如何过年的片子。
为了拍电影,全家人齐聚一堂。但有一个问题,三舅王吉祥十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失智,他的女儿王庆丽在那之后再也没回过老家。
于是大鹏找来演员刘陆来扮演表妹丽丽,并虚构了她春节回家和父亲团聚的情节。

父女久别重逢原本承包了主要的戏剧冲突,但由于姥姥的意外病重,一个隐藏的家族矛盾提前浮出水面:老人去世之后,谁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王吉祥?
影片围绕王吉祥悬而未决的命运徐徐展开,而演员刘陆,则成了整个事件的风暴眼。
大鹏将回家拍摄电影的过程记录下来,连同45分钟的短片《吉祥》,构成了《吉祥如意》这部影片。
短片的部分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提供了一种真实的沉浸感。在后半部分的幕后纪录片中,我们见到了真正的王庆丽,看到了影片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对影片的「干预」,短片中构建出的真实感被部分消解掉了。
不过几乎同时,另一种真实感很快建立起来。我们会对恰好被记录下来的天意产生敬畏之心,这是纪录片很重要的一部分魅力。
而《吉祥如意》几乎可以说是顺应天意的产物。

纪录片意味着「真实」,真实的人物,客观地记录;而剧情片则以「虚构」为前提。
《吉祥如意》似乎模糊了剧情片和纪录片的边界。
当影片中的真实人物面对演员刘陆时,需要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王庆丽来对待,这已经进入了表演的范畴。
对于缺乏表演经验的非专业演员来说,想要获得令人信服的表演,需用尽量真实的刺激引导他们做出自然的反应。考虑到王庆丽多年没回过家的事实,久未谋面的亲人面对刘陆时自然流露出的陌生感,恰好满足了观众对这一情境的想象。
如果我们对比“真假”王庆丽和王吉祥见面的场景,比较两者观感上的差别,我相信会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和我一样认为,至少在影片后半部分揭开谜底之前,刘陆这个同样陌生,但是和亲戚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假王庆丽”,似乎比真的还要真实。

未经矫饰的陌生感并不是亲戚们表演的全部内容,我们应该都记得大大爷和刘陆单独见面的那场戏里,他们谈起如何安置吉祥的问题,大爷几度落泪。如何解释他们面对刘陆流露出的真实情感呢?
影片中的真实人物,在面对一个虚构人物时,他们的反应或者表演,是否具有真实性,或者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在表演中有一个说法,叫做“moment of truth”,演员的【至真时刻】。简单说就是在完美的表演时刻中,演员真的成为了ta所塑造的人物,演员的身份以及电影拍摄的情景对演员的干扰暂时接近于零。也就是说“真实”,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观感上真实的表演」,是可以与虚构创作共存的。

我们很容易忽略一点:即便是客观地拍摄真实的人物,他们在摄影机前的一举一动,本来就无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表演性】。甚至有人认为,纪录片的魔力恰恰在于人在镜头前潜意识里的表演性。
“看我们能抓到什么。”这是导演大鹏在现场经常对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他让刘陆来提出话题,解封陈旧的记忆,记录亲人们的反应。
刘陆是故事中的虚构部分,是导演介入真实的工具。我们甚至可以把她看作一台摄影机。
一切在镜头前的行为都是表演,反过来,所有影像都是对表演的如实记录。
我们经常目睹像克里斯蒂安·贝尔这样的演员,不断地为了角色增重或是减重。单纯从演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以认为所有的影片都是纪录片,也都是剧情片。
或者说它们都在追求一种「有真有假」的「非虚构」状态。
我们不妨把刘陆在《吉祥如意》中的经历,看成一场体验式的表演纪录。
它是一场对表演本质的实验性探索。

刘陆有很多关于人物事实性的“真相”,供她去把握王庆丽这个人物:有一个孩子父亲出事前对王庆丽很好父亲出事后母亲提出离婚王庆丽在法庭上说了不利于父亲的话,导致父亲净身出户后来的十几年里,王庆丽没回过老家,最近几年开始,每年的春节打电话回家,询问父亲近况
在整部影片中演员刘陆是一个体验者,一个观察者,没人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她说什么话,她的手上没有剧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感受,以及,想象。
 刘陆和吉祥
刘陆和吉祥
 王庆丽和吉祥
王庆丽和吉祥
刘陆需要想象,这个我面前牙掉光了的老人,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是王吉祥。这些照顾他的人是我的家人。
刘陆挽着吉祥的胳膊在村子里面走,想象自己曾顺着同一个积雪的土坡溜下来,壮年的吉祥拍拍她身上的雪,把她扛在肩上。
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