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燕食记》: 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

《燕食记》: 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
文 | 李掖平
摘要:
《燕食记》在近百年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下,描摹香港社会和各色人等与美食相关联的日常生活。通过诗意诠释岭南美食之美之魅,深情礼敬人物形象“善与爱”的人格之德,精妙设置互融互衬的三重叙事复调,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和敞开。其人物形象蕴含悯恤、疼惜、从容、节制、洁净、崇德、尚爱、向美等传统文化因子,包含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对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性格关系进行了独特思考。这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方式和审美效果,彰显出的是作者对历史和文化、社会和人性、生命和生存、写实和抒情的独特理解和认知。这种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恰恰也是小说的灵魂所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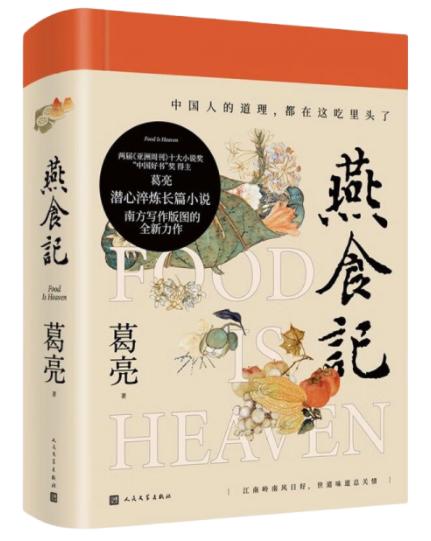
作者:葛亮
葛亮的《燕食记》以香港著名的岭南风味美食为中心,在从20世纪初至今近百年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下,描摹写生香港社会和各色人等与美食相关联的日常生活,笔力的重点始终放在呈现民众俗世的现实日常生活及其或热闹或寂寥或浮华或沉潜的世态人情,只为记存那相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宏大社会主题而言,更为生动具实、更为丰富鲜活、亦更为真实可信的时代光影和生命存在。然而如实描摹不禁使人眼前一亮食欲大动、更使人艳羡不已心向往之的香港和岭南美食小吃的各色样态,绝非葛亮的终极艺术目标。写一部关于饮食的小说,只是他的一个创作计划。有时候写什么可能真的并不特别重要,而怎么写和为什么写,才是一个优秀作家更为关注的重点或者说中心。所以我认为,通过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和敞开弥散在整部小说书写空间里,充盈在岭南普通民间日常生活里,沉潜在各色美食小吃的制作技艺里,鲜活在众多人物形象性格里的诸如悯恤、疼惜、从容、节制、洁净、崇德、尚爱、向美等传统文化因子的丰富蕴藏,为深蕴岭南美食中的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绘态画魂,借此廓清和厘定传统文化精髓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根性支撑,借此敞开并礼敬香港乃至中华大地上一切“人格之德”的美丽与魅力,才是葛亮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而且将其写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高度与深度的创作旨归。这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方式和审美效果,彰显出的恰恰是作者对历史和文化、对社会和人性、对生命和生存、对写实和抒情的独特理解和认知。而这种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恰恰也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
一、诗意诠释岭南美食之美之魅
诗意诠释岭南美食之美之魅,是《燕食记》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的第一个要素。我高度认同《收获》期刊编辑刘嘉文说《燕食记》“是当代文学史上关于中华美味的召唤之书”这句荐书语,因为我们确实可以在小说里看到岭南一带闪亮着中国传统文化光泽的各色美食。诸多,许多,林林总总,如同缤纷花雨漫天飘洒,只让你觉得眼里心里一片又一片繁花似锦。将这部小说放到整个当下文坛来看,都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件艺术个性标示度最为鲜亮最为独特的文学珍品。作为一部专门讲述有关美食故事的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所有人、所有事,都与香港及岭南的各色美食和小吃有着或“剪不断,理还乱”、或“不思量,自难忘”的密切关联。小说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夕食”为开篇,又以《食啲乜》为书的后记,作者坦然告知读者“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更重要的是,小说借关乎岭南饮食文化的日常情景,以诗性之笔塑造出一群既具有秉承“人格之德”共性、又具有鲜明鲜活自我个性的美食大按、小按、红案、白案师傅形象,生动传神地描摹、刻画、雕绘了从兵荒马乱到天下太平一段漫长岁月中冷暖世间人生人性的百态情味和韵致,在发探和激活中华美食文化的神韵与精髓,追光和定格中华民族在日常生活细节之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遵循、礼敬、赓续、发扬的同时,使岭南美食体系带着荣光尊严、带着浪漫诗意进入文学书写和审美视阈,获得了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
饮食之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自然毋庸赘述。作为中国饮食文化观念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后来,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强调国家要以人民为根本,而人民靠粮食赖以生存。唐代司马贞为《史记》做注释时,注明此话最早是管仲所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这种阐述由庙堂和书斋逐渐走向民间后,粮食被民众扩大解读为日常所需的各种饮食。从民生乃治国之本的意义上来说,“食”,作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要事,始终贯穿于中国族群繁衍和文化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如儒家所言,重视民生,重视人权,从人之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满足百姓的衣食需求,提倡富民思想,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这一阐述为“民以食为天”进一步提供了符合伦理正义性的理论支撑。
于是,我们在《燕食记》里读到了与美食风味佳肴相关且又互为融会贯通的诸多故事。这些故事以香港“同钦楼”大案荣贻生无人能敌的“手打莲蓉”月饼为载体,通过塑造不仅懂得美食的美味、更深谙和珍惜美食的内在文化精髓的诸多人物形象,缠绕联通起人世间和人性中的所有情味、滋味和意味。书写他们对美食的美好回忆,描摹他们对人与人之间有情有义、重情重义的崇尚与礼敬,以飞扬灵动的诗性诠释了岭南美食文学之美之魅。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以独特的文学抒情方式,一一描摹敞开了香港和岭南食坊间流行的各色美食的成品过程或各色茶点的品鉴流程,如对慧生自创的那道名为“鹤舞白川”仿鱼片制作流程的描摹,再如对茶楼里斟茶的“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海底捞月”四套看家本领的介绍,以激活一段或族群或个人的历史回忆,承载一份思乡恋乡的情怀、记住一片美丽而忧伤的乡愁。说起中国的美食(菜肴和点心),当属广东岭南地区款式和风味最多,让饕客们涎水直流艳羡不已。据百度百科介绍,广式点心品种异常繁多,甜咸、酸苦、麻辣、荤素各种食材均有,丰富性居全国之首。其品种、款式和风味由皮、馅和技艺构成,点心皮有四大类二十三种,点心馅有三大类四十六种。制作点心的师傅们凭着高超的技艺,赋予这些不同的皮和馅以千变万化的组合与造型,制成各种各样的花式美点。口味咸甜兼备,款式造型新颖灵俏,制作技艺精细高超,色香味清谐爽利,令人百食不厌。落实到《燕食记》里,有对广式点心“四大天王”(虾饺、烧麦、叉烧、蛋挞)的品鉴心得,也有对各色点心如萝卜糕、皮蛋酥、芝麻包、水晶生煎等从选材到备料到火候到成品呈现的制作方法和料理妙招的详尽梳理,更有对粤菜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特色的概括总结……毫不夸张地说,举凡岭南美食点心和粤菜的奥妙与神奇,都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形貌和活色生香好滋味的品格成为艺术审美形象。
第二,通过对人、对情、对爱的深情追忆,承载起国人对深蕴岭南各色美食之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情与认同。进入文学视野中的各色美食,其能指早就超越了食物本身,而成为一种情怀、一段回忆、一片乡愁、一种人生的寓托。有一首如今已记不清名字的流行歌曲曾这样吟唱:唯美食与爱,能让漂泊落地生根;唯美食与爱,能让孤独得到安慰和治愈;唯美食与爱,能让失落的心获得救赎。美食,填满肚子;爱,充盈内心。然而国人喜欢美食推崇美食的一个更重要原因,则是因为能从美食享用中获得处世为人的教化,获得生活智慧和生存哲理的启迪,以助力人格德性的养成。
早在长篇小说《北鸢》里,葛亮就借文笙母亲昭如之口,引例安徽毛豆腐、益阳松花蛋、肴肉等特色吃食,以“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句话,诠释过国人在饮食上善待“意外”的理由——因为这“意外”实证了哲理“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而在《燕食记》里,葛亮更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立体化呈现了美食的文化精髓和奥义。诸如对材料的爱惜、对制式的遵循、对分寸的拿捏,对尺度的掌控,以及对形神合一的尊重、对行事立人“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成功之道的领悟等。小说中的每一种美食小吃,都彰显出拿捏分寸、掌控尺度的精准与协调。仅举小说上阙里第一回的这段文字为例:
五举想起什么,便问,阿爷,你说怎样的叉烧包,才叫“好”。阿爷一乐,说,我孙包的叉烧包,就叫好。
五举也乐了,说,阿爷,我是问你正经的呐。
阿爷便正色,思付了一会儿,说,我看,这好的叉烧包,是好在一个“爆”字。
五举也想一想,问,叉烧包个个爆开了口,不是个个都是好的?阿爷说,是个个都爆开了口。可是爆得好不好,全看一个分寸。你瞧这叉烧包,像不像一尊弥勒佛。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弥勒,是因为他爱笑。可是呢,这笑要连牙齿都不露出点,总让人觉得不实诚,收收埋埋。但要笑得太张扬,让人舌头根儿都看见,那又太狂妄无顾忌了。所以啊,好的叉烧包,就是要“爆”开了口,恰到好处。这香味出来了,可又没全出来。让人入口前,还有个想头,这才是真的好。
五举说,爆不爆得好,得面发得好,还得“蒸”得好。
阿爷哈哈一笑,对喽。发面是包子自己的事,“蒸”是别人的事。这蒸还更重要些。不然怎么说,“三分做,七分蒸”呢。所以啊,人一辈子,自己好还不够,还得环境时机好,才能成事。古语说,“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这段文字里阿爷所说,正是分寸的拿捏和尺度的掌控之于叉烧包如何爆口才恰到好处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在诠释做人既不可太过张扬、又不可太过拘谨的生活智慧和生存哲理。而五举悟出的叉烧包不仅要面发得好,还得“蒸”得好的道理,也并非只关乎美食制作的协调性和系统化,亦深蕴着身在社会怎样处世为人、如何抓住成功机遇的道理。从制作叉烧包的技艺,到处世为人的道理,再到掌握尺度与分寸的生活智慧和生存哲理,一层层领悟,一步步深入,可谓微言大义,精警深刻。更重要的是,这种微言大义,精警深刻,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以诗意鲜活的文学描摹完成的。
二、深情礼敬人物形象“善与爱”
的人格之德
深情礼敬人物形象“善与爱”的人格之德,是《燕食记》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的第二个要素。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葛亮每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分南方北地,无论男女老少,亦不管身处何境——繁华盛世也好,艰难时局也罢,心底深处都始终藏有“善与爱”。《燕食记》以饱蘸深情的诗笔,将香港或各类厨师或普通市民或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或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任凭风云际会变幻无常,终守人性向善恒久如常的人格之德,写得生动传神活色生香,使读者感动到眼也潮湿心也潮湿。尤其是那些厨艺高超的男女主角,从荣贻生、叶凤池、赵本德、陈五举、韩世江、聂师傅,到月傅、慧生、凤行、云重、露露,他们或得名师真传,或因家学积累,或天赋异禀、出身草莽却能自悟于闾巷乡野,或仅仅不过就是为谋生而学厨。虽出身、教养、遭际、性情各自不同,大按、小按、红案、白案各司其职,但在日常生活中,始终持守着“善与爱”的情愫和情怀,即使是在日军入侵港岛沦陷的那段战乱岁月里也不改初衷,照旧在厨艺上追求技艺的精益求精,在人情世故上讲究通透和悯恤,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最灿烂的光泽。
善,被苏格拉底视为世界的最高目的,认为个体生命道德生活的最高准则就是尚善。主张人之为人一是要努力获得对世界的善的最高知识,二是要在生活中以善的理性锤炼自我灵魂,使善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品格。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里,善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被推崇为是完善自我(泛指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然本性,是理性控制下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满足。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力主张正人君子要心有善念、言有善语、行有善举,以养成洁身自好、悯恤他人、善待万物、尚爱向美的人格之德。
洁身自好、悯恤他人、善待万物、尚爱向美的人格之德,在小说主人公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二人身上彰显得格外鲜明和鲜活。荣贻生是香港最享盛名的广式茶楼“同钦楼”的行政总厨,从老字号迁港,历经三朝,无论是在店里还是在社会上都称得上是德高望重。其“手打莲蓉”的制饼技艺更是无人能敌,尤其是那款用枣蓉、杏蓉、莲蓉创制出的“同钦三蓉”,更是在当年的香港风靡一时,甚至流入黑市被炒至“一盒三蓉一条金”的高价。荣师傅的制饼技艺堪称一流,处世为人却一向低调。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性格温厚、虔敬礼法。在厨艺上,不管时潮多么浮躁,不论世风如何日下,他都是一心一意倾情踔力只为制饼,一是要制最好的“莲蓉包”以飨他人,二是要将制饼的高超技艺传承光大——“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在生活中,对师傅、对徒弟、对妻子、对友人、对街坊邻居,甚至对竞争对手,他一律倾情以真,待人以诚,其“善与爱”的人格之德熠熠生辉。
而人格之德在陈五举身上的敞开,则是与其从拜师学徒到扬名立万的生活经历相伴相随。五举虽是从茶楼里最基层的“茶壶仔”做起,却有幸一路走来得到了诸多好人的真心相助。他最早进入香港“多男”茶楼时,打的第一份工是跟在茶博士屁股后头煲水、做些下栏活。因为做事勤勉,被茶头赵本德师傅看中,抽空便口眼心授,有意将自己斟茶的看家本领在五举面前多过几招,后来更是正式将他当“企堂”培养。二人感情渐似祖孙,五举称赵师傅为阿爷。当五举被香港“同钦楼”大案荣贻生一眼看中主动提出想招他为徒时,赵师傅虽心有不舍,五举也表态自己不要去做什么点心,一辈子就跟着阿爷做企堂。赵师傅却说五举是一个有大天地的孩子,愿意助他成为一条“过江龙”。正是赵师傅的这种善心善意善举,在五举心中植下了“人格之德”的种芽。
进入“同钦楼”后,荣师傅让五举先去做最基础的小按学徒,带五举的是以包虾饺著名的聂师傅。五举明知偷师是业内俗例,别的学徒也都“双偷成性”(干活偷懒,瞅空偷师),他却每日只知目不斜视地勤力干杂活。聂师傅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师傅若看得上五举,便会教我本事。我若是偷来的,自己用着也不踏实”。正是这种做人以诚的人格之德,使聂师傅决定将做虾饺的全部技艺倾囊相授。
一只小小的虾饺看似简单,其实其发面、擀皮、调馅、揉团都暗含许多门道,所以历来被奉为茶楼点心“四大天王”之首。虾饺之难,难在由表及里,配料要求严苛,面皮也极为讲究。聂师傅叮嘱五举,做虾饺如同做人,必须认真,实诚,精益求精,从虾饺皮的烟韧,到虾三只、肥肉四粒、笋五粒的馅料搭配,再到定型的十二道褶,都须一丝不苟,绝不可因为已经盛名在外便偷工减料。“咱们这虾饺,必须包上12道褶,才算成了”。这是聂师傅给五举上的第一课。
每一只虾饺都必须包上十二道褶,这似乎是一件再小不过的“小事”,往大处说亦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善”,然而这却正是聂师傅对五举的人格教化。当年,刘备在临终前留给其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遗诏,劝诫他要从小事开始防范作恶,否则小恶积少成多会坏大事甚至会乱国;忠告他要从好的小事做起,因为小善积多了方可成大事,方能成就惠泽天下的大善。刘备这句话后来被世人尊为做人立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叉烧包从捏十二道褶减到只捏十道,从小处说也不过就是偷工,实在算不上是恶或者说不过是小恶,但从大处说,小恶不制必然发展,若一力纵容下去,焉知有朝一日不会从偷工逐渐演变成犯错甚至犯罪?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而引起质变的,反观社会上那些罪犯,哪个不是从“小恶”开始走上犯罪道路的呢?由此可见,正是这份中正、诚实、虔恪、严谨,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遵规守德,聂师傅才能将一只小小的虾饺做得“晶莹剔透入口香滑多汁”,获得了堪称一绝的广泛赞誉。更重要的是,聂师傅不仅教会了五举做虾饺,更教会了五举做人务要持之以恒的遵规守德、虔恪敬业的道理。聂师傅的叮嘱由此也表征出德行教化的价值和意义。
正式跟着荣贻生学做“大按”后,荣师傅摆出“十方阎罗”的严苛架势训练于他,从做礼饼的“酥皮”开始,反复强调“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夜以继日地训练五举怎样掌握技艺的“慢”,接着又以炸“芋虾”来反复训练五举如何掌握技艺的“快”。五举花费整整一年的时光学到的这“一慢一快”,高度契合了荣师傅传授技艺的秘诀,即技艺是学出来的,更是练出来的、“熬”出来的。同时,这“熬”,也正是岭南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之道。五举心里清楚,自己从这种学、练、熬中获得的不仅是制作礼饼的技艺,更是做人做工、行事处世要从容节制、慎终追远、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规矩的道理。而师傅对他的严苛,其实正是对他的器重,因爱之深,故教之严、责之厉。
然而,就在五举已得荣师傅真传,炒得一手好莲蓉时,美妙的爱情降临了,他爱上了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独生女戴凤行,并答应入赘戴家,夫妻同舟共济撑起“十八行”。向荣师傅辞别时,五举承诺此生不再使用从师傅这里学来的制饼技艺。五举结婚后,每到年节总要备礼携妻去同钦搂探望师傅,虽师傅避而不见,他却每每站在门外数小时,且数十年雷打不动。这种倔强的坚持只因师傅于他有恩,他便终生尽孝致礼。
小说的结尾是师徒俩在香港厨师总会举办的厨艺大赛上进行冠亚军对决,对决的主题是“鸳鸯”。五举做出的是一道名为“太极”的鸳鸯点心,由豆腐、黑豆、黑芝麻、阿胶融汇制成,“黑白交融,壁垒分明”。荣师傅则是亮出了他最拿手的制饼技艺,但他有心成全五举让五举夺魁,便故意以受过伤的右手端炒锅炒莲蓉,结果锅便掉落到炉灶边,荣师傅主动认输。这时五举却走到师傅身边,执起师傅的手轻轻按摩其腕肘,然后将炒锅重新架在灶上,开了火,炒好莲蓉,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正是书末这场无人胜出的比赛,将荣贻生和陈五举“善与爱”的人格之德推向了高峰,亦推向了极致。
三、精妙设置互融互衬的三重叙事复调
精妙设置互融互衬的三重叙事复调,是《燕食记》高标独立的诗学审美表达与建构的第三个要素。从叙事策略来看《燕食记》,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复调小说,既是非虚构书写与虚构书写的叙事复调,又是人物形象与美食技艺的格物(人品与物格)复调,更是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的对话复调。三重叙事复调互融互衬的叙事策略,彰显出作者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
复调小说理论,原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解读叙事文本的话语,认为复调小说的主人公不只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或对象,也并非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表现者,而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复调小说不是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有不同意识的世界;复调小说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这些观点在《燕食记》里都得到了具体践行。对此,葛亮接受记者采访时有明确的表态:“我希望借由这个文本去体现某种在文学深处的一种对话性,就是一个当下的人如何和他对望的历史之间产生一种砥砺思辨乃至于相互之间融通的关联。这也构成了这个小说有关于非虚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复调。”
非虚构书写与虚构书写的交织缠绕和融通关联,构成了《燕食记》的第一重叙事复调。小说是以一种故事中的主人公与创作主体(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的方式来构建和完成叙事的。非虚构书写主要落实对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经历和情感指归的那些写实性叙述描摹层面,而虚构书写主要践行于创作主体作者对故事中人物经历的那些时空的浪漫性想象联想层面。如小说的引首“一盅两件”,开篇就巧妙设置了一个承担穿针引线功能组织叙事的角色(第一人称“我”),这实际上就是作者葛亮本人。且不说其赴港读书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学者身份,与葛亮来历相同,就连“我”特意申请的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亦和葛亮做过的科研课题和参与过的文化对谈、访谈的内容有密切的关联性。这个“我”,是一个自由游走于小说上下两阕间的“自由人”,按照故事讲述(上阙主讲师傅荣贻生;下阕主讲徒弟陈五举)的需要,“我”不仅自由调度这师徒二人在上下两阙间时而单独出镜,时而交集同行,更随时随事与他们俩、也与故事中的其他角色进行有关时局、有关美食、有关社情民意的交流,能达成共识当然皆大欢喜,各持己见也能互为参照。“我”的自由调度使读者在阅读《燕食记》这一虚构文本时,获得了某种有实人在场的真实感,而“我”和故事中人的平等对话,则使整个故事的讲述获得了叙事的内在张力,成功构建起一个“有相同价值有不同意识”的丰饶艺术世界。
与此同时,作者让诸多人物在书中充分展示自己的生活经历,并随时随地对身处的社会环境、人际交往、日常生活体验进行自己的考量、反思甚至质疑。如慧生后来对自己和月傅当年情同手足、自己与叶凤池结为夫妻的那一段段过往交集,时而会生出惶惑:再来一遍,我还会那样做、那样选吗?时而还发出质疑:若不会,又会怎样呢?而荣贻生、陈五举、叶凤池、向锡堃等人,甚至可以称之为是意识相对独立的“思想家”,似乎就是他们一直在推着历史事件展开,推着社会风气前行,甚至引领着港岛的美食风尚。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隐去了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理想,恰恰相反,葛亮在给予笔下人物以极大自由的同时,更想呈现一个当下之人(作者本人),秉持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究竟应该怎样去谛视历史和表现历史。
譬如,当小说在以上帝视点来客观描摹梳理各色岭南美食的发展历程,讲述香港和岭南美食坊间的真人真事,再现以向家、何家、司徒家为代表的家族变迁过往的同时,葛亮总是会适时插入一些以第一人称主观视点(作者视点)为中心展开的关于个人或家族故事细节性的虚构叙述,让自身直接参与对历史时空的阐释和勾画,并即时跟进现实自我对此的共情与认同。这实际上既是叙述主体对历史的呼唤,亦是历史给予叙述主体的回馈,呈现出一种非虚构与虚构的叙事复调。
女性形象的精神气质与各色美食的物格之间的互文性,构成了《燕食记》的第二重叙事复调,即人品与物格的复调。似乎是与“世界的一半是女人”的社会性别定律相呼应,《燕食记》里女性形象的塑造,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绝对不显弱势。且不说用力甚多的慧生、月傅、凤行们,就是用笔较少的如司徒云重、颂瑛、露露们,亦都既体现着女人之为女人代表着“民间”与“日常”的共性,又活跃着各自的鲜活个性,堪称已达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佳境。如果没有她们,小说的人物塑造会留下较大的遗憾。
张爱玲曾对女性这种“民间”与“日常”的特性,有过精辟论述:“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葛亮显然对女性这种“民间”与“日常”特性,及其由此给予男性的包容和呵护、给予社会尤其是给予日常生活的根性支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这部小说里,葛亮始终紧贴人性和性别的内在肌理,去描写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既写出了男性天生就属于政治和经济,属于宏大和沉厚的特性,又写出了女性更安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民间”与“日常”的特性。
在《燕食记》中,时光的打磨让女性这种“民间”与“日常”的气韵,逐渐化合为生活习惯乃至近乎本能的坚忍而坚韧的生活方式,一旦深入骨髓,便能够举重若轻地应对各种社会动荡和文化变故。所以当月傅和慧生九岁时被买进“般若”尼庵,原有的岁月样态被打碎,习惯的“日常”亦被挤压殆尽,继而香港又沦陷为日军占领地之后,她们也会竭尽所能去应对一切变故,想方设法在画艺、棋艺、厨艺方面努力修为。尤其是她俩合作创制出的“般若素宴”,更是闻名整个港城,从政界要员、到商贾显贵、再到文化名流皆趋之若鹜。于是,被这种气韵浸润的先是“般若庵”、后是贻生成长的向家和叶家,以及最终成就技艺的同钦楼,便成了一个个“兼容并包”的中华精神有机体,游刃有余地消化着传统及其外来文化,表面看起来很有些现代甚或后现代,但根性又总能追溯到传统的精神血脉。作者一方面以月傅、荣慧生、何颂瑛、戴凤行、月明、司徒云重等女性的气质和品性,来指代岭南美食或清雅、或妩媚、或灵俏、或朴拙、或冷冽、或热郁、或疏离之气韵,另一方面又让岭南美食的繁复物格,在这些女性关于中国文化既传统又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想象中,占据了与社会、时局、政治、经济话语不即不离而又血脉相连的重要位置。并由此构建起人物形象与美食技艺的格物复调。
《燕食记》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的对话复调,则是经由以“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故事叙述方式得以建构的。虽然故事的讲述是由“我”要完成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而拉开了帷幕,但实际真正开启故事大门的钥匙,是“我”用搜索引擎搜到的一篇题为《风月尘尘话流年》的网文,网文署名“越秀俚叟”。“我”沿着这条线索找到一个年轻姑娘,得到一本她太爷爷写的书《羊城钩沉》,书中偶然掉落下一张信笺,“宣纸洒金,已黯淡成了点点灰污。上面密密地写着小楷。抬头是‘敬启者:般若素宴’,跟着一列列的,读下来,竟是道道菜名。末尾的落款是:慧生拟,月傅书”。于是,“我”找到了故事的主角荣贻生(小名唤作阿响),故事正式进入讲述环节。
实事求是地说,仅仅是一个故事开端,我们就很难分辨其中哪些是确有其事的“实”,哪些是文学想象和联想的“虚”。因为这个“我”,本身就是一个处身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却自由穿行在现实和历史过往时空中的文化研究者。追溯和还原历史上某些事件留下的印痕,对“我”来说是一份为了寻绎和确证一个伸向无意识深处的标尺,或者说是为实现对历史记忆的一种现代编码和当下定型的工作。因此这种追溯和描摹,就可以名正言顺而且理所当然地放飞艺术想象力和联想力,任由其衍生出无限广阔、无限丰饶、无限具实又无限浪漫的细节,建构起一个足够安放风云际会的社会背景、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杂树生花式的人际关系、广阔深密的心理意识流动的文学空间。毫无疑问,它既是虚的又是实的。其“虚”,是指在创作主体的想象力和联想力的推进延绵中,所有的过往时空都可以沿着或再现或扭曲或畸变的路向重新构建。其“实”,是指创作主体的所有思绪毕竟都牵系在创作主体“在当下现场”的肉身之上,阳光灿烂的愉悦重温也好,心理创伤的再度撕开也罢,定格狼性的反抗姿态也好,追忆温软的春风化雨也罢,都可归属到文学的合理想象范畴内。当这些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被有机缝合为一个完整叙事空间的时候,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族群、此时与彼时的密切呼应就得以宏大而具实、精深而鲜活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燕食记》“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故事叙述方式,本身又构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复调。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葛亮|《燕食记》
《燕食记》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以宏阔的笔力书写了岭南的饮食文化。小说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笔触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小说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以细致入微的文笔,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稿件初审:周贝
稿件复审:王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