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野千鹤子,成为“上野千鹤子” | 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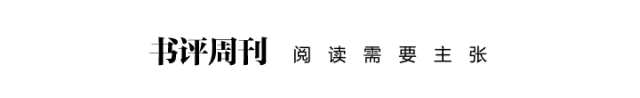
一位自陈“曾经无法接受自己是个女人”的女性,如何成为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开创者?
2019年,一段东京大学新生开幕典礼上的演讲,让上野千鹤子走进了中国人的世界,人们也开始在阅读中关注她的研究:《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始于极限》……而她的成长历程,却超出一般人对于学者的想象——她成长于女性哪怕读完研究生也没有工作可做的时代,她觉得在大学里教社会学一点意思都没有,她曾经想象过当客人寥寥的冷清酒馆的老板娘,她自陈自己曾经是“厌女”的精英女性……
我们带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在2021年圣诞前夕,采访了这位一直在一线抗争的女性主义学者,我们想知道,女性主义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如何与女性学相遇,又如何开创了日本女性学这门学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知道上野千鹤子,如何成为今天的“上野千鹤子”……
以下是我们对上野千鹤子采访全文的1/3,完整版将收录于《开场:女性学者访谈》,如果你曾经关注过我们的“女性学者访谈”系列,是的,它结集出版了,收录了我们已发布的所有采访的完整版(已发布的采访均为删节版)与未发布的采访。购买方式见文末,限期、限量五折特惠预售中。
●点击下图,了解预售详情。



女性学者访谈系列
No.8
(节选)
上野千鹤子
■ 1948年生于富山县。为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代表人物。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NPO组织“女性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长。
■ 著有《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不惑的女性主义》(不惑のフェミニズム)《女性的思想》《一个人最后的旅程》《始于极限》《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等。2011年荣获朝日奖,2020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采写 | 青青子
特约译者 | 陆薇薇(东南大学日语系主任)
在过去几年,当人们提到女性主义或是讨论性别议题时,上野千鹤子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如果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波伏瓦将西方女性的生命处境抽丝剥茧,一册《第二性》流转西东,为女性找到了生活的症结,或者说,一种命名,半个世纪后,上野千鹤子便是那个手持利刃,为东亚社会的父权结构剔骨的人。
即便你没读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一定看过她在2019年东京大学新生开幕典礼上的演讲视频,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这一句——
上野千鹤子
“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作为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者之一,上野千鹤子从女性主义出发,构建“家庭-市场”“生产方式-再生产方式”“父权制-资本制”的理论体系。作为日本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上世纪90年代,她着手进行“慰安妇”与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等问题的研究,就此与吉见义明等学者展开过几轮激辩。世纪之交,年过50岁的上野千鹤子开始研究照护问题,出版《照护的社会学》《一个人最后的旅程》等。尽管研究课题一再变化、拓展,但她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始终如一:“我一直在思考女性的‘无薪劳动’问题”。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上野千鹤子的采访节选,内容为完整版本的1/3。我们的话题从女性学开始,聊到她一路走来的滴滴点点,还聊到她的学术思考与坚持。当然,我们还聊到红发和愤怒的象征(笑)。
最后,谈及对于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女性有哪些期许时,上野千鹤子沉思了一会儿,说:
“女孩总是容易当优等生,当老师的宠物。毕竟,不辜负周围人的期望,也是女性的‘美德’之一。而优等生会有这样的习惯,习惯察言观色,尽量满足老师和父母的期待。有一些女性学者也是如此。
但我认为,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使它不能为你带来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原创性是极为关键的,模仿别人毫无意义。所以首先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得是失,我都希望她们能够坚持下去。此外,女性的人生中有许多曲折,即使因恋爱、结婚、搬家、生子、育儿而暂停了学术研究,学问也还是会等待着你的。
因此,我希望女孩们即使一时中断了研究,也能再次出发,继续下去,因为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定年龄界限,学问会一直等待着你的。
很棒吧?做研究是很有趣的。”
点击视频
观看上野千鹤子的采访视频片段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Unveiled:Women in Academia
NO.1
即使父亲疼爱我,
那也是一种对待宠物式的爱
新京报:就你个人而言,是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觉知的?一个可能冒犯的问题是,你是否曾为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过困扰?或者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内心的“厌女症”的?又是如何与它持续做斗争的?
上野千鹤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小时候就意识到了,我的父母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我的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母亲则是位任劳任怨的专职家庭主妇,夫妻关系并不和睦。作为长媳,我的母亲和婆婆一起生活,那时候我以为,孩子们长大后,都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当我想到自己长大后会过和母亲一样的生活时,觉得这太糟糕了,我受不了。这样一来,不仅我妈成了反面教材,而且我开始厌恶自己身为女性这件事。另外,我有兄弟,所以我还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明显的女性歧视。我的兄弟们受到了严厉的管教,走上了人生的正轨,他们都成了医学专家。而我,没有被期望做任何事情。因为是女儿,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即使是像社会学这样的“无用”工作。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清楚地感受到了不同,所以虽然我也得到了宠溺,那我也是女儿。我的父亲很疼爱我,但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对待宠物式的爱。我在家里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我变得讨厌自己的女人身份,也就是所谓“厌女”。
自青春期以来的十多年里,我一直无法接受自己是个女人。所以我不擅长同女人打交道,觉得和男人在一起要容易得多,我表现得像一个“名誉男性”,也就是“假小子”。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而当我遇到女性主义时,它拯救了我。因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基于女性爱自己身为女性这一事实的思想。
我经常被问:上野女士你“厌女”吧?我会回答说:Yes。如果不“厌女”的话,我便没有理由成为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女性主义者是那些与“厌女症”作斗争的人。现在,随着年岁渐老,我可以接受我的女性身份了,并且爱上了它。或者更进一步说,我变得不想成为一个男人。
新京报:我很好奇,你最早接触女性学的契机是什么?
上野千鹤子:在我年幼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女性学,直到二十多岁,我才接触到它。对我来说,女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可以将自己作为研究的对象。
大学时我主修的是社会学,但始终找不到立足之地。直到开始从事女性学研究,我才有了积极性,迫切地想去做些什么。女性学,就是将女性经验诉诸语言与理论的学问。对我来说,身为女人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谜,所以很自然地想在这方面下功夫。
不过,在那个时候,女性学还没有被公认为是一门学科,所以我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之后能靠它谋生。
新京报:你是日本女性学的开创者,影响了女性学/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日本的学科建构过程。能否谈一谈,日本的女性学、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上野千鹤子:把women’s studies这个词翻译成“女性学”的,是井上辉子。但women’s studies的本义,是跨学科的女性研究。而“女性学”的译法使它看起来是一门学科。因此,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个误译。但我将其称为创造性的误译,因为它更容易被生长于汉字文化圈的人们所理解。
井上辉子还对女性学下了一个定义——“女性的(of women)、由女性开展的(by women)、为女性进行的(for women)学术研究”。这一定义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一些人看来,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是没有问题的,但“由女性开展的”“为女性进行的”部分则颇为不妥。不少男性学者抗议说,如果说这是由女性开展的学问,那么男性是不是不能从事女性学研究?同时,他们认为,为女性进行的学问,使这门学科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不够中立,只能将其称作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称作学科。
但井上辉子完全没有屈服。她指出,“由女性开展的”,意味着女性从研究的客体转变为研究的主体;而“为女性进行的”,意味着女性学要为妇女解放做出贡献。井上的宣言表明,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学如同车的两个轮子,是不可分割的,女性主义是女性解放的思想与实践,女性学则是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
我认为,这一宣言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出之前的学问都是“属于男性的(of men)、由男性开展的(by men)、为男性进行的(for men)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回应那些男性学者说,男性即使不从事女性学研究也无妨,你们可以研究自己的“自画像”。
但井上辉子的定义也带来一个问题:女性学是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体系中添加了一个关于女性的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女性对它感兴趣,男性几乎完全提不起兴趣。在他们看来,你们女性从事女性学的研究就好,和我们没关系。因此,主流学术界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有鉴于此,对这点十分不满的女性学研究者开始改变女性学的研究范式,使其不再仅仅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将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gender。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界诞生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一词。没错,女性学研究一直在有女性显影的地方研究女性,但也有女性缺席的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这些公共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由男性研究者还是女性研究者开展,都会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研究。如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剖析为什么这些行业没有女性参与其中。如此,公共领域如何被男性化的问题就成为性别研究的课题。
事实上,当你使用“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在人类构建的社会里,没有不涉及性别的领域,所有领域都能成为性别研究的对象,没有什么领域是性别研究囊括不了的。而且,“社会性别”是一个非日常的学术术语,一经确立,性别研究这一学科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性别研究不是一门学科。
在此,我还想补充一点,过去有些人会说,我不是女性解放运动者,但我是女性主义者。之后,又有人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我是性别研究学者,因为性别研究让人觉得更学术。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女性主义和女性学是不可分割的,性别研究也同样如此。性别研究是从女性学中诞生的,所以我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列为“女性学/性别研究”。
NO.2
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
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
新京报: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解放浪潮很多都孕育自学生运动。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一书中,你回应了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对你参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评价。具体来讲,你和小熊英二(以下简称“小熊”)的分歧主要来自哪里?这场运动如何影响了你的学习经历和生活?
上野千鹤子:小熊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矮化为学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忽视了日本的学生运动有更加宏大的社会史背景。当时日本学生运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反战。在日本战后的社会运动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反战和平思想,学生运动也不例外,人们反思日本的重创、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此外,学生运动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轰炸机是从日本基地飞去越南的,日本成了加害者的同谋,也是加害国。学生的矛头正是指向这里,他们深刻地反省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坚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帮凶。
我也希望中国人民能了解,在战后的日本,反战和平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日本不仅有受到战争重创的被害人意识,日本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加害人意识也非常强烈,而越南战争更是刺激并强化了人们的加害人意识。
尽管有这样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背景,小熊却将它矮化了,他将学生运动归结为学生们在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你和小熊的区别是不是亲历者和未亲历者之间的区别?
上野千鹤子:历史书写本就是后来人(非亲历者)的特权。未亲历者声称历史是什么样的,这是对历史的暴力扭曲,虽然他们施加暴力的方式各不相同。我对小熊研究的不满之处,在于他的方法论。学生运动发生在半个世纪前,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有很多亲历者活着,但他却没有采访其中的任何一位。如果所有相关人士都离世了,那就只能依靠书面记载,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活着,他却采用了所谓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小熊的书中,几乎只有男性出现,仅在最后一章提到了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田中美津,但是他却从没采访过她。他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解读非常浅显。女性解放运动到底是什么,他几乎不明白。所以田中美津提出了强烈抗议。她当然要生气。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邹韵/薛梅
版本: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11月
从时间顺序来看,是先有学生运动,再有女性解放运动。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最初的女性解放运动领袖,大多是被男性学生运动家背叛的新左翼女性运动家。当时,那些男性同志的目标是革命,而革命是遥不可及的非日常世界,为了那个世界,要牺牲当下的日常,牺牲自己,为革命献身,可谓一种男性运动的英雄主义。女性对此提出了批判。自己每天要吃喝吧?有了孩子,还要抚养,育儿时片刻不能离开,这就是日常。所以牺牲日常不是实现非日常的一种手段,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那么遥不可及的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于是,日常成为战斗的中心,女性解放运动者们要求男性将战场从非日常转向日常,比如“谁在替孩子换尿布?”的论争。而这,便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个人即政治”的实践。
女性还对此前的日本反体制运动提出了批判。日本的革命运动大多采用绝对服从的军事组织形式。以革命为目标的人,是革命士兵。士兵要做到绝对服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对这个组织体系也进行了质疑。比如认为不应该在组织中设置唯一领导人,组织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式的,等等。而这样重要的背景,小熊却全然不知,也不去问,不去写,他没有理解女性解放运动是如何从学生运动中诞生的,其必然性又是什么。
NO.3
女性的变化令人惊喜,
男性的变化却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在《厌女》这本书中,你深入剖析了弥散于日本社会中的“厌女症”,同时,你也提到,“厌女症”不只是男人才有,女人也会染上。自《厌女》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它已经成为人们解析当下性别问题的“圣经”。我很好奇,就你这几年的观察来看,日本社会的“厌女症”有哪些新的变体与表现?
上野千鹤子: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时代变了,针对“厌女症”的各种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揭发、抗议、签名等运动,参与者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同时,这些运动大多以线上形式展开,降低了参与门槛。无论是名人,还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都可以随机发起网上签名,取得成果的也有不少。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年青一代的女性对各类“厌女”现象不再容忍,也不再忍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前任会长、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辞职事件。他当时说了一句歧视女性的话,结果被迫辞职了。这说明,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如果他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也有可能踩上地雷把自己“炸死”。
关于森喜朗被迫辞职,有些人说是因为外部(海外)的压力,但比起外部,日本国内女性的抗议更为激烈,他这才不得不辞职。这是一个日本女性取得成功的故事。
另一方面,男性的变化正朝着令人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自己已无法轻易享有曾经的既得利益,因此,部分男性的受害者意识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对女性进行攻击。如今,日本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类男性针对女性主义的恶意评论,日语里称它们为“狗屎回复”(kuso-reply)。
这种男性的攻击性不仅出现在互联网上,还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最近发生的小田急捅杀女性案,就是一种“厌女”谋杀。杀人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杀害理由竟然是他无法原谅那些表情看起来幸福的女人。男性的这种变化很可怕。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新京报:你曾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女性主义运动成果并没有延续到更年轻的一代。在你看来,断裂/未能传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传承这些抗争的遗产?
上野千鹤子:当我问现在的年轻人,你是从哪里得知女性主义的?他们回答我说,是通过艾玛·沃特森在联合国的演讲,还有人说是从韩国学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年轻女性是从外国学到女性主义的。我当时很失望,我说日本也有女性主义。
之所以未能延续,我想是因为传承人的断层。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结婚和生育的女性作为地方上的草根女性主义者,成为各地女性活动中心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时的日本妇女没有机会外出工作,她们或是专职的家庭主妇,或是做做兼职的主妇。她们只能在下午五点钟之前待在外面,之后要回家做家务,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前的女人”;而年轻的职场女性只有五点钟之后才能下班,所以我们称她们为“五点钟之后的女人”。这两类女性群体错身而过,没有时间上的交集,也无法在某个地点相遇,她们完全是轮流地出现在社会空间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日本各地的女性活动中心都非常活跃,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设立女性活动中心,因为当时经济很景气,而且如果地方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女性活动中心,会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说明负责人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于是,地方政府与地方草根女性主义者迎来了蜜月期。
蜜月期的顶点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年在北京郊外举办了非政府人士参加的NGO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妇女参加了该论坛,其中六千人是日本女性,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大家去中国很方便,又对中国很感兴趣。我是自费去的,但这六千人中很多是地方政府出的资。不过那是最后的高峰,在那之后,就出现了倒退。
当时这些去北京参会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而在同时期,日本职业女性的比例已经大幅增加,但这些年轻的职场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没有交集,导致前一代的实践经验无法传递给年青一代(比如与我对谈的田房女士)。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是电视时代,作为男权媒体的电视在综艺节目中经常嘲弄取笑女性主义者,试图告诉女性,如果她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被欺负,就会遭到可怕的对待。正是这种对于若与男人为敌就会吃亏的恐惧,使她们放弃了抵抗。我认为,当时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负面认知也影响了女性解放运动之后的一代人。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因为“慰安妇”问题,日本对于女性运动的支持开始出现巨大倒退。1995年,日本政府带着女性亚洲和平基金(又称国民基金)去北京参加了妇女大会,该基金源于一个模糊官民立场的构想:由民间募集资金赔偿给受害的原“慰安妇”,期间产生的事务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可是没想到,第二年,一个名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团体诞生了,他们开始篡改历史,要将“慰安妇”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同时,日本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地方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再也负担不起女性运动的经费。二十一世纪初,倒退进一步加剧,女性主义者被指责为破坏家庭、破坏文化传统,遭到无数攻击。
近年的女性主义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她们是全新的一代,她们不知道之前的女性主义者遭受过怎样的抨击。与此同时,另一个大的变化是出生率的下降,也就是“少子化”现象,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被精心抚养长大。因此,受到宠爱、在男女混合学校长大的女孩,觉得自己不应当遭到不公的待遇,所以她们决定不再忍耐。我认为这里也有代际变化的影响。
NO.4
过分强调研究者的学历,
扩大了实践运动与学术研究的距离
新京报:目前,日本的性别研究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相较于创立之初,有哪些变化?所处的研究环境又如何?
上野千鹤子:性别研究现在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可以在大学里任职并获得研究经费。我们这一代是开拓的一代,我们培养出来的后生力量现已成为性别研究的中坚,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我们的年代,主要开展的是宏观研究,关注性别研究中的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y)、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而下一代的研究人员则开始关注更为细分的领域,如性别法学、性别经济学等。而且,她们强调实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此,性别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正如我过去所写,一方面,仅通过性别这个变量已经不能分析所有问题了;另一方面,除却性别,也不可能分析任何事情。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时代。
在学术领域,女性学的学科建制取得了进展,性别研究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一方面,由于性别研究的对象已经多元化,研究领域不断细分,由此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如性别法学会、历史学与性别学会、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加强性别研究者之间的联结变得更加有必要。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女性运动家和女性学者非常接近,有人从运动家成为学者,也有很多人既是运动家又是学者。但随着性别研究的制度化,运动家和学者之间出现了鸿沟。你必须有学历才能在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就无法成为一名学者。日中韩都是学历社会,大家注重海外,特别是在欧美留学的经历。要想在本国的大学教书,就必须在国外获得学位。那些拥有留学经历并取得学位的人,比始终在日本国内学习的人更有优势。这样一来,那些对日本本土情况不甚了解,但在国外学习过的学术精英反而可以在日本获得教席。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
新京报:是的,当然也有一些高校教师是从中国的名校毕业的。
上野千鹤子:韩国最顶尖的学府是国立首尔大学。但据说即使你从那里毕业,你也不可能成为这所大学的老师。
日本在语言上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相较中国、韩国来说,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只是,如果你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就当不了大学老师,只有就读名校的女生精英才能成为下一代的性别研究者。我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她们在做很伟大的研究,但我认为,这样会扩大运动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距离。
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网站里,有一个“女性学/性别研究博士论文数据库”(https://wan.or.jp/general/category/女性学ジェンダー研究博士論文データベー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已有多少积累与增加,研究主题和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总体来讲,如今研究者的层次和水平都在提高。
NO.5
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女性话语在前,
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学者/写作者/女性形象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我通过陆薇薇老师得知,你写了一本叫作《女性的思想》的书,可以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吗?
上野千鹤子: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女性前辈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阅读她们的书籍时,会觉得女性写的书果然还是比男性的书更能让我产生共鸣。森崎和江是我这本书中介绍的女性前辈之一,她生于女性解放运动之前的朝鲜半岛,后来回到日本,是一个出生于日本的殖民地、视日本如异国的日本人。日本战败后,许多日本人试图抹去历史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森崎那时便宣称自己今后不再相信男性话语,而要只身一人思考一切问题。
虽然出生在朝鲜半岛,森崎和江的身上仍深深烙印着日本的原罪。自己的祖国侵略了从小哺育她的朝鲜,她一直为此深感内疚。拥有她这样的前辈是我们的荣幸,我从中受益良多。
我们的女性前辈们艰苦奋斗,为我们创造出了许多经验与思想财富。例如田中美津,她被称为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旗手。还有富冈多惠子和石牟礼道子,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表达女性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女性话语在我们面前,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她们有恩于我。
我不仅从日本女性那里学到了这些话语,还从国外学者那里借鉴了许多。她们当中有很多人自称女性主义者,她们努力思考、笔耕不辍、积极行动,我从她们那里获益匪浅。因此,不论女性主义者之名有多受争议,我也不会放弃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这是为了告诉那些前人,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中国的女性们也一定有这样的女性前辈吧?我想,读了我的《女性的思想》后,你们一定会想写一本中国版的《女性的思想》。

《女性的思想》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陆薇薇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
新京报:作为性别研究学者,你曾受到过来自外界的刻板评价吗,比如在中国,性别研究经常被认为是只有女性才会做的研究,做性别研究的女性研究者也经常被认为只能做性别研究?你是否曾为此而烦恼?到目前为止,在学生生活、教学生活、研究和写作中,你是如何处理性别身份、研究内容与外界期待的?
上野千鹤子:这也是个有趣的提问。我被称作“日本最可怕的女人”。但这样的称呼并没有困扰到我。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讨厌的男人靠近我了,我也很少遭遇性骚扰。他们更不会小看我,而是会承认我有比他们厉害的地方。这样很好。虽说认为女性主义者厌男是一种误解,但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碍。
性别研究在学术界时常被边缘化,更有甚者,认为它是愚笨的女人从事的二流学问。而我之所以被称为“日本最可怕的女人”,是因为我在多次论战中取得了胜利,在他们眼中,我擅长理论、头脑聪明。我证明了,做性别研究的并不都是蠢笨的女性,他们的想法多么可笑。
人们对女性主义者往往有刻板印象,他们认为我们不受男人欢迎,是丑女,不打扮,而这些我也能一一击破。我个人就很喜欢时尚。我这样打扮也是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就不能很时尚?虽然我现在是短发,但三十多岁时,我是打扮得很女性化的,比如特意留长发、穿有褶皱花边的衣服。所以,当有人说:“什么?女性主义者也会打扮?”我便告诉他们,打扮会让人心情愉悦!他们还会阴阳怪气地说:“你是不是不甘心呀?”但我认为,“不甘心你也打扮就是了”。
新京报:近年来,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你一直以一头红发示人。红色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我有一个猜想,红色代表着愤怒,而在之前的采访中,你也提到过,愤怒是你持续行动的动力。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你如何理解“愤怒”对于女性的力量?
上野千鹤子:这有点过度解读了(笑)。我之所以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的头发慢慢白了,我想把它染上颜色。但我不想要金黄色,因为我不想自己看起来像个西方人。另外,我还考虑到,自己这个年纪要是有一头乌黑的秀发,那反而会是很恶心人的事。我想清楚地告诉别人这是染上的颜色。话说回来,绿色、蓝色、紫色可能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关于愤怒这点,海尔布伦(Carolyn G. Heilburn)写了一本叫《女性的自传》(Writing A Woman’s Life)的书,里面写道:“愤怒是女性最禁忌的情绪。”而女性被允许拥有的情绪,是羡慕、嫉妒、恨,因为这是弱者对绝对无法对抗的强者所抱有的感情。而愤怒则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位置对等之人的侵犯时所产生的一种正当的情绪。我认为女性应该多表达愤怒之情。前些日子,有一个面向女性的讲座,是关于愤怒情绪管理的,教大家如何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我反倒觉得比起管理愤怒,我们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表露愤怒。
女性可以再愤怒一些。愤怒也有愤怒的方法,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愤怒的方法。■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Unveiled:Women in Academia
完整余下2/3对谈内容
收录于《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完整版余下两万余字内容提要:
“伊藤织诗之后,上野千鹤子如何反思日本#MeToo运动的发展?”
“有关照护研究,上野千鹤子为何驳斥了凯博文?”
“照护研究如何影响了上野千鹤子对死亡的看法?”
“上野千鹤子如何描绘当下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状态?”
“上野千鹤子如何解读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学术之外,上野千鹤子竟然喜欢看《爱的迫降》?”
点击书封进入预售链接
11位投身人文研究的女性学者
11篇再现完整学思历程的深度对谈
从40后到80后
直面一代又一代女性学者的性别困惑
“没有人逼迫我研究女性的生活,我就是想要以女性生活为研究对象……”
“我花了很长时间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当我遇到女性主义时,它拯救了我……”
“我一直很反感一种说法——你是一个女性,你只能做和性别相关的研究。”
“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
投身学术
纵然仍需面对性别难题
但学术亦带给她们
前所未有的自由
点击图片进入预售链接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预 售 开 启
11/10-11/16
“双11”特惠
限时五折 限量预售
68元34元
当当网下单独享赠品2023年开场月历卡
进入思想的另一半天空
购买《开场:女性学者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