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关于《红楼梦》,这些大家都说过什么
【编者按】
虽然曹雪芹生卒年迄今仍无定论,但2015年,多方仍在用各种方式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澎湃新闻特刊发一组稿件,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以及他的那部经典之作——《红楼梦》。
在四大名著中,唯有《红楼梦》研究有了专用名词:“红学”。“红学”从清代开始至今,已延续了100多年。期间,文史哲等多路大师都有涉及“红学”研究,他们或评论,或考证,或索隐,甚至还续写和模仿创作。一或源于《红楼梦》的内容旨趣丰富,把玩不尽;二或因为《红楼梦》于各个文化层次皆可阅读欣赏,在大众中的流行程度或又激起了学者、作家的“红学”兴趣,致使如今看来“红学”蔚然大观。
下面看看都有哪些大家曾做过“红学”研究,罗列一下他们的“红学”代表作,以及关于《红楼梦》他们都说过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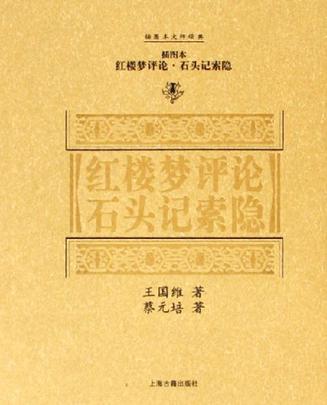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而,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冥,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红楼梦考证》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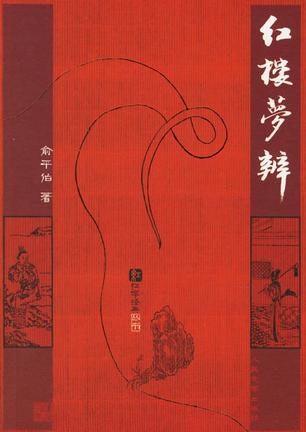 俞平伯:《红楼梦辩》
俞平伯:《红楼梦辩》
从高鹗以下,百余年来,续《红楼梦》的人如此之多,但都是失败的。这必有一个原故,不是偶合的事情。自然,续书人底才情有限,不自量力,妄去狗尾续貂,是件普遍而真确的事实,但除此以外,却还有根本的困难存在,不得全归于“续书人才短”这个假定。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要体会《红楼梦》之所以为伟大与博深,单看人们对它的认识演变的整个过程,也就不难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说来话长,应该有一部“红学史”。这里只谈一点。《红楼梦》在清代,不止一次遭禁遭毁,列为“淫”书。有人甚至有过这样异想天开的念头:把《红楼梦》打发到国外去,拿它的“毒素”去回报洋商们所给予我们的鸦片毒害——现在看来,真不愧是“奇书”必有“奇用”!然而这正代表当时一般正统士大夫对它的认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顾颉刚(没有专著的红学家) :《红楼梦辩·序》
《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
读《红楼梦》的人,或偏于黛玉,或偏于宝钗。偏于黛玉的人,也必喜欢晴雯,而恶宝钗,兼恶袭人。女子读者当中,做贤妻良母好媳妇的人,却常同情于宝钗,而深恶晴雯,完全与王夫人同意。这里头就有人生处世的真理存焉。大抵而论,阮籍、嵇康之辈,必喜欢黛玉,喜欢晴雯;叔孙通二程之流,必喜欢宝钗,而兼喜欢袭人。袭人后来嫁蒋玉函,许多男人读者唾骂,那是另一件事,是理学妖孽之所为,因为与理学之贞节观念冲突。大概袭人若终身不嫁,或学鸳鸯上吊自尽,必博得那些儒者的恭维。这是话外不提。我认为袭人之行为人品,比大观园任何男子还强。何以《红楼梦》的男子,都那样不行,都是泥做的(贾政在内,贾赦贾琏,更不必说),这又是话外。
吴宓:《<红楼梦>新谈》
《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W.M.Thackeray之The Newcomes(注:萨克雷名著《纽卡姆一家》)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
 茅盾:《节本红楼梦·序言》
茅盾:《节本红楼梦·序言》
《红楼梦》是没有扭捏做作的。全书只写些饮食男女之事,并没有惊人的大事,但同类性质的书往往扭捏做作出许多“惊人之笔”,希望刺激读者的感情,结果反令人肉麻。《红楼梦》 并不卖弄这样的小巧。它每回书的结尾处只是平淡地收住,并没留下一个“介绍词”引诱读者去看它的下一回书。但是读者却总要往下看,不能中止。《红楼梦》 每一回书中间也没有整齐的“结构”。它只是一段一段的饮食男女细事,但是愈琐细愈零碎,我们所得的印象却愈深,就好像置身在琐细杂乱的贾府生活中。“稚齐的结构”自然是好的,不过硬做出来的“整齐的结构”每每使人读后感到不自然,觉得是在“看小说”,觉得“不真”。
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载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十二月号)
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我若是写出来一两个站得住的人物,我就喜欢得要跳起来。我知道创造人物的困难,所以每逢在给小说设计的时候,总要警告自己:人物不要太多,以免贪多嚼不烂。看看《红楼梦》吧!它有那么多的人物,而且是多么活生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伟大的作品;它创造出人物,那么多那么好的人物!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世界名著中,一部书里能有这么多有性格有形象的人物的实在不多见!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
《红楼梦》的长处,在处理过去一时代儿女纤细感情,恰如极好宋人画本,一面是异常逼真,一面是神韵天成。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曹雪芹佚著浅探》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曹雪芹佚著浅探》
《红楼梦》我在青年时代就读过,但对它的兴趣不大。倒是王国维慨叹不知《红楼梦》作者的身世、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考证,引起了我对这部书——实际上是对研究它的作者——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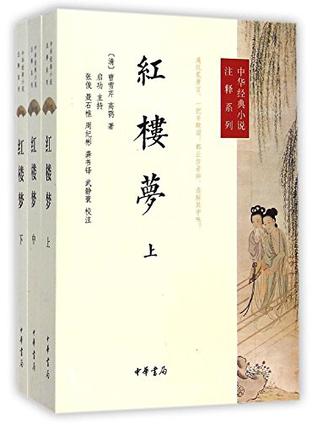 启功:《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
启功:《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
宝玉的婚姻既由王夫人做主,那么宝钗中选,自然是必然的结果。这可以近代史中一事为例:慈禧太后找继承人,在她妹妹家中选择,还延续到下一代。这种关系之强而且固,不是非常明显的吗?另外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血还家”,更犯大忌。血缘太近的人结婚,“其生不蕃”,这本是古代人从经验得来的结论,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
 何其芳:《何其芳论红楼梦》
何其芳:《何其芳论红楼梦》
伟大的不朽的作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关于它的深入人心,清代的笔记里有过一些故事。有一位作者说,他从前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听说有某商人的女儿,貌美,会作诗,因为太爱读“红楼梦”了,后来得了肺病。她快死的时候,她父母把这部书烧了。她在床上大哭说:“奈何烧杀我宝玉!”又一位作者说,苏州有个姓金的人,也很喜欢读这部小说,他给林黛玉设了牌位,日夜祭祀。他读到林黛玉绝食焚稿那回儿,就呜咽哭泣。这个人后来竟有些疯疯癫癫了。这些故事是比较奇特的,未必都是真事。前一位作者更是企图用那个故事来反对“红楼梦”。然而这些故事却也反映出来了这样的事实:“红楼梦”的艺术异常迷人,它所创造的人物异常成功,它对许多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
我喜欢红楼梦里传写人物的生动手法。还没有说话,就听见那人的声音了。红楼梦里的人物的出场入场,一颦一笑,来踪去脉,口角眉梢,心头话尾,舌尖牙缝,歌哭笑骂,正经,胡调……没有一处不是活灵活现。
 宋淇:《红楼梦识要》
宋淇:《红楼梦识要》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描写女主角伊丽沙白,读者可以在读完前三分之一时就已经有极清楚的印象:富于幽默感、俏皮、可爱,至于以后无非是她对男主角达赛的偏见逐渐消除、由恨变成爱,我们看不到她性格上的新特征。这当然是传统小说的描写方式。《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技巧就丰富复杂得多。即以探春而论:第3回,探春问宝玉写黛玉题名颦颦有何书典;第18回,元春省亲时,探春写诗;第37回,探春起诗社;第40回,探春的居住所在,由其室可观其人;然后到第55、56回,探春理事,她的见解、才华、能力才豁然呈现。当然在这以前及以后,仍有很多枝节的描写,拼成一幅完整的肖像。读者不由得不佩服曹雪芹的耐性:他是如此胸有成竹,能够忍到全书一半时,才将重要角色的性格完全描绘出来!同样的,我们读《金瓶梅》时,就没有这种感觉:西门庆、潘金莲、春梅等的思想、感情、欲望几乎没什么新的发展,只是重复已知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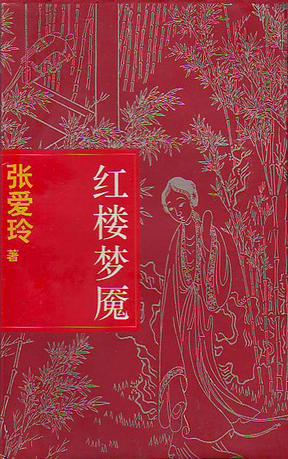 张爱玲:《红楼梦魇》
张爱玲:《红楼梦魇》
《红楼梦》的一个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从前的人开口就谈《红楼梦》,正是因为谈言微中,足以自喜,而听者也觉得津津有味。偶然写几条“笔记”、“索隐”之类的谈红文字,也依然不失其轻松。但是一旦把《红楼梦》拉进学术研究的范围,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或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那就不免要板起面孔,作一本正经状,毫无轻松趣味可言了。我自己读《红楼梦》本是从趣味的观点出发,现在莫名其妙地写起严肃的红学论文来,实在觉得可笑。所以当我决定把三篇有关红学的文字收入《历史与思想》的时候,我已不打算再写这类东西了。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
五十年来,论证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贾宝玉不肯做官,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嵇康、阮籍都不愿意做官了,陶渊明也不愿意做官的,觉得没有什么稀奇。这个不能这么比,嵇康和阮籍的时代跟曹雪芹的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两种不同的做官的行为,它的内涵完全不一样。《红楼梦》里说的不做官,是跟仕途经济对抗的人来说,否定读书人做官考举的道路,这对清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是一个另外的诱导。封建王朝要把读书人都诱导到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然后呢,帮他来巩固统治政权,《红楼梦》里主导的思想叫他不要走这个路,完全是相反的道路,就是《红楼梦》第一个方面的思想。
 王蒙:《红楼启示录》
王蒙:《红楼启示录》
最动人的还是石头的故事,窃以为《石头记》的名称比《红楼梦》好,《红楼梦》这个题名起得多少费了点劲,不像《石头记》那样自然朴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至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云云,就透出俗气来了。
白先勇:《<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
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夭折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这是《红楼梦》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当然,中国小说中穿插戏曲,并不始自《红楼梦》,《金瓶梅》中更有许多戏曲穿插。但《金瓶梅》中的戏曲多为装饰性,与小说主题不一定有重大关连。而《红楼梦》的戏曲,却与小说正文融为一体,不仅使小说情节丰富,更重要的还暗示出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刘心武提出,秦可卿是解读《红楼梦》的关键,因为她的名字谐音“情可轻”。)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蒋勋:《蒋勋说红楼梦》
蒋勋:《蒋勋说红楼梦》
《红楼梦》其实是一本畅销书,三百年来,从手抄本流传,到木刻活字本,到石印本,一直转换成电影、连续剧,《红楼梦》不但没有随着时间“退流行”,还在不同的世代,发生了久远而广泛的影响。书商在做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的畅销排行榜时,无法理解《红楼梦》在长达一百年、两百年间真正永不消退的“畅销”。
陈大康:《<红楼梦>不是飞来峰》
当时小说出版有两种情形:书坊看准能赢利,便收购书稿;反之则要作者自费付梓。于是,《海游记序》中就有“书成时颇多趣语,因限于梓费,删改从朴,惜哉”的感叹,而《歧路灯》则因“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便“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址间”,湮没了近二百年。在这种情形下,曹雪芹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坚决维护了创作的独立性与纯洁性。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红楼梦》上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但他同时又声明“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即并不是为迎合某些读者的口味而写作,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
我并不是纯粹研究《红楼梦》。我的研究是为了让红学与清史“对话”。《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的背景下,它可以让现代的读者体会18世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国有数不清的章回小说,为什么《红楼梦》独放异彩,为什么当时、现在都有这么多人喜欢读呢?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本像这样描写旗人生活方式的小说。书中的旗人又不是纯粹的满人,而是汉姓包衣。他们有着汉人的血统,但是作为满人的奴仆夹在两个文化的传统之间。所以这部小说中的很多语言、风俗就是满汉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