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古典音乐的电影推荐?
可以是《莫扎特传》、《绝代妖姬》这种偏重人物介绍的,《幻想曲2000》这种着重于音乐的也可以,BBC 的纪录片也很喜欢。如果有其他类型的也欢迎推荐。希望推荐时能简单评价一下,如果能附上豆瓣链接就更好啦 =)
谈一谈纯属个人的想法。
比起一般的古典乐电影,《塔尔》在表述的宽度和深度上要更胜一筹。它对于古典乐元素的表意运用,以古典乐为“点”做社会“面“辐射的野心,以及似乎与古典乐作品相差甚远,但实际又在行业颇为契合的强烈当代性,让它在一众古典乐作品里显得颇为突出。
《塔尔》描述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古典乐行业,而是借此而折射出的当代西方世界。它的核心,是当代世界以各种理念而出发的,对于一切人与事的“定义”,是人受到的外来审视与外部判断,以及应运而生的“原有自我的被忽视”。而个体在其中的受容,逐渐的崩溃,成为了影片的重点,并由古典乐行业辐射到了全体西方世界---一个人人展示着种种“正确”,却都只是迎合而非本心,被价值观捆绑住的大环境。
在世人的眼中,古典乐行业是最纯粹于音乐本身的存在,是完全的“艺术”,对应着音乐家们对作品的感性接收的表现。然而,事实上的古典乐界,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名利之心与“正确”思想的影响,这些与音乐和情感本身毫无关联的因素。想要进入其中,便需要让自己服从于其行业规律,从而变得不再纯粹。
由此搭建出的古典乐金字塔,看似高高在上而绝对威严的音乐殿堂,但其内里的运行逻辑却完全是对音乐的否定。这也同样是西方世界的状态,它貌似完美庄严,拥有着太多的“正确”观念,并以这样的观念来判断人与事。这看上去构建起了人人平等,所有群体均受到重视的社会,但却无异于以外在的某种“规则来做出定义,忽略了被定义者的原本自我。
而在这样的古典乐界与社会之中,塔尔的状态与反映成为了影片表现的重点。她需要足够质量与数量的古典乐资源,以便用音乐的演出与创作去表达自我,其中一个缩影便是马勒:她用马勒的音乐去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需要去完成马勒九部交响乐的全部录音,并追求最好的发行介质。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塔尔就必须进入到行业的种种规则之中,让自己淡化自我性,从而在失去纯粹的勉强之中挣扎,以服从规则而强行维持的“符合外部定义”的形象,去争取圈子中的优势话语权地位。而在社会层面上,塔尔也需要这样去做。两方面的人物表现,在电影中交错出现,构成了极强的对照性。片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镜子,让塔尔的身影频繁同时以复数出现,暗示着“塔尔的多重性”之主题。
必须要注意的是,塔尔的真实一面,当然是归属于个体情感的,但也在敏感中带有极度的自私。在情感关系中,她只关注自身的体验,最典型的便是对旧情人的始乱终弃,这也与创作和指挥音乐存在着相似点:艺术,同样只聚焦于艺术家本身的内心表达。而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自私却是不一定吻合普世道德观的,随之构成了塔尔的自我冲突。而有趣的是,当塔尔置身于外部世界,需要用迎合普世观念来营造形象、玩转行业,获得音乐诠释的资源和地位时,其运用的“规则”本身也是不光彩的。自私的真实与对外的迎合,同样有着负面的姿态,显得冲突又和谐,似乎构成了这个时代整体的“负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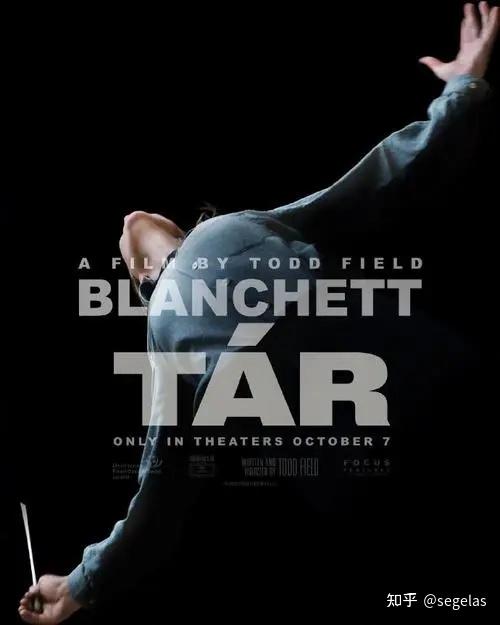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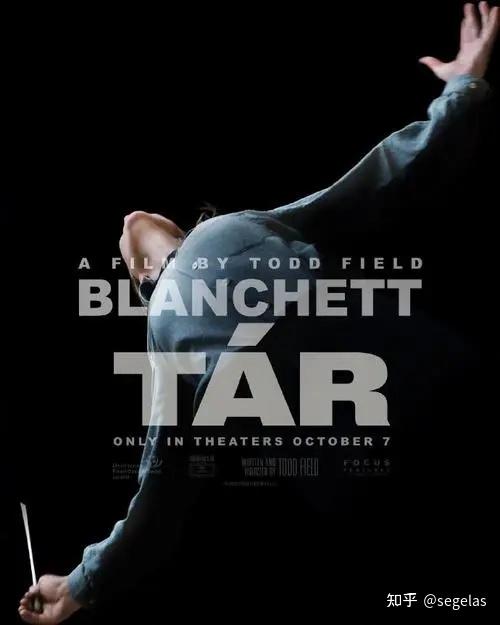
影片的第一阶段,展示了塔尔的多重性,对外吻合审视观念的形象包装与对内表达情感的真实心理,分别对应着“独立而强势”与“极度的自我”的状态,让后者成为了前者掩盖之下的本质。
关于“外部审视与外来判断”,以普世思想进行的定义,以及塔尔对其的反馈,在影片的开头即有强调。第一个镜头,是其他人用手机对塔尔睡觉样貌的私自直播,画面上给出了观众对她的各种看法与评论。这个简短的瞬间,给出了多样的信息---作品关于塔尔在睡觉时完全放松而流露出的”极端自我“,关于她的真实情感,也关于与“自我”形成天然冲突的“他者眼光”,而表述范围则远不限于古典乐行业,而是更广阔的社会。随后的影片中,当手机进入到塔尔的酒店房间,并进行拍摄时,画面上同样出现了观众的评论。
由此,影片的主题已然得到了定性:外部审视之下的普世标准与个体真实情感的关系。塔尔先是用对外形象的包装去吻合外部眼光,甚至要去运用规则以提高自己的行业地位。但包装终究无法维持下去,在外界审视下暴露出不符合“正确”价值观的真实,一个只关注自我情感需要的人,随之因自己的情感纠葛而面临巨大的危机---抛弃此人产生的纠葛,正是导致塔尔的私人感情关系成为丑闻曝光,毁掉音乐事业的诱因。这也对接到了音乐的部分:音乐的指挥与创作是仅关于自我情感表达的,是极度的“自私“,但与之相关的古典乐行业却更加接近普通社会,资源和地位的获取都需要对标准的迎合。
而对于塔尔本人,开头部分同样给出了逐渐叠加的“外部的审视,以及被审视者对外部的迎合”。塔尔第一次出现,便是从“纯粹自我”到“迎合包装”的过程。最开始的她,身穿着邋遢的睡衣,将马勒交响乐的唱片洒落一地,用裸足点出了自己当天的“主旋律”: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的《马勒第五交响曲》。无论是将作品随意摆放的行为,还是选择作品时的光脚状态,都表现出塔尔此时的“纯粹”。而后,这种纯粹则一点点地消失了。塔尔被量体裁衣,穿上了贴身合适的正装,一反此前的慵懒,呈现出了女子古典乐音乐家在外人眼中的“应有模样”:严肃端正的艺术精英,冰冷坚硬的独立女性。而她身穿正装的目的,则是为了参加媒体的现场采访活动,正如主持人让她回应“外人眼中的指挥只是个打拍子的人”一样,是一次最标准的“外部审视的接受与反馈”。
在塔尔逐渐“包装”自己的画面推进时,主持人的介绍始终同步,念出了外界眼中的她,坐拥无数---以指挥家而言,甚至过于没必要的臃肿---荣誉的大师,这显然是塔尔由“背书”所形成的形象。同样的手法,在随后“塔尔应酬说话”与塔尔维基介绍文案特写的同步中,也再一次出现。而在采访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主持人试图进行“正确“的普世价值观赋予,希望将塔尔带到“女性在行业中的被歧视”的方向上。
而塔尔本人,对此则是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需要用迎合外在观念的方式,获得行业中的地位,由此完成她表达自己的音乐目标,以创作作品或诠释马勒的方式,在车上讨论“dg终于愿意为马勒录音发行黑胶碟了”。首先,这体现在了她的采访中,只能迎合着主持人去说出“大师与女大师的不同称谓”的话语。然而,就像她马上追补了一句“但现在已经有了好转”并回到音乐话题一样,她只是在勉强扮演这样的形象,试图让自己显得理性而独立,用强大的形象迎合外部价值观下值得认可的“女权倡导者”认知,生怕漏掉了强调这一点的机会。而她的内里,则是一个情感充沛的感性之人,只关心音乐,真正的自我也只在纯粹的音乐之中展现。在她登上采访舞台之前,镜头始终对准了她的脸,强调着她吃药、打手势、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稳定住一个“强大”的姿态。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她在自家中创作作品时的状态:松松垮垮,突然间抬头,敏感而不安。

对于塔尔蕴含在音乐这一“感性载体“的极度自我,影片有着多样的表达。在片头演职人员表的部分,画面并未出现塔尔的身影,只有背景音乐中塔尔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哼唱。显然,片中频繁出现的由外部标准而“演绎“出的塔尔在此消失,而只融于音乐之中的声音,则无疑是最真实的她,外在的消失带来了其灵魂深处的出现。这也是作品特意设置了“塔尔对少数民族音乐涉猎”这一有些相悖于古典指挥家作风的原因:少数民族音乐有别于古典乐,并未拥有世俗社会介入的庞大体系,并没有那样的外在威严,而是生长于大自然,更加原始,也就更加专注于纯粹的人心呈现。
而在采访段落中,我们也能看到镜头对塔尔的不同处理方式。谈论“女性力量”等非音乐“正确”观念时,她只是与主持人分庭抗礼,处于画面的一侧,而当话题变成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其后的音乐理解,她瞬间来到了画面的中央,拥有了独自的特写待遇。这样的处理,展现了塔尔的真正自我,以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既有着代表自我的“音乐”与“不了解音乐,而是赋予各种价值观定义”----对指挥和音乐的理解来自于外界评论和文章书籍---的主持人的对抗,也有着对其话题的一定程度配合,对“外界评判中的优秀形象”进行的妥协式扮演,并以磕磕巴巴的状态而表现出不自如甚至痛苦。
同样的表现,也出现在了塔尔与他人的交往中。在与指挥家卡普兰的饭局中,二人的表现泾渭分明。塔尔不解释自己的诠释手法,鼓励卡普兰去“摆脱别人的技术指导,找到自己”,对爱情进行反应时,也会潇洒地表示“会为你和那个偷窥你的男人让出座位”。而卡普兰则一味想从塔尔处获得作品演绎的技术性手法,而忽视了自己对作品感受的把握与再现,对待塔尔关于爱情的调侃也局促不安。从他询问塔尔“怎么看我的演绎,乐团的评价虚高了”,就可以看出他更偏向于“外部审视”的性质,而和他在此处表现完全不同的塔尔,则显然与这种性质构成了反向的关系。
而在塔尔教课的部分,冲突再次出现,并进一步地引导出了塔尔在两重性状态里的痛苦。她试图让男学生抛开对音乐家进行基于“非音乐的社会性价值观”的定义,将巴赫从“女性歧视者”还原成单纯的音乐家,欣赏他的作品。在演奏中,塔尔举出巴赫演奏名家格伦古尔德,便是对此的侧写:古尔德的个性,让他的演奏完全不考虑任何的所谓标准化理解,将一切作曲家的钢琴曲都弹成了巴赫,而录音中几乎自成一路和声的哼唱习惯,以及隔绝音乐行业的“自闭”,也让他显得远离世俗,只专注于“自我的音乐”,完全随心演绎。然而,男学生对音乐的一切却都是不纯粹的。他报考茱莉亚学院,是因为小提琴家萨拉张出自这里,是来自于外界标准的权威性背书。而他不听巴赫这样的“古典乐奠基者”,则是因为他不符合当代观念的对女性态度。二者共同指向的,是他对音乐的不专注甚至不关心。这在他聆听塔尔教导与演奏时一刻不停的抖腿中体现无疑,并因为价值观不合而干脆放弃了音乐课。而对其推崇的“普世价值观”,他自己其实也并非真的相信,只是对这种外部标准的刻意迎合---在塔尔否定了他的言论后,他愤怒地骂出了“婊子”,将之前口称的“尊重女性”抛到一边。

塔尔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当她试图用音乐表现出纯粹而极度的自我时,从外界接受到的反馈却是基于非音乐角度的,这让她被迫包装出一个“非音乐”的自己。在这样的古典乐与社会环境中,音乐和真情往往是缺席的。在授课的段落中,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隐喻:第一个画面,镜头缓缓地扫过了单调地拉着固定音阶的乐手们,声音不成调子,而后干脆被塔尔终止,最终定格在“不关心音乐”的男学生身上---在这样一个本应属于音乐的排练厅与课堂之中,“音乐”却不在场,因为从事音乐的人并不重视它。而塔尔对此的痛苦,同样在此处可以窥见。不仅仅是她热忱解说却被辱骂的待遇,还有着镜头上的暗示:无论她如何移动,从未占据画面的中央。同样地,当她试图迎合外界去表演出一个符合他人预期的强大形象时,例如登台接受采访之前,也同样会位于如此的构图之中。就像她也会在此谈到“乐手的评价打分”,她必须压抑一部分自我,迎合外界价值观标准,但这与她展现自我后的负面反馈一样,都会对她造成痛苦。
塔尔拥有一个“不关心他人”的真实状态,这只对接到她的个人体验,并导致对普世道德观的巨大逆反。这样的设置,与她外在被赋予并被迫迎合的“强大独立”形象,构成了最明显的极端反差,由此强化了她的痛苦程度。塔尔对马勒的着迷,就像维斯康蒂的名作《魂断威尼斯》里的手法一样,制造了主角与马勒的对等关系,由马勒的极度感性人格来表现主角的特质。特别是,当塔尔与经纪人在车里时,二人谈论了塔尔与情人和马勒与妻子阿尔玛的关系之类似,让塔尔与马勒的对照显得更加细化,也必然地将塔尔变成了马勒那样的敏感脆弱之人。而在电影里,每当塔尔身处于独居的私密环境时,她的感性便会体现无疑---在酒店房间里,她会突然意识到女儿曾经的潜入,而回到自家,几个“放下行李,收拾屋子”的镜头表示了她的状态变化,离开外部环境而进入自我空间之后,便是她与情人的拥抱,诉说着对女儿的种种难言之痛,伴随她内心开放的则依然是少数民族音乐的录音。
值得注意的是,导演设置了两个“对塔尔的注视”,对应塔尔接受的“倾向于外部价值观的审视”与“侧重于纯粹自身的审视”。前者来自于塔尔的经纪人,负责对她的形象包装与外部对接,与她维持着工作上的交流。在塔尔接受采访时,经纪人默念着主持人的介绍词,对塔尔的公众形象定义显然由她所做。而当塔尔遇到音乐上的共鸣者,与其愉快交流,身处于画面中央之时,镜头数次给到窥探此处的经纪人,随后由她来进行打断,让塔尔去赴约与卡普兰的交际聚餐。而后者,则来自于片头两次出现的红发女人。其从未以正脸出现,是被塔尔抛弃的旧爱,将用自杀来毁掉塔尔的“社会形象“外衣,揭露她繁杂的感性本质。她暗示了塔尔私人关系混乱的问题,是她内心中极度自私于爱情的部分。在塔尔接受采访,返回酒店时,始终会有女人的背后镜头,从其视角出发而拍摄塔尔,似乎在戳穿塔尔在公众环境下的强大形象,暗示她内心中存在的感性自私。

随着影片进入第二阶段,塔尔的状态也愈发明晰,与环境发生更密切的互动,并将环境范围扩大到了非音乐行业的社会之中。同时,随着第二阶段的深入,对外形象与对内真实的并立开始崩坏,后者的存在让前者无法持续下去,而后者本身则给身处行业与社会之外部环境的塔尔带来了崩塌。
如上所述,塔尔的音乐创作始终是她表现“聚焦自我情感“之真实内心的重要载体,第二阶段里从“切水果”到“灵光乍现”的过程,以前者有别于对外规整严肃形象的生活随性感,表现出了塔尔创作音乐的“真“。从邋遢睡眠中醒来的她,听着音乐念叨伯恩斯坦,布鲁诺瓦尔特,迈克尔托马斯等一众马勒名指挥的名字,与他们打招呼甚至抱怨其演绎手法,给出了其基于马勒音乐构成的与他们的心灵神交,以及“反对外威严”的真实形态。而当她与老音乐教育家吃饭时,二人谈论着对音乐的真正看法,用词也毫无“严肃”地嬉笑怒骂,这与第一阶段里塔尔和卡普兰的饭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拥有着更随意,更音乐,也更真实的表达。
因此,这也带有了她对等于马勒的脆弱。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导演都给出了相似的表达方式:创作中的塔尔突然意识到房间内存在的某种不安,随即恢复创作,似乎将这种内心敏感的外化感知变成了音乐的养料。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相应场景,回到钢琴前的塔尔弹起了《马五》的第一个小节,随即画面连接到了塔尔指挥《马五》开头的排练场景,让马勒在丧失女儿之痛创作的该作品,特别是描写葬礼的第一乐章开头,成为了塔尔自身的情感体验。
同时,以塔尔带着女儿上学的段落为起始,我们看到了“由行业到生活”的表述对象过渡。“爱情”,成为了兼容与连接二者的载体。塔尔带女儿上学,前去解决女儿的被霸凌问题,这是她的生活内容。而在二人在后景中离去时,镜头的前景给到了塔尔的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情人,她正在创作音乐。职业,行为,与塔尔的关系,借由前后景并列而强调的“塔尔生活关系者”,给予了情人以“塔尔生活和音乐行业中的真实情感载体”的双重属性。随即,塔尔与女儿共处于私密的车内环境,二人肆无忌惮地唱歌与大叫,将从音乐过渡而来的生活之真实,也与塔尔的对外形象区分开来。而后,与塔尔出现情感纠缠的年轻乐手正式出场后,这样的表达再次被运用起来。二人首次邂逅时,塔尔身处于私密的卫生间环境,不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洁癖,并随性地弯腰窥探隔间里年轻乐手的靴子。这是区别于外部笔挺形象的自然形象,也引导出塔尔的爱情。
塔尔的“随性”真实,其自私中带有的敏感、脆弱、反道德观,与对外呈现的“威严标杆”之表演,其吻合的“正确”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并同时作用于音乐行业和生活环境中。对这种并立体现最明显的一幕,是塔尔拍摄唱片海报的部分。她先是处在“包装与宣传她“的经纪人于前景越肩视角呈现的视线中,手里拿着乐谱,与前景中经纪人手里唱片封面上正在做读谱笔记的阿巴多如出一辙,这暗示着她此刻吻合经纪人思维的“表演摆拍”。随后,镜头突然从经纪人的越肩视角中移开,切到了塔尔的视角,她看到了年轻乐手的身影,随后“拿着乐谱的阿巴多”消失,镜头里只留下了“拿着乐谱的塔尔”,说明了她此刻从“经纪人视角下的表演”到“对接真正音乐的流露”的切换。
在电影中,塔尔的表达真实,往往发生在各种各样的私密空间里,而在外部的状态则是“表演向”的。为了达到音乐创作与指挥,借此表达自我的目的,她必须要迎合外界,压抑自我,这样的悖论正构成了她的痛苦,也必然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在音乐的部分,第二阶段的表达非常明显。塔尔以此前一幕“感受真实不安”后引导出的《马五》第一乐章指挥为开始,但随后却频频终止排练,每次暂停的头几句话必定会是德语的指导,而后迅速切换到英语。这是非常有趣的变化,德语是以德奥为核心的古典乐中最“原始与根本”的语言,在表达自己对音乐的诠释时,塔尔下意识地以德语开始,意味着她此时对音乐的“接近”。同样的德语使用,也出现在了塔尔说服乐团经理更换不执行自己要求的人员的时候,希望让音乐的演绎能完美实现自己的意图。然而,她马上切换到英语,这是世界性的语言,更加符合各国乐手---在多个排练场景中被逐一特写强调----共同组成“人种集合”的当代乐团状态,也是对于各国乐手平等视之的“正确价值观”,这也对应着现实中行业中盛行的“指挥家与乐手对音乐诠释的民主”倾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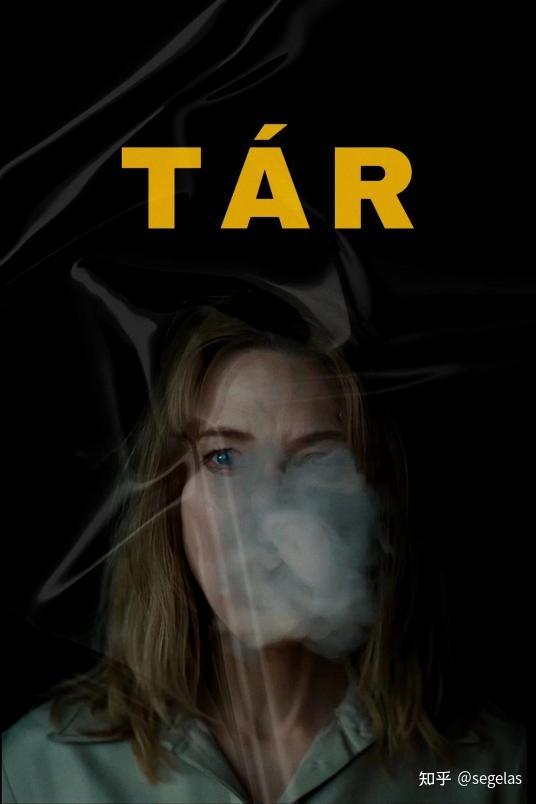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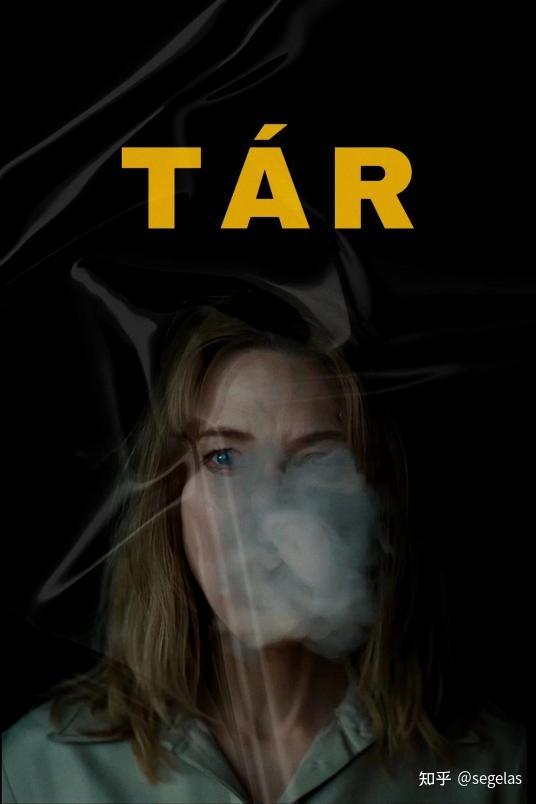
由此可见,在排练中,塔尔先流露了真实的自我,随后迅速压抑自己,拿出更符合外界标准的状态。此外,这里的她始终带着强势的动作。这说明着一个事实:塔尔希望用表演出的强悍与威严,宛若克伦佩勒和卡拉扬一样的形象,让自己成为更强势的女性形象,来控制住“会给指挥家偷偷打分”的乐手们,让自己表达“真情”的音乐理解与演绎意图得到落实。这显然是关于“性别”的又一层“标准吻合”。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整个排练段落里,音乐的进行都是断续的,这就像此前“无音乐响起的音乐课”一样,暗示着塔尔此举妥协现实的失败结果,她根本无法以此来真正实现内心表述。并且,当《马五》第一小节的小号出现问题时,塔尔必须请dg公司的录音师帮助---随后更是登上录音室商谈---让乐手站到拍摄区域,方能完美地给出效果。在那一时刻,镜头处在乐手的身后,演奏音符的乐手于黑暗处,与后景里模糊的乐团和塔尔远离,而后者则出现在旁边的黑白监视器里,这无疑淡化了音乐的“真”,将之与塔尔拉开了距离。显然,塔尔在音乐上的情感表达,需要用唱片公司的录音队伍这一“行业内力量”,才能较好地完成。或许,就像切利比达克对录音的鄙视那样,经由这等离开舞台现场的制作与后期而形成的音乐演绎,并不具备“真”。并且,即使塔尔拿出了“平等”与“强女性”这两个吻合当代价值观的对外形象,她最终也需要首席小提琴手的情人站起来帮助。塔尔在音乐层面的“妥协表演”,必定招致失败。
这种失败,也延伸到了第二阶段的生活层面。最明显的,无疑是塔尔去学校为女儿出头的段落。在有意识行为的层面,此时的塔尔却带有了强势感,暗合着她“独立女性”的表演形象。然而,在塔尔传递强力威压的同时,镜头却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始终摇晃、无法安定的手持摄影。这否定了塔尔外表的威严,并在一个她走进女孩的主观视角中,以摇晃传达了她做此表演时的内心不安。而在塔尔与女孩说话时,如上述音乐段落里的语言手法一样,塔尔同样说了德语,暗示着她此刻的真情流露。同时,被警告的女孩处在仰拍状态,看似强势的塔尔反而被俯拍,也是对她真正力量缺失的表现。
并且,导演也给出了一个与电影开头部分有所呼应的手法。塔尔跑步,暗合着她穿不上表现威严的得体演出服,表示自己要减肥的开头,这构成了她对外在形象的“打造”。但跑步时首先出现的刺耳车声,随后的嘈杂犬吠,以不优美的噪音暗示着塔尔此举与“音乐”的联系切断,并以塔尔对“声音不和谐”感到的不安为结束,“减肥塑形,穿上正装“的“打造威严形象之表演”被打破,露出了她不安的真正情绪,并对接到了其在这种混合状态下对音乐的掌控下降。

在音乐层面,塔尔有所让步,与dg的拍照者讨论唱片封面,与杜达梅尔----拉美族裔+自由斗争+招募穷人孩子对抗贫困的属性拥有者,片中一个若有若无的“正确性标准下的乐界代表”暗示----的照片一样,虽然口称来点不一样的,最后也只是与阿巴多摆出一样的姿势,也让自己暂时成为了杜达梅尔等人一样的“摆拍者”,也暗示着自己需要向类似于杜达梅尔的“非音乐之价值观正确”进行的让步与迎合。而在生活层面,塔尔也如上所述地给出了让步,让自己靠拢向独立女性的“正确价值观”,甚至有些表演过火。
随着影片的进行,塔尔逐渐失去了一贯拿捏的平衡,“威严独立”的外界生活与“自私感性”的自我创作,开始互相掣肘,将一切导向悲剧性的结尾。作为暗示最先出现的,是塔尔又一次带有极强象征意义的跑步段落。她身处外部,为了“穿上合身的正装”而健身,到报刊亭购买自己封面的杂志的行为,则是与健身等同的“注意外部形象”。然而,在这里,塔尔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杂志,而是由老板拿出了预留的一本。这是一个微妙的瞬间,它给出了塔尔此时在外部环境里的“被动状态”,打破了她在外面的一贯强势,反而带有了私密空间里的脆弱感。此前的作品中,导演只会以镜头语言的方式去暗示这个状态,到了这里则首次来到了更明确的行为层面。
并且,随着塔尔在外部空间失去强势,私密空间里的她也开始无法表达真实的感情了。她处在自己的房间里,将杂志放进柜子关门,拿起乐谱手稿,这说明了私密空间里从“对外形象”到“自我表达”的切换,而后者正是符合这一空间的存在。但是,塔尔的创作却被来自“外部形象包装”的要素打断了。代表“外部视角”并打造塔尔社会形象的经纪人闯入,给塔尔看了旧情人带来的绯闻报道。经纪人开始哭泣,展现出脆弱,这不符合她带有的“对外包装强势女性“的属性,与不符合标准观念的“丑闻”报道一同,预示着塔尔对外形象的破灭,业界地位的动摇,而促使塔尔外部崩塌的恰好就是她私密的“爱情”因素。原本分处于“音乐”和“非音乐”两端的私密与公众空间的运转平衡,开始混淆起来。音乐对标的感性之真性情问题侵扰了公众空间里的包装形象,并反过来打断了私密空间里的音乐---塔尔的创作,因为经纪人哭泣与展示丑闻意味着的“对外形象崩塌”,无法进行下去了。
可以想见,在影片开始之前的时间里,塔尔一直很好地实现了平衡,让“音乐”成为了她的感性抒发平台。封闭且进行创作的自宅自不用说,而指挥音乐的舞台也同样是塔尔的“私密空间”。她用符合正确观念标准的形象包装,获得了行业内的资源,让自己足以实现音乐创作意图,而在音乐上则以真实的自我充分发挥。然而,在影片的中后段,这样的平衡不可避免地结束。塔尔的社会形象崩塌,让她留下了失去行业资源与地位的风险。

而这也延伸到了随后的具象化表达段落---塔尔对乐团的失控,让她无法在排练中带领乐团发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声音。作为前导,塔尔在私密空间的自宅与车里,先是找到了不断运行的节拍器,而后听到了空调发出的刺耳响声,这两处都带来了私密空间里塔尔对“音乐”的失控。车里的噪音是完全非音乐的,而前者则更具象征性:排练和创作用到的节拍器,离开了塔尔的掌控,自顾自地运行不停,而塔尔此时一度站在钢琴前,却没有弹奏它,与此前在家中“同样感到不安,随后回到钢琴前弹出旋律”有着鲜明的对比。“对音乐的掌控力失去”,也引导出了排练的段落,从而得以落地。空调的噪音接到了《马五》第四乐章里用到的竖琴的特写,而塔尔迅速打断了演奏,重启后再打断。
在这里,音乐的抒发是不顺利的,这意味着塔尔在音乐上的缺力。而其原因,便是她的真实“感性”---舞台上的年轻大提琴手对她微笑,让这里充斥了塔尔“曾被媒体斥责”的性取向要素,同样的还有塔尔在指挥不顺时下意识看向女情人首席的目光。在塔尔与情人的对话中,导演给出了一个微妙的信息:在过去,同性恋成为了塔尔职业生涯的拖后腿存在,而现在则是“反正我们领养了女儿,他们也说不出什么了”。由此可见,在对外形象中好容易过关的同性恋问题得以消弭,一方面是社会价值观的风向转移,一方面也是由塔尔养女儿的“迎合外界审视,给予自己正确性”,这也让塔尔在生活中带有了一种“包装”的意味,说明了她此前对外在非音乐层面的“以迎合实现情感”,等同于她在音乐层面的“包装形象以获得音乐资源”,是对塔尔第一阶段状态的再提示。
然而,这一次的问题,从同性恋来到了更加难以被外界接受的“情感丑闻”,带有了更强的反伦理。它是塔尔“真实自我“的呈现形式升级,顺应着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崩坏之变化,让塔尔无法再延续此前掩盖真实与迎合外界的“包装“。它对塔尔在乐界的影响,在经纪人因绯闻曝光的哭泣中便可窥见,意味着塔尔的真实感性对其对外形象与乐团掌控中的不利影响。
而在本段中,这一点也有着音乐层面上的具体呈现。音乐舞台理应是塔尔表达自我的私密空间,但其涉及到的乐手与其背后的整个行业,却属于非音乐且不私密的公共社会范畴。因此,塔尔的矛盾产生了:她需要用公众形象来维持自己在乐团面前的地位,拥有音乐诠释的资源,但这就要求她抛开自我,迎合包装,但这样的虚假也就意味着音乐表达的不顺利,对外形象也会因为无法延续而证伪中,失去在音乐行业里表达自己的资本,二者无法平衡,而是相互进行负面的影响。
可以看到,对比第一次排练,第二次的塔尔出现了变化,她的解说更加弱势,有了“拜托你们”的双手合十,不再试图在乐团面前表现强势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变化,对应着此前绯闻纠葛的曝光,让塔尔在影片中后段的包装褪去,在外界面前暴露出了真实的脆弱感性。塔尔在音乐上的矛盾,在此完全出现,这也意味着她在音乐上的进一步失败。在非音乐的行业中,她必须包装自己,不能拿出本应属于音乐的真实自我,这本身便是对音乐表达的削弱。同时,更加弱势的表现,以及舞台上出现其暗恋的大提琴手与女情人首席,又象征了塔尔在音乐中“感性真实”的必然存在,破坏着其维持乐团掌控力的对外形象。两方叠加且自相冲突的结果,便是排练的连续中断。

而后,塔尔则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在乐团中必须拿出的“非音乐形象”,以及其失败。她与解雇的老乐手交谈,先是讨论了后者买下的柏林墙倒塌纪念雕像,这意味着意识形态这一非音乐的社会性概念,而两德统一象征的西方视角下的“大同,解放,自由”,则当然是价值观里的“正确”存在。柏林墙倒塌的庆祝演出中,本片中频繁被提及的“伦尼”伯恩斯坦指挥两德乐团中各一半人的组合进行了《贝九》的现场。这部作品的主题正是“大同与自由”,而乐团的组成也体现了“平等”的概念,正是音乐与普世价值观的结合。
然而,塔尔却成不了伯恩斯坦。在这里,她试图用公关辞令劝退对方,制造平和的分手状态,去吻合当代乐团中“指挥与乐手人人平等”的观念,而非给出此前陈述的“不服从音乐指挥”这一音乐原因而行强力驱逐,仿佛老派指挥那样的“为了音乐诠释,一切以我为主”。其形象无疑吻合了两德统一的正确社会价值观,以此掌控与“柏林墙《贝九》”乐团同样地由多国人组成的团队。然而,她并不能很好地延续自己“正确”的社会形象。二人先是吻合两德统一概念的对坐,在构图中姿态完全对等,随后却由于塔尔的愤怒而出现了变化,对等被破坏,塔尔与对方开始各处于“背面与正面,前景与后景”的分裂状态,塔尔的言谈也失去了社交的客套,充满了揭伤疤的攻击性,其情绪宣泄本身带出了真实内里的“不顾及他人的自私感性”。而她在混乱中发出对对方“婚姻观”这种不吻合正确观念的质疑,与对方破坏“统一”而同样“不正确”的“攻击同性恋”一致,意味着塔尔公众形象之于“正确”的偏离,利用社会观念进行乐团掌控的不力,以及“感性真实”对此的削弱影响。前述中的“矛盾”,再次得到了证实。
力推对其带有私人情感的年轻大提琴手,辞退老乐手,带来了塔尔在音乐演绎上的最直接冲击。同时,这其中也带有了塔尔的极端自我性:她只考虑了自己的音乐演绎和隐秘情愫,却在换人与独奏的选择中无视了年轻大提琴手的立场,将她完全抛向了乐团的对立面,毫不顾忌她的境遇。而在乐手们眼中,塔尔此举无异于假公济私,而塔尔对其的看好不仅仅是出于感情,还有重要的音乐表现力,能更出色地实现自己的音乐诠释。这个选择,是音乐与情感的双重结果。然而,它的结果放在外界标准下,却是不尊辈分与私情泛滥的离经叛道。与情感丑闻一样,这种对接着塔尔真实一面的行为,都会让她失去行业里的地位,导致乐团的离心。
导演用了三场戏进行站位的衔接,来表现乐手更替给塔尔带来的影响:辞退老乐手时,塔尔站在右侧,随后她与情人商量接班人选,说出“慢慢想办法”的台词,一切都还在掌控中,右侧的站位也延续了上一幕中“主导解雇”的状态,但在下一场与经纪人讨论新乐手的场景,她却突然来到了左侧,预示着这一幕中的关键变化。在这里,象征塔尔“社会形象”的经纪人首次流露出了感性的一面,并带来了对塔尔的巨大影响与隐患:她没有删除丑闻对象的邮件,而这个必然会遭到外人攻击的问题,本应是迅速解决的。
代表“对外“的经纪人的此举,以及她在首次迎来特写镜头中的首次迟疑,让她与塔尔的关系、自身的状态,从“工作”变得更加情绪化,也更倾向于音乐上的争端。这无异于塔尔原本强势坚固的“对外形象”在感性压制下的坍塌信号,并伴随以音乐层面的不和谐。如塔尔自己看到邮件后面部被遮挡的动摇状态一样,塔尔形象包装开始破产,真实的情感经历与私密内心开始表面化。导演穿插了一个“塔尔跑步“的短促画面,用其瞬间的终止表明塔尔“对外形象”的破产。而在二人一开始讨论的乐手更替话题,结合站位的变化,则延续此前两段,给出了塔尔真实一面暴露于生活后,对于乐团掌控力的弱化影响,而她也很难再指挥乐团,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心绪。

暴露真实后,塔尔对乐团的音乐指挥力,在行业中的资源获得,发生了双重的下降,让她无法再完美地诠释音乐。这一点在此阶段有着丰富的表现。首先,经纪人发生动摇的上述一段中,塔尔和经纪人随口提及了“dg只给我们发行数字音源,但中国市场很重要,因此给中国作品发了实体唱片”,这表现出了此刻“对外开始情感化”所带来的资源影响,让塔尔在商业规则面前败阵,拿不到最佳的音乐介质。随后,她与大提琴手吃饭,已然犯了乐手待遇不平等的忌讳,会导致她在即将到来的乐团投票中受到影响,但她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却依然赴约,说明她此时已然完全展现出真实的情感一面。在纯粹的音乐层面,塔尔与大提琴手惺惺相惜,后者的醉心音乐,不理观念、国别、礼仪等繁文缛节,完全的真实和自我,正是塔尔的理想化镜像---在贝多芬生活过的餐厅,二人畅聊音乐,大提琴手不优先塔尔以示礼貌地抢着点单,也亳不顾忌身材地大吃肉食,在德国人塔尔面前随意地大赞反对希特勒而逃亡苏联的“叛德国者”,比起本国人罗斯托罗波维奇更喜欢杜普蕾,听音介质不是保真的唱片而是简陋的视频。而她演绎的《埃尔加大协》录像,也成为了电影中被唯一一次持续放送,且聚焦于她拉琴时身形的音乐,对应着她作为塔尔完全理想化状态的“音乐诠释成功”。
事实上,这也正是塔尔被她吸引的原因,关于情爱冲动,也关于音乐诠释。然而,非理想化的塔尔,却无法像大提琴手一样,她的音乐是要被非音乐的社会因素阻碍的。她欣赏了上述的《埃尔加大协》录像,却被邻居抱怨报纸被偷的敲门声打断,音乐被生活化的杂事阻碍,而塔尔则以更接近真实的第一语言德语,进行了下意识的反映。而在之前的一段,在与大提琴手吃饭时,虽然塔尔非常欣赏地微笑注视对方,但她自己终究只能吃着减肥的沙拉,无法完全抛开“穿进西服”的“形象需要“,这让她与理想形态的对方拉开了差距。而象征“对外”经纪人的首次感情波动,来自于塔尔的“你也可以推荐自己接班”,让她看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追逐希望,这预示着塔尔在外部社会环境中的“音乐化”,以及与音乐相关的真实情感化。
然而,这却带来了“音乐”的崩塌。作为先导,塔尔再次游荡在深夜的家中,看到了嗡嗡作响的冰箱,这是对此前两次“探知噪音”的延续,意味着塔尔对“声音”的进一步失控。随后,在又一次排练中,获得大提琴手助力的塔尔,难得地完成了一段完美的演绎,这种“舞台上纯粹音乐”的实现,却旋即被打破:塔尔希望推出大提琴手来表演《埃尔加大协》,却因为让大提琴首席乐手参加竞演,而犯了不论资排辈的行业忌讳,这将带来对乐团领导力的后续问题。而在塔尔与乐手---值得注意的是,依然用英语---沟通时,画面中她的身后始终存在着经纪人的身影。这场戏开始时,经纪人因为排练的效果而泪流满面,暗示了塔尔“对外”的情感化倾向持续进行---这也正是塔尔此刻面对着需要用非音乐观念去合作的乐团,正在进行的事情,并在随后与丑闻一并地带来崩塌。

在影片的发展中,崩塌逐渐表象化,直接呈现在了塔尔对乐团的掌控之上。她刚刚完成了一个在音乐层面极致完美的排练,这是在作品中非常罕有的段落。然而,这样的完美马上被打破了。在台下,塔尔先是处理了一系列的乐团杂务,特别是对此前出现过的老指挥,考虑到他“与卡拉扬和阿巴多相比毫无存在感”的乐团历史地位,专门给他调整了专职司机待遇以确保他的心情。这样的“刻意讨好”,包括一系列的乐手人事工作,都是乐团中的非音乐层面要素,是塔尔作为指挥必须应对的东西。她不能仅仅做好音乐,抒发个体情绪,而是要以社交和情商等“交际手段”,笼络住乐团的人心。此前与之谈论音乐甚欢的老指挥,到了此时也暴露出了“社交对象”的真相,正是对塔尔聚焦“个体”的最佳驳斥。
并且,塔尔暂时的乐团处理得当,也被迅速地打破了:听到旧情人自杀的消息,塔尔不再对答如流,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显然是塔尔极端自我的感性形象对于乐团这一"外部”的入侵,并严重破坏了塔尔对后者的掌控。对外形象让位于感性本体的塔尔,无法掌控乐团,也就无法让乐团演奏出完美的音乐,从而输出自我的情感----二人始终坐在观众席的阴影中,背对镜头,而远景里的舞台则明亮而空荡,说明了感性破坏外部之后,塔尔对“音乐演奏之地”的远离。
此后,塔尔与老指挥的再次聚餐,成为了上述“驳斥”的完整表现,完全推翻了第一次聚餐时的音乐氛围---他们的话题从音乐逐渐变成了富特文格勒受到的纳粹身份调查,最终落于老指挥对塔尔性取向的反感:塔尔说“你不会将性与纳粹调查相提并论吧”,而对方则回复以“一直以为衣架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同时强调了自己对政治立场与性取向的不宽容态度。而在另一方面,象征着“对外形象“的经纪人,也进一步出现情感化的动摇。在塔尔告知其乐手选拔结果的段落中,导演始终将镜头对准经纪人,强调了她此时的情感化状态,这一方面带来了塔尔”不顾及他人感受,只关注自己的音乐演绎与情感满足“的感性自私,同时也表现了塔尔的感性自我对其生活的占领,对外包装形象的弱化。这两个段落连接在一起,便构成了对塔尔现状的综合呈现----“音乐”无法抛开价值观等外部因素而保持纯粹,但"对外包装”却被感性真实破坏,必然带来对“音乐”的削弱。
在“身穿外套的办公室”这一外部空间中,我们看到了塔尔在苦恼旧情人死亡与乐团问题时的沉默。而她对音乐的掌控力,也随之表现以虚弱的状态。持续反复出现的“起床寻找噪音来源”片段,再次恶化升级,干脆到了塔尔打开冰箱门却发现声音来自别处的“不可知”地步。而塔尔在自家的音乐创作,也变成了在钢琴阴影中的枯坐,甚至无法像之前一样弹出几个音符。她依然可以在音乐中获得暂时的感性体验,就像聆听年轻乐手演奏《埃尔加大协》时的沉醉,此时对方的身形甚至掩盖在幕布之后,象征着塔尔对音乐体验的极度纯粹。并且,她也可以在对方造访自家时,与之愉快地交流自作曲目,驱赶掉此前枯坐钢琴前的灵感缺失。
然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塔尔会马上回到现实中,面对着因自私而导致的情感丑闻的必然爆发,其所象征的“对外形象被感性内里的破坏”,以及变得一团糟的乐团地位与音乐事业。在交流创作时,塔尔走向年轻乐手,下一幕中,对方则走入现实感极强的破落街道,与塔尔远离。而更有趣的表达则是塔尔与女儿的互动,当二人充满亲情地交流时,女儿表示自己会给每个玩偶发短棒,塔尔则回复”不可能每个人都指挥,这不是什么民主“。在这里,感性要素的存在感被拉升,而塔尔则否定了自己曾经在排练沟通与乐手对话中试图营造的”平等与民主“,否定了自己对于当代古典乐团通行规则的贴合形象。这也正是塔尔在处理年轻乐手待遇时的表现内容,并将带来乐团的崩溃。

在最后的阶段,一切都变成了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塔尔的精神以梦境的形态出现,她在黑暗中看到了水波荡漾的爱人们,但这样的”爱情“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倒影,这也与"音乐”相结合,让塔尔在梦境中的原始森林开始着火,暗示着塔尔追求的“原始森林里的民族音乐”,这一最具纯粹性的音乐形式的毁坏开始。同时,这些信息也同样折射到了现实世界中,让塔尔的自我聚焦与私密情爱,被直接地放置在”外部审视“之下,随之滑向音乐与爱情的深渊。它以经纪人被塔尔无顾忌的伤害后的背叛而开始,以塔尔授音乐课和与学生进行音乐与价值观的争辩共为进展,以和年轻乐手共处时接受”价值观举牌人群”示威的在线视频与文字评论画面作为象征-----就像塔尔面对乐团委员会时受到的质疑那样,她与音乐家情人们的过往,被外界以名利规则的视角进行解读和批评,从而导致了音乐和爱情的丧失。特别是自杀情人对塔尔维基百科的修改,完美地说明了塔尔感性一面给对外形象施加的影响:受到塔尔抛弃的情人,改变了外界了解与定论“塔尔其人”的文字内容。
到了此时,塔尔的生活已经全面失去了感性表达的条件。她依然可以在手握指挥棒的时候诠释出自己的情绪,传达自己极度紧绷的感受,但音乐的演出段落却迅速被切掉,代之以她与首席情人充满了攻击性的接触。随后她再次出现在这里,已经是远远坐在观众席的被解职。她依然试图创作音乐,但旋即被邻居的敲门声打断,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一般地走进隔壁,看到了重病---随后在面临乐团解职时再次目睹其死去---的少女,从纯净的音乐世界走入了残酷的现实世界,再也无法回去。而在爱情层面,她追随着年轻乐手的脚步,却进入了一堆断壁残垣之中,并狠狠地摔了一跤,外显的鼻部伤痕成为了她形象崩塌外露化开端的符号。
更重要的是,塔尔的小提琴首席情人因为外界的抨击而不堪重负,并因为塔尔与年轻乐手的亲昵举动,与塔尔决裂。甚至连塔尔和女儿的亲情,当后者被情人从她手中”劫走“时,导演也以车内镜头带来的”第三方视角“,强化了这一幕发生背后的”外部审视“因素。塔尔观看着网上抨击自己与年轻乐手共处视频时,接到首席的电话,电脑屏幕与手机屏幕上的两个情人共同出现,让塔尔的全部爱情支线都被置于外界评论的压力之中。而作为乐手领袖的首席的离开,也必然意味着乐团掌控的丧失----她因舆论压力而离开塔尔,乐团也因为舆论压力而解除了塔尔的职位。
当塔尔再次戴着帽子坐车回家时,一切都与电影开头的类似场景完全逆反了:邻座不再是“对外”的经纪人,而是“情感“的年轻乐手,而这样的切换带来的,是随后在家中与首席情人的激烈争吵,而不再是电影开头的和谐相处。她的生活,即使仍有”穿进礼服“的跑步减肥与”塑造强势“的拳击运动,但这二者的目标,”诠释内心的音乐实现“,已经在马勒演出海报上的随意涂鸦之中宣告破产。对于乐团与行业,她从”迎合自如“变成了”排斥后退“,先是在第一人称视角中看到评委会成员们后急忙倒车,到了管理者们开会时则一言不发,表情僵硬,再无曾经的对答如流,而苦心维系着的指挥家人脉,也在和卡普兰的决裂中宣告断裂。不可避免地,她也失去了对音乐的诠释平台,先是音乐被邻居称为噪音,随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勉强登上了《马五》的舞台,但却在极度的敏感中怒殴乐手,仿佛宿命一般地因感性而毁掉了最后一次的自我表达机会。
塔尔能做的,只有观看伯恩斯坦指挥马勒作品的录像,倾听着后者对“音乐只作用于情感”的纯粹性描述,却终究无法让自己变成后者,成为他那样的人---指挥柏林墙倒塌的政治型演出,将他所谓的'热马勒“演绎带到“绝对高度的个人情感化风格”,也以公开的同性恋身份而获得世界的认可。外部价值观,音乐,情感表达,性取向,伯恩斯坦实现了一切的兼容,这也是导演反复将他与塔尔进行对应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伯恩斯坦与塔尔类似的”指挥与创作并行“,以及其对非古典乐创作的倾向,用《西区故事》为代表的蓝调对应塔尔的”少数民族音乐“。而塔尔,正是”失败了“的伯恩斯坦。

值得玩味的是,在影片结尾,导演给出了一条出路:对于西方世界与”高端氛围”的远离。当塔尔去到了遥远的亚洲国家,进入了质朴的环境,她反而找回了音乐与情感的能力。无论是她拉开窗帘后外面低矮楼房的平常风景,还是穿行而过的平常街道,还是指挥的平常乐团,都与此前威严光辉的西方古典乐世界截然不同。甚至连演出的作品,都不再是马勒这样的”高端”存在,而是游戏原声。然而,在这里,她却重新拿起了指挥棒,并且在与女按摩师的对视中唤醒了内心中因情感关系混乱而毁掉一切的恐惧,甚至被震荡到了呕吐的地步。无论正反,塔尔都迎来了更真实的感性状态,拥抱音乐,也不掩饰负面情绪。
显然,导演否定了西方古典乐界,以及其所象征的“无数正确观念环绕下而表面庄严”的西方社会。塔尔在最后一幕中飘流在河上,才遇到了马龙白兰度片场里跑出来的动物。这是有趣的类比,马龙白兰度本人,便是最为自我情感化的表演艺术家,而他深处原始森林与河流深处的电影则无疑是《现代启示录》,正以“从当代社会性外表到原始自我的回归”为主题。塔尔钻入了瀑布,才听到了大自然的和谐声音,进而恢复了对音乐本身的纯粹聚焦与诠释能力。“对原始的回归”,正是导演给出的出路,并在最后一个画面中达到了高潮:倾听塔尔音乐的观众,并非西方古典乐演出要求之下的正装穿着,而是匹配游戏内容的原始部落打扮。以“正确价值观”为核心构建,并随时进行“外部审视”的西方世界,就此被完全地否定了。
《塔尔》以古典乐行业映射社会,展现了其在种种正确的普世价值观的“绑架式定义”之下的后果。这必然地引发了古典乐评论人的一些争议,认为其是对古典乐界的丑化。然而,因为社会大环境的走向,古典乐界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甚至由于资源的匮乏,受众的有限,市场体量与教育产出所决定的供需紧张,反而成为了“最需要人脉与包装“的行业。
一个年轻音乐家,老师是谁,是不是格拉夫曼或者巴伦博伊姆,看好他的指挥家是谁,是不是阿巴多、蒂勒曼,或者至少是帕沃亚尔维,拥有怎么样的身份属性,是不是杜达梅尔那样的“拉美+自由斗争”的正确buff叠加。并且,音乐家的长相如何,演奏是否有着极度吸引眼球与感官刺激的dramatic,能不能在唱片封面与现场演出中“起范儿”,也变得愈发重要起来。
而在另一方面,指挥和乐手人人平等的观念,吻合当代的普世观念,但却不利于音乐的演绎,指挥的理解无法完全执行,导致了当代演出的“千场一面”,缺乏了曾经富特文格勒等人给到的丰富与个性。由此而观之,《塔尔》将社会缩影的载体选在古典乐行业上,倒也不算偏差太大。
古典乐很伟大,当代的古典乐行业却未必如此。正如同,那些价值观本身很伟大,用它们来进行“赋予定义与施加标准”的社会性行为,却未必如此。或许,这样的互文特性,也正是导演捕捉到,并将古典乐行业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放大,由此构建出影片表意思路的出发点。
退一步讲,以古典乐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造与加工,也是创作中并不罕见的事情。“完全忠实于一切客观现实”,是人们对电影创作的一种习惯性标准。它不需要更深度的分析,人人皆可参与,因此分外有市场,但却淡化了电影“表达导演设定的某一主题”的个体表达性质,将它当成了绝对的纪录片,甚至新闻联播。

《金发梦露》遇到的差评,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此---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梦露,是基于他的表达需要的梦露,而人们的梦露,则是基于时代观念思潮的梦露。而问题便在于,没有人真正完全了解客观存在的梦露,但后者庞大的人数与“时代性正确”,让它成为了看上去的“客观真理”,并以此驳斥了多米尼克自己的那个少数派梦露。
《塔尔》就是《塔尔》,片中的古典乐界就是片中的古典乐界,仅此而已。至少,它表现的古典乐,以及对音乐家和指挥家的表达运用,远远比“古典乐真伟大,你听过吗?《卡农》”这种透着“强行古典乐”的《无伴奏》等作,要来得高明多了。而它对于凯特布兰切特的使用,也与后者在《蓝色茉莉》中演绎的那个逐渐从富有阶层的包装中崩溃的贵妇角色,有着强烈的互文效果,同样十分巧妙。
它将“聚焦自我的情感“归为自私,将“对外迎合的包装“定成虚伪,对立的两重侧面皆是黑暗,从而否定了这个时代本身。而貌似高大的塔尔本人,其崩塌正是同样光彩的古典乐行业的坍塌,成为这个“表面上正确繁荣“的时代的缩影。而美妙的音乐,便是这个时代与这部电影中,始终缺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