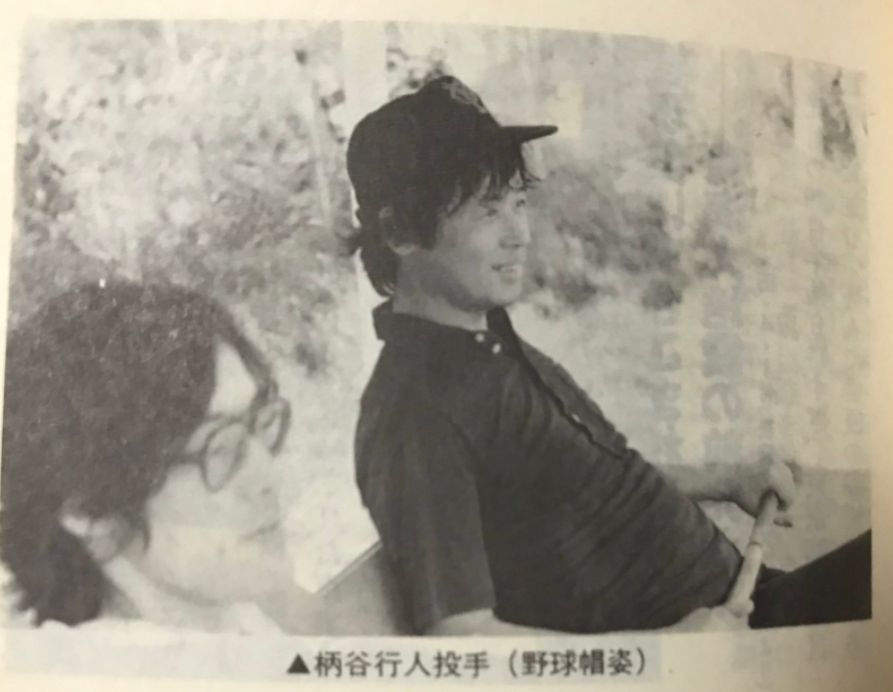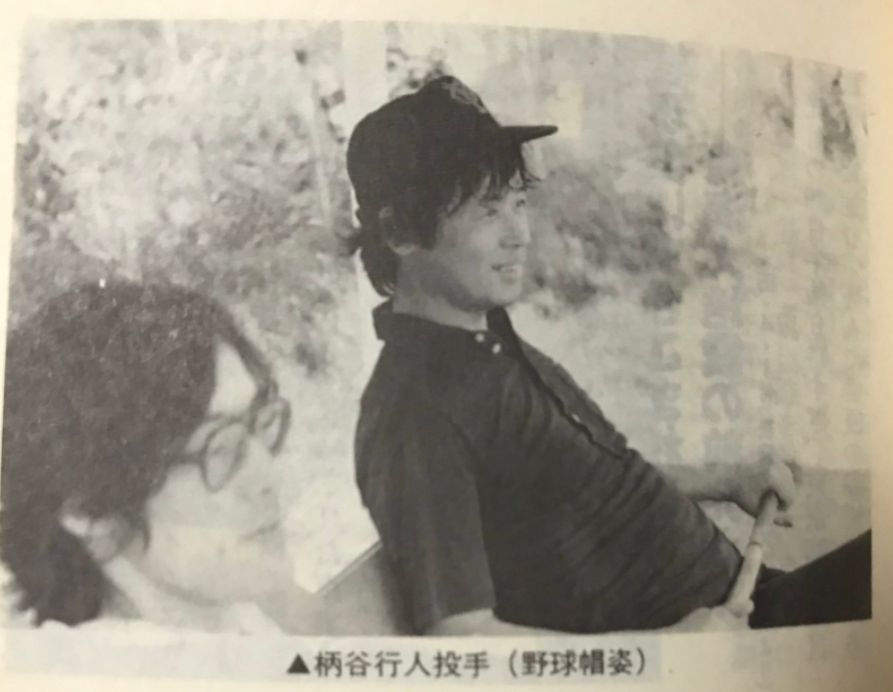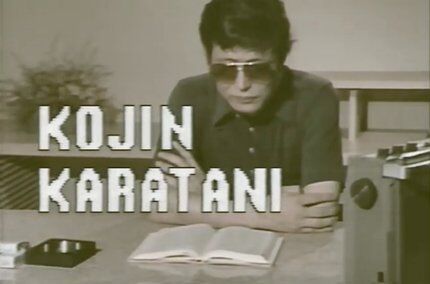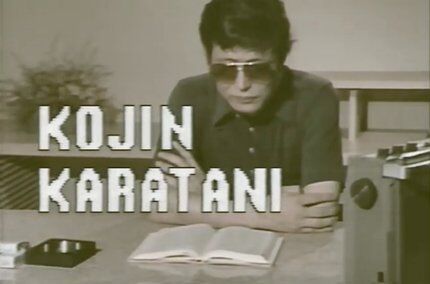【完结】柄谷行人《探究Ⅱ》第三部:关切于世界宗教 第七章 赠与和交换 与后记
《探究II》原作者:柄谷行人翻译:太玄一点校对:想看穿着lorica hamata扔罗马长矛的高华怎么被破四旧屋顶日语角提供校对协作帮助,欢迎加入屋顶日语角进行志愿翻译!译文遵循非商业化学习用,可规范转载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屋顶现视研:柄谷行人《探究Ⅱ》第一部:关于专名屋顶现视研:柄谷行人《探究Ⅱ》第三部:关切于世界宗教||第六章 无限与无限定1
我们假想了一个没有内外之分的交往空间,认为诸多共同体就此将自身折叠起来,从而形成了其“内部”。交往空间在共同体之前就存在,现在也存在——如今,它是被货币所媒介的、不断重新组织的诸多世界性关系的网眼。它是一项各个共同体(国家)无法将其分隔开来的、跨越国家的运动,不仅任何共同体都无法从中自立出来,不如说它们反而依存于这一交往。尽管如此,各个共同体都将自己从中隔离出来,以图保持作为“内部”的同一性(identity)。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无论是扩大还是缩小共同体的规模,都是一回事。例如,西欧的经济共同体(EC)虽然超越了众多国家的对立,但也不过是为了相对其外部(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的共同性。苏联集团可以说也一样。然而,它们再现了现代国家之前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谓的世界帝国并没有掩盖世界整体,而是必然保有其外部、因而遵从着共同体式的逻辑(内外分割)。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村落、家族、各种各样的集体、或者说像“个人”那样的小型共同体。谈到共同体,我们通常会想到村落,但“个人”只要有内部和外部,同样是一种共同体。它们虽然在思想上保持着内部的同一性,但实际上却属于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情境(context)。所谓的“未开化社会”也一样:显然,它们不可能孤立于交往空间而存在,并且这一情况不是由某一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才开始的,只能说它原本就是这样。
有些人批判始于“个人(意识)”内省的哲学,主张共同体(system)的先行性。然而,如果认为哲学始于共同体(系统)的话,就变得和哲学始于“个人”的观点相同了。如果说个人已经是社会性的,那么共同体就也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共同体与社会性的事物相对,它将自身封闭起来,就像是一个自立出来的世界那样存在着的系统。我所说的交往空间,当然是社会性的(复数体系的)。进一步地说,只有它才是“历史”性的。与之相对,具有开端(因而具有终结=目的)的历史只是“叙事”,不过是共同体的同一性之中的虚构罢了。
共同体脱离了“社会性的”交往(交通\交换 = communication),从而封闭了自身,这正是内部与外部的分割:被限定和组织了的内部(cosmos)与无限定的、没有被组织的外部(chaos)。在共同体中,最大的禁忌正是这一界限的设定本身。正如后文即将论证的那样,乱伦禁忌也是由于与外部相区别的内部的组织化而产生的。无论是“冷社会”还是“热社会”(列维·施特劳斯),对于共同体而言,关键是保持内与外的界限,换言之,是脱离社会性的交往而封闭自身。
我们不能只从共同体的内部来考察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共同体作为一项孤立的事物来对待。只要这样做,很可能就会陷入共同体式的思考,因为共同体所倾注努力的,是保持内部的同一性(identity),也即其自身仿佛具有某种自律性一般而行动。虽然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自律性,但正因如此,共同体才将威胁到自身内部自律性的事物放逐到“外部”,并将其视为由“外部”而来的事物。
然而,这样的“外部”只是相对于共同体的“内部”而存在,实际上仍然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这一恐怖的外部(弗洛伊德)不过是亲切(heimlich)的内部的自我异化罢了。这样的外部(异界)以及属于那里的异者(stranger),已然是从共同体出发而看到的事物,因而对于共同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cosmos和chaos、中心与边缘的辩证法,就此成了共同体的存续装置本身。
共同体原本就拒斥的外部和他者,存在于社会性的交往空间之中。一切共同体都排除了“社会性的事物”,但不能没有它而继续存在。因此,“社会性的事物”暗中出现在共同体的外部(异界)。再次使得共同体(文化)活性化的力量,不只是来自于无限定的外部(chaos),也来源于像这样伪装了起来的“社会性的事物”。
2
“未开化社会”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指古代社会(morgan),或是其偶然幸存下来的部分。例如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他们并不是与玛雅或是印加文明完全没有关系。正如19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拒斥文明与阶级社会、创建了公社那样,印第安人或许能够有意识地自我封闭起来。(实际上,在美利坚合众国,也有从欧洲移居而来的宗教团体就此自我封闭地变得“未开化”的例子。)他们积极地创建了绕开通向文明化与阶级分化、或者说国家形成之路的组织。读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作品,我不禁这样思考。
然而,这件事本身就是交往空间先行于未开化社会的证据。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野性的科学”,终究不是孤立的部族社会能够获得的知识。例如,即使有拒斥电力的嬉皮士公社,他们也仍然保持着已经知道的农业与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与之相同地,未开化社会可以说接受了某些事物,也排斥了某些事物。
最为被排斥的是社会性的交换。这一点看似与在交换体系中把握未开化社会的列维·施特劳斯的看法相悖,但正如我们之前区分了社会与共同体那样,我们应当把交换分为社会性的交换与共同体内部的交换。后者被称为赠与。支撑着赠与这一交换关系的,是互酬性(reciprocity,相互性)的原理。
列维·施特劳斯引用了如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如今的法国南部,被请饮酒却不把它喝掉是十分无礼的,是一种敌对态度的表现。同样地,例如在家庭内部,通常来说交换会采取赠与的形式。在这里同样存在相互性,被赠与者被迫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亏欠感。这一相互性的特征,是赠与及其还礼(反向给予)之间没有等价的必要,并且也没有办法比较。还礼这件事本身才是重要的。如今的资本制社会也一样,在家庭内部,劳动是一种赠与。例如,正如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将主妇在家庭内部的劳动用交换这一术语、也即将其作为雇佣劳动来看待也未尝不可。然而,我们不能把赠与这一交换关系翻译为一般的经济交易。问题不止在于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试着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和子女对此的还礼。如果在“社会性的”交换这一术语上来看,它们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非等价交换。然而,赠与这一交换关系正是这样的东西。
在共同体中,无论货币经济怎样渗透,都残留着作为赠与的交换关系。例如,在日本大部分的企业中——这也是广义上的“家”——经营者与从业人员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买卖(契约)关系,但同时在实质上也是赠与这一交换关系,它是相互的(reciprocal)。因此,这些企业是难以接受生人(异者)的排他的共同体。
无论什么情况下,习惯都不会是不合逻辑的。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考察其外在性的含义与经验性的表现之上,而是必须抽出整个关系的体系。习惯不过是这一体系的表面。
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整体供给(全体的給付,《探究Ⅱ》译者注)的一个方面,婚姻提出了整体供给的一个例子,同时也伴随着全体供给的机会。这些整体供给,是指被称为物资和材料、特权、权利、义务等的社会性的价值,并且它们以女性为对象。结构起婚姻的总体性的交换关系,不是在各自给予和得到一些东西的一男一女之间,而是在由男性成立的两个群体之间成立的。在这里,女性不是以这一关系的一方、而是以被交换的物品之一的姿态现身。仿佛理所当然一样,即使女儿的情感被纳入考量,这也仍然是真相。即使她同意了提议的婚姻,她也只能以此催促和允许交换的实施,但无法改变“交换”本身的特性。即使在婚姻被认为是个人间的契约的我们的社会中,这一观点也必须被严格遵守。这是因为,婚姻在一对男女之间展开了一个互酬性的循环,虽然伴随着这一婚姻的责任规定了它各式各样的特征(種々相,《探究Ⅱ》译者注),但它不过是一个更大的互酬性循环的次要样式罢了。正是这一更大的循环,保证了一个男人与身为某人的女儿或者姐妹的一个女人的结合——通过这个“某人”与这个男人或者其他男人的女儿或者姐妹的结合来保证。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第八章,暂无中译本
这一体系性是通过对乱伦的禁止而得到的。反过来说,对乱伦的禁止是为了形成作为赠与的交换体系不可或缺的“逻辑性的”必要条件。对乱伦的禁止不是历史性的问题,也不具有“根源性”。列维·施特劳斯不是从心理学上,而是将其作为使得“结构”得以可能的、逻辑性的必要条件来看待未开化社会中对乱伦的严厉禁止。
另一方面,规则体系通过对乱伦的禁止而成立,列维·施特劳斯在这一层面上承认来自自然的文化自立。的确,这样的规则体系不是来源于“自然”,但这一“文化”,即排除了交通\交往的、共同体式的文化,也不处于原始阶段。与这一“文化”相对立的不是“自然”,而实际上是“社会”,因为一切共同体都已然处于社会性的交往之中。然而,这一点却被隐藏和遗忘在了文化(内部)/自然(外部)的分割之中。
我之前曾对“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与“语言系统”(索绪尔)做出了区分。前者是“社会性”的,后者则是“共同体式的”。假设如此,那么列维·施特劳斯自然可以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尤其是音韵论)适用于对未开化社会的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基于对communication = 交换问题的抽象而成立。它之所以能适用于未开化社会,是因为在未开化社会中,“社会性的事物”已然被排除在外了。
3
然而,列维·施特劳斯不是单纯的结构主义者。他没有忘记未开化社会也是“历史性”的、因而从属于交往空间。他拒绝将未开化社会对应于历史的初级阶段的“进化论的解释”,以及仅仅将未开化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来考察的“功能主义”。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将一个共同体作为孤立的事物来考察,这种观点才应当被否定。
把研究限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上可以做出极有价值的工作。经验证明,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出自那些在一个特定地区内生活和工作的调查者。但是必须避免对其他地区下任何结论。况且,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种时下状况,那么他首先就会成为一种幻觉的牺牲品,因为一切都是历史。
——《结构人类学》第一章《绪论:历史学与民族学》,译文选自张祖建译本
“一切都是历史”在我们看来,意味着一切封闭的共同体都处于交往空间之中,这一点、以及甚至“封闭”本身就是历史(事件)。所谓“结构”,就是指从属于这种历史性的同时,共同体为了保持自我封闭的自律性而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的“同一性”(变换群)。并且这一“结构”有着怎样的含义(功能),是依存于各个共同体的历史的。
所谓历史(Geschichte),换言之就是在交往空间中的事件。一切共同体都将其转变为了叙事(history),但列维·施特劳斯的目标,可以说是穿透这种结构才能看到的“历史”。当然,这不是历史学家所把握到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无论具有怎样的实证性,叙事都已然潜入其中。从未开人开始类推原始人的想法,就是其中之一。
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反对将未开人的思想与幼儿的思想类比的想法。未开人中原本也有幼儿。“即使是最未开化的文化,也总归是大人的文化。”并且未开人也总是认为文明人是“幼儿的”。一般来说,一种文化(共同体)会将其他文化视为“幼儿的”。但另一方面,列维·施特劳斯十分重视“幼儿”,这不是因为在幼儿之中能找到“未开人的思维”,而是因为在这里能找到多形的社会性(social polymorphe)。
例如,幼儿在其最幼期能够发出一切声音、学习一切语言,但一旦选择了一种语言,就“失去了无法取回的、在音声学方面敞开的无限的可能性”。或许巴比伦神话的根据,不是在于过去曾经存在一种共通的语言,而是在于任何人都有过一段对一切语言“敞开”的幼年期。然而,作为这一多形的社会人,幼儿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成长的时候,恰恰失去了这种“社会性”。
虽然大人的知识图式根据人所属的文化和时代而分化,但它都是由一种普遍的基础精心制作出来的,这种基础比一个特定的社会所能够使用的基础更加无限丰富。其结果是,每个孩子从出生时开始,就在萌芽时期带有只能在各种文化和时代中选择、保持和发展其中一些的可能性的总体。每个孩子都在出生的同时,就基于其粗糙的知识结构的形状,享有了人类从远古时期开始对自己与“世界”及与“他人”的关系加以规定所使用的手段总体。然而,这些结构是排他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只会从被呈现出来的一切之中整合特定的要素。因此,每个社会性组织的类型都代表了一项集体以之为义务的、使其生存下去的选择。按照集体的要求做出选择、拒绝与大人的思考相比较,孩童的思考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基层,并且在这一阶段,结晶化尚未发生,仅仅不完全地凝固的各种形态之间的交流尚且是可能的。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列维·施特劳斯,尚无中译本
“未开化社会”也好,其他什么也罢,列维·施特劳斯在这里难道不是在暗指共同体以前的人类吗?——多形的社会人,或者说作为普遍的基层的原始人。例如,被列维·施特劳斯誉为最早的人类学家的卢梭,他所说的“自然人”不是共同体式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虽然厌恶被封闭在共同体之内,但另一方面,他们和任何人之间的“交流都尚且是可能的”。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假说。然而,对于颠覆将共同体式的存在方式视为人类的本性(自然)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假说。
4
对社会性的事物即交往空间的先行性之假定,是一种假说。尽管如此,它不是一个思辨的(speculative)假说,我们当然也无法从实证的(先历史学的[先史学的])角度确认它。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实证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叙事(物语)性的思辨正大摇大摆地施展着自己的权势(堂々と幅を聞かせている,译者注)。例如,人们往往认为最初只存在小型的家族,其随后向外扩张为部落、共同体、国家以至帝国。这完完全全是神话式的思考。
所有流传下来的神话,都属于讲述共同体如何形成的类型,是共同体为了确保内在的同一性而写就的叙事。比如说,正如前文所述,《创世记》记载了亚当和夏娃被神创造出来、人类由此开始繁衍。然而,该隐却和其他部落的女人结了婚,那么其他部落是谁创造出来的?这一疑问在《创世记》中被无视了,因为对于一个神话来说,重要的只是共同体的人类的同一性(identity)。它是反复与共同体的起源有关的叙事,而不是历史(事件)。
后文所述的历史性的体验,已然先行于《创世记》被写就的时间点。许多游牧民族的部落不是根据血缘关系,而是根据盟约(契约)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是否是犹太人的判定(ユダヤ人であること,这里说的应该是犹太式的存在,译者注)不是基于血(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契约。然而,这一点却被颠倒过来,仿佛所有成员都来源于亚当和夏娃。
《创世记》不只是巴比伦神话的变型,例如,它与日本的《古事记》的创世神话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正如高群逸枝所指出的那样,在《古事记》中,原本“多祖一氏”的情形被颠倒为了“一祖多氏”。也即,许多部落被皇室所支配的事件(历史),被颠倒为了所有部落都由一个氏族(皇室)派生(差异化)而来。对于共同体的创世神话来说,这一现象无处不在。叙事就是这样遮蔽“历史”的。
然而,圣经旧约与一般的创世神话所不同的是,从亚当与夏娃时期开始,“契约”的观念就已经被写入其中了——不是通过血缘的系统(出身),而是在与无限者的“契约”中发现了共同体的共同性。也即,赋予与“共同体式的”事物相对的“社会性的”事物、以及与同一性相对的多数性优先地位。在犹太共同体之中,这两种倾向不断地争斗。不用说,预言家的系列是站在“社会性”这一侧的。
一般来说,共同体的创世神话将原本的多数性与社会性掩盖在自我差异化的同一性系统之中。当然,即使批判神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应当批判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对小型家族发展为大型共同体、随后交易由此起步、货币由此形成的神话式的思考产生怀疑。
例如,马克思也认为交换始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接着,在这一“交换的历史性的扩大与深化”中,货币必然地——“法语版”为自然发生地——形成(《资本论》)。然而,是先有共同体,然后产生交换的吗?被命名为“旧石器时代”之时代的痕迹,展现出其涉及范围之广。这些痕迹意味着石器本身曾经是交易的对象,也就是说,交换在各个共同体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共同体虽然通过从这样的交往空间中自我封闭、从而形成自身,但交往空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可以说在各个共同体的“外部”(间隙)中生存了下去。
为什么交往空间会被封闭到诸共同体中呢?可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伴随着种植(农耕)的定居。另一方面,畜牧在其性质上是非定居的,后者虽然也是共同体,但其内/外的分割并不在实际上的空间之中。它在实际上的空间中没有任何分界。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游牧民族将原本的交往空间保存了下来。江上波夫专注于研究欧亚游牧民族(nomad)在其文化样式上所具有的、与实际空间距离无关的、涉及大范围的“普遍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化,是定居性的共同体的特征。
这两种差异基本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社会性的交换与共同体式的交换(赠与)之间的差异。例如,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在本书中,我们一直试图证明,所谓交换不是买卖的一个方面,而应在买卖中看到这一交换的一个方面。”(《亲属关系的基本原理》)换言之,他想说的是赠与的交换关系才是本源性的。当然,关于“未开化社会”,我们不能像弗雷泽那样从市场经济的交换(买卖)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赠与的交换关系,但也不能像列维·施特劳斯那样,将“社会性的”交换关系与如今已经完成了的市场体系中的交换(买卖)一视同仁。这是因为,使得买卖得以可能的货币究竟从哪里来、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不是自明的,反而是最大的谜题。
货币不是来源于赠与的交换关系,这一点是显然的。货币是从“社会性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它不是单纯地来自定居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交易。正如经济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未开化社会”中的货币不过是一种象征。也就是说,它从属于赠与的交换体系。货币、也即在所有共同体中都通用的“信用”——这不是共同体的“共同幻想”之类的东西——不可能由此产生。它只能产生于没有内部与外部之分的社会性的交往空间。
马克思这样说道:
这种一般价值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资本论》第二章《交换过程》,译文选自中央编译局译本
当然,马克思没有通过上文这样的历史性的说明来论证货币的生成。在之前的“价值形式论\价值形态论”中,货币(一般价值形态)之谜被处理为了唯有通过他所说的“抽象力”来解释的东西。这是因为,可以说它与货币之无限性的秘密息息相关。
货币的无限性。正如前文所述,它不是与有限相对的无限定,而是被封闭起来的现实的无限。换言之,货币作为这种无限,已经预先包围了各个共同体。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交易无论怎么扩大,也产生不了一般价值形式。反过来说,一般价值形式有着符合一切自我封闭的共同体的强制力。
从共同体出发,是无法说明货币的社会性=无限性的。同样地,这样也无法说明世界宗教。世界宗教可以说常常显现在世界市场之中。像柏格森说的那样,首先有封闭的社会,其随后通过世界宗教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不过是无稽之谈。世界宗教的“世界性”,在于没有内/外之分的交往空间的回归,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因而它对于共同体的世界而言是强迫性的显现。然而,不能将其与共同体的强迫症的性格相混同。它的强制力来源于“社会性的事物”的无限性。因此,与列维·施特劳斯相反,我必须这样定论:赠与的交换和买卖的交换相同,只是社会性的交换的样态之一。
本书在1986年到1988年秋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连载于《群像》,但在出版的时候完全更换了文章的顺序。第一部《关于专名》原本最后才写,而第三部《关切于世界宗教》则是最早写下的。这一变换之所以得以实现,虽然一方面仰仗了文字处理机器,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每一章基本上都在不同层次上探究同一个问题。
我在《探究Ⅰ》中说过,唯我论不是指“只有我”,而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假定“我”适用于所有人。这是以内省为起点的思考,它不仅存在于认识论和现象学之中,也同样是存在于否定内省的语言学和其他各种科学之中的框架。为了批判唯我论,我考察了“这个我”与“其他的我”并非同一、并且也不属于同一个规则体系的条件,在“出售-购买”和“教授-学习”的非对称交流关系中寻求这一条件。他者只会出现在这样的关系之中。
在《探究Ⅱ》中,我试图从其他观点出发捕捉这一问题,也即把并非是所有人的“我”的“这个我”,当作单独性来看待。它不是在一般性之中看到的个体。然而,作为单独性的个体这一问题,已然不能在认识论的框架之中考察了。于是,我将其移到了逻辑学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在《探究Ⅰ》中被称为唯我论的思想,在这里对应于将个体置于类别之中看待的思考,也即个体(特殊性)-类别(一般性)这一回路的思考。单独性存在于这一回路的外部,它与孤立的我、或是唯一的物之类的东西毫无关系。单独性所指的必定是不含任何一般性的“这个我”或者“这个东西”的“这个”,但它不同于起指示作用的“这个”。之后,专名问题的考察就从这里开始。
那些探究单独性问题的人未必没有到达这一步,但他们的思想大多是拘泥于“这个我”的存在主义[实存主义]的思想。然而,对单独性的特别关注其实并不是拘泥于“我”,因为“我”也好,“物”也罢,其无可替代的单独性才是问题所在。这一点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是不可能的。与孤立的事物和单一的事物相反,正如《探究Ⅰ》所展示的那样,通过专名而发现的单独性与社会的、即非对称的关系有所联系。
第二部提出了如下观点:笛卡尔的cogito不是个体(主观)而是单独性。也就是说,cogito不是一般性的我(主观),反而是从这种一般性的我或者说共同的规则体系(共同体)之中脱离出来的外部的、单独性的实存。强迫并促成这样的cogito的,是差异,是他者性。笛卡尔所说的“神”的观念,可以说就是这一差异以及他者性的绝对性。斯宾诺莎推进了这一观念,将上述的外部与超越都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本身视为神。对一切表象的怀疑,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世界”的原因。因此,斯宾诺莎的神(普遍性)是与单独性或者外部的实存分不开的。
第三部明确了“类别-个体”的回路如何在社会科学中作为框架制约着我们的思考。这一章为何是“关切于世界宗教”?因为这样的框架,或者说作为废除了内部与外部的区别之物的“世界”这一观念,首先是作为世界宗教而出现的。当然,它与共同体或者说共同体的宗教完全不同。它产生于共同体的“间隙”或者说“交往空间”,并且作为解构共同体的、强迫性的表象而出现。在“类别-个体”的逻辑之中思考得出的理论,结果只会使得共同体必然化。
可以说本书的结构就是像这样,从抽象的层次进展到具体的层次。当然,认为第一部和第二部难以理解、难以下手阅读的人,也可以从第三部开始阅读,因为我实际上就是从第三部开始写作的。尽管如此,我始终将更加具体的现实情况放在心头,但为了应付这一点,我又必须把问题放在更加基础的东西上。像第一部和第二部这样的探究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在《探究》的连载中持续追问的,可以说是在“间隙”或者说“外部”生存的条件和根据。可以说,它是“超越论的”的同时,也是对“超越论的动机”本身的质问。当然,它不仅是理论的问题,也是生存的问题。所谓《探究》,是一种重复。
本书连载于《群像》期间,每个月都会劳烦三木卓先生。本书出版的时候,一如既往地承蒙渡边胜夫先生的照顾。在此向二位表达深深的感谢。讽刺的是,我在停止了本书的连载之后,渡边先生就任了《群像》的总编,我也开始了《季刊思潮》这一杂志(的工作)。偶然的是,我们积极地参与进现实性的情境[文脉]之中。最后,在此对每个月都阅读这一几乎没有人读的连载的、确确实实地给予了我建议与鼓励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1989年4月15日,柄谷行人
我将单行本转为文库版发行,是因为(单行本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年。当初为了出版这本书而修改在杂志上连载的部分,这已经是昭和末年的事情了。因此,虽然距今大约过了五年,但它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是很久以前了。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或许理解我所关心之事的人很少,更不可能期待国外有谁能够理解。但我感觉到,我所思考的事情如今在美国终于开始带有一些现实性了。首先,被后结构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所解决了的“主体”的问题,不得不再一次被提出。这一问题大概必须作为singularity而出现。其次,它同时会与在multicultural(社会性的)空间中的差异有关。这恰恰说明,同一时代中人们的思考最终会变得相似。
一本综合总结了《作为隐喻的建筑》、《内省与溯行》、《探究Ⅰ》等著作的书不久就会以英语出版,而这本书今后也会为了以英语出版而改写。然而,它原本是作为“探究”而被写就的。虽然有一个模糊的预想,但一边写作一边思考,什么时候、会产生什么想法却是无法预测的——这本书就是以这样的做法写就的。秉承这一做法,我现在也正在写作《探究Ⅲ》。只有当写下这些想法的时候,我才会有“正在思考”的实感。
——1994年3月3日 柄谷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