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应该有的模样
 《邪不压正》好不好看?
《邪不压正》好不好看?
好看,也不好看!好看在于开头部分,前半小时非常棒,大开大合,纵横捭阖,恣意汪洋,带劲有气魄。然后,结尾的部分也还好,看着同样过瘾。但中间的部分嘛,作为一部完整的影片,实在有注水的嫌疑,搞了很多事却不在点子上,挠痒没挠到实处,尽管细节上不少地方很好玩,但作为整体一点都不好玩。简直就像姜文在苛意捧自己媳妇,所以她的这条线给了过多的戏,超出了观众可接受的程度。
那《邪不压正》值不值得看?
值!毕竟导演是姜文。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姜文的风格非常明显。毕竟当下的中国影坛,只有一个姜文,对于真影迷来说,他的片子都值得看一看。
 中国有个性的导演不多,能够在影片中任性耍个性的更不多。观众看电影看着不爽,但姜文并不在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拍电影就是要先让自己爽了,然后才是观众爽不爽的问题。很明显,《邪不压正》里姜文玩的很爽。这种不讨好观众的想法与玩法,对中国电影的边界,对电影工业来说,非常难得,尤其这还是一部商业气质很浓的影片。在整个华语圈,除了姜文也没有谁敢这么玩了?冯小刚算一个,但他也要搂着点,在严肃影片玩脱之后,还是乖乖去拍喜剧来找补,到底还是要向商业低头。而姜文,《一步之遥》没玩好,但《邪不压正》还是照样,稍有收敛,但依旧放旷,这种脾性,其实非常难得。
中国有个性的导演不多,能够在影片中任性耍个性的更不多。观众看电影看着不爽,但姜文并不在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拍电影就是要先让自己爽了,然后才是观众爽不爽的问题。很明显,《邪不压正》里姜文玩的很爽。这种不讨好观众的想法与玩法,对中国电影的边界,对电影工业来说,非常难得,尤其这还是一部商业气质很浓的影片。在整个华语圈,除了姜文也没有谁敢这么玩了?冯小刚算一个,但他也要搂着点,在严肃影片玩脱之后,还是乖乖去拍喜剧来找补,到底还是要向商业低头。而姜文,《一步之遥》没玩好,但《邪不压正》还是照样,稍有收敛,但依旧放旷,这种脾性,其实非常难得。
大陆电影导演届,在张艺谋与陈凯歌失去锋芒之后,贾樟柯作为文艺头牌,始终没有拿出一部有票房说服力的作品,这挺遗憾,也让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能够在商业与艺术间掌握平衡的人,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姜文,这也是他可以任性、可以嘚瑟的最大资本。当然,他也不是瞎嘚瑟,而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冲这一点,《邪不压正》就值得看看。
就像我们去美术馆看画展,花钱也不一定能看得懂那些的画作的内容,但还是可以感受到美与力量。《邪不压正》也是如此,看不全懂,但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冲击力,而且让人跟着一起激荡。
 《邪不压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邪不压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邪不压正》的好话,这里不多说,毕竟已有很多人评价过,而且写的很好了。这里只探讨一下可能性问题,从一些旁证上来说一下《邪不压正》的不够优秀之处。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张北海是一位传统文人,老北京,解放战争之前青少年时期的他生活在北京,后来伴随国民党败军退到了台湾,再后来去了美国,长期在联合国任职。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革命元老的关系非常好,与宋哲元、张自忠等军中中坚私交也甚笃。张北海从小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深受影响,其实《邪不压正》中姜文饰演的蓝青峰,原型就是张北海自己的父亲,片中最后露出的张将军即张自忠(不过,片中将张自忠演绎成为了一名花帅就实在是无理了)。张北海出生在东城区的胡同里,青年时期他有个著名的家教老师,叫叶嘉莹。叶家与张家关系不错,身为诗词大师的叶嘉莹因私谊被请来免费教了张北海两年多传统文化,督促他背下了全本的《论语》,为张北海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当他在联合国工作的时期,写作了大量散文,因为文笔优美,误打误撞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名著名作家。《侠隐》是他退休之后创作的一部武侠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好多人都想拿到版权,来进行影视改编。结果,最终被姜文拿到了版权,并进行了改编,眼下的《邪不压正》就是最终改编的成果。对了,张北海还有个著名的侄女,叫张艾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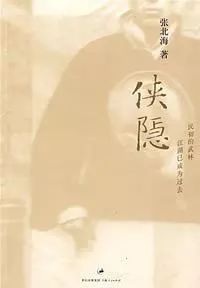 好的小说容易诞生好的作品,两者相得益彰。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的电影版,就相互成全,各自都成为了经典。国外这种经典,更是数不胜数,无论是《教父》,还是《阿甘正传》《发条橙》,或者《指环王》系列,小说与电影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像《阿甘正传》与《发条橙》,电影对小说的改编非常大,甚至改编了原著的风貌,但似乎不影响各自成为经典。还有一些小说写的一般,但电影异常精彩,像《黑客帝国》《海上钢琴师》《饥饿游戏》等,还有华语的《卧虎藏龙》。
好的小说容易诞生好的作品,两者相得益彰。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的电影版,就相互成全,各自都成为了经典。国外这种经典,更是数不胜数,无论是《教父》,还是《阿甘正传》《发条橙》,或者《指环王》系列,小说与电影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像《阿甘正传》与《发条橙》,电影对小说的改编非常大,甚至改编了原著的风貌,但似乎不影响各自成为经典。还有一些小说写的一般,但电影异常精彩,像《黑客帝国》《海上钢琴师》《饥饿游戏》等,还有华语的《卧虎藏龙》。
相比较而言,《侠隐》算是一部经典。作为武侠小说,这是一部不一样的武侠。张北海说是写武侠,其实是写的市井生活,所谓“侠隐”,就侠义精神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隐藏于时代的烟火色之后,古色古香,简直是一部能吃能看能吻出香味的作品。
江湖侠义、恩怨情仇,不过是串起全书的一条线,古书的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北平,张北海费尽心力,花了六年多的功夫,最大程度地还原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北平城的模样。张北海一直对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北京(那时叫北平)格外感兴趣,因为那是所有的儿时记忆,《侠隐》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出那个时期北京的样貌。他做到了,一个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北京,通过《侠隐》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出来。在《侠隐》里,那一条条胡同: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那一道道美味: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碗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那一个个名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都宛如眼前,活灵活现。
 高手写作,总能在一篇之中传达出更多的状味。郁达夫早在1934年写的《故都的秋》,一篇文章就把当时北平萧索与闲散的风味写了出来,这就是高手。张北海用了整部书的篇幅,同样讲出了旧北京的风土人情。而到了《邪不压正》,这种风味一下子就没了。尽管姜文在道具上非常用心,但看完《邪不压正》给人留下的印象大概只有北平的屋脊,再就是可以藏人的钟楼了。其他,就淡了很多,声香味全没了。
高手写作,总能在一篇之中传达出更多的状味。郁达夫早在1934年写的《故都的秋》,一篇文章就把当时北平萧索与闲散的风味写了出来,这就是高手。张北海用了整部书的篇幅,同样讲出了旧北京的风土人情。而到了《邪不压正》,这种风味一下子就没了。尽管姜文在道具上非常用心,但看完《邪不压正》给人留下的印象大概只有北平的屋脊,再就是可以藏人的钟楼了。其他,就淡了很多,声香味全没了。
这其实没有办法,小说的改编太难了。《邪不压正》只抽取了《侠隐》中的恩怨情仇,无法原样地展现出小说中城市的模样。即便有,也不是张北海笔下的北平,而是姜文眼中的北平。姜文对屋脊格外有感情,《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等片里都有屋脊,《邪不压正》中将屋脊再一次放大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这大概是姜文记忆中的青春,当时他在军队大院野蛮生长,大人不管,成群的孩子就上屋踩瓦、嬉戏打闹,成为他最为绚烂的记忆,于是当需要再现旧时北京的模样时,在他脑海里复活的不是张北海笔下的东城巷子,而是皇城前的一片片屋脊。
 再就是故事框架,影片限于篇幅,只是取了一个故事的壳。李天然回国复仇,是整个故事的框架。小说中,是通过这个复仇的过程,串出了整个北平城的风味。李天然懵懂着回到北平,然后遇到了裁缝关巧红并爱上了她,中间夹杂蓝青峰等人,引发出更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所有的关系,都是为了展现北平。
再就是故事框架,影片限于篇幅,只是取了一个故事的壳。李天然回国复仇,是整个故事的框架。小说中,是通过这个复仇的过程,串出了整个北平城的风味。李天然懵懂着回到北平,然后遇到了裁缝关巧红并爱上了她,中间夹杂蓝青峰等人,引发出更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所有的关系,都是为了展现北平。
而影片中,复仇也是主题,蓝青峰与李天然之间的关系在设置上也更进了一步,只是他与关巧红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突兀了,与复仇的主题明显偏离。这就是整个影片的中间部分都显得格外尴尬的主要原因。看起来,就好像是姜文在不停地位自己媳妇周韵在加戏,一直加到脱了轨。这就是小说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冲突,取舍没有达到平衡,以至于小说中看起来顺其自然的情节,到了影片中就显得尴尬,让人不明所以。
 影片另一处改编上也存在错位,更显得分裂。本来,李天然为师父报仇,针对的就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朱潜龙以及日本人根本一郎(原著中叫羽田)。书中,羽田早早就被李天然手刃,而影片中,则李天然则一直要等到朱潜龙与根本一郎凑到一起再杀,这种执念,有些无厘头了。
影片另一处改编上也存在错位,更显得分裂。本来,李天然为师父报仇,针对的就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朱潜龙以及日本人根本一郎(原著中叫羽田)。书中,羽田早早就被李天然手刃,而影片中,则李天然则一直要等到朱潜龙与根本一郎凑到一起再杀,这种执念,有些无厘头了。
张北海并不喜欢金庸梁羽生开辟的新派武侠的道路,他更喜欢王度庐郑证因等老派武侠小说家。金庸讲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王度庐则一板一眼地讲述儒家文化中的“守孝报恩”等传统观点。在《侠隐》中,张北海笔下的李天然行使的就是“为师报仇雪恨”的故事老路,但《邪不压正》中将故事的格局提升了,往民族矛盾上去靠,李天然徘徊于杀与不杀之间,原因被归结于日军会不会对华发动战争上,似乎是李天然一个人决定了战争爆发的时间。这种格局的提升,与小说的格局是拧巴的,而姜文想突破又没有彻底突破,就尬在那里,不上不下。难以让人接受的是,中日战事的爆发系身于北平警察副局长与一个非核心的青龙会成员身上,这不足以让人信服,属于强行升格,非得把王度庐风往金庸风上嫁接,肯定会变得拧巴。
就是这么说来,无论是风格还是故事,大卸八块后重组的《邪不压正》已经完全不是《侠隐》的味道了。两者没有相得益彰,姜文另起灶炉,实际上是拧巴了,并没有改编好。
 姜文自己说,《邪不压正》的故事类似于“哈姆雷特+李小龙大闹卡萨布兰卡”,倒是很准确一些。哈姆雷特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身负家仇国恨,一心想要复仇,却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错过诸多机会。然后卡萨布兰卡中的维克多也是,原本心中有任务,却一头撞入了温柔乡,陷入了爱情的池沼之中。《邪不压正》中的李天然就是会武术的哈姆雷特+维克多,原本心中有大任,结果面对任务,却迟迟无法出手,陷入爱情与养父的纠结之中,节外生枝出许多故事,当然最终他还是化身成为了Bruce lee,大杀四方。
姜文自己说,《邪不压正》的故事类似于“哈姆雷特+李小龙大闹卡萨布兰卡”,倒是很准确一些。哈姆雷特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身负家仇国恨,一心想要复仇,却又犹豫不决,优柔寡断,错过诸多机会。然后卡萨布兰卡中的维克多也是,原本心中有任务,却一头撞入了温柔乡,陷入了爱情的池沼之中。《邪不压正》中的李天然就是会武术的哈姆雷特+维克多,原本心中有大任,结果面对任务,却迟迟无法出手,陷入爱情与养父的纠结之中,节外生枝出许多故事,当然最终他还是化身成为了Bruce lee,大杀四方。
但是,对于电影观众来说,大家想看的是干净利索,是快意恩仇,这也是《让子弹飞》里所呈现的东西。结果到了《邪不压正》中,表面一看还是《让子弹飞》的风格,但只有其形,神韵上已经变了,变得让人无所适从,不是那个味了。同一个饭店,同一个厨子,结果他自己把风味给改了,大家不适应不接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继续回答下《邪不压正》应有的样子?
继续回答下《邪不压正》应有的样子?
将武侠拍出人文情怀来,唯一成功的是李安的《卧虎藏龙》。王度庐的小说,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已经存在很大的隔阂了。小说讲的故事,还是传统的江湖恩怨,但到了李安的手下,就变成了人类的普遍的情感危机。原本,李慕白收剑退出江湖,但偏偏退而不得,被玉娇龙搅浑,再度掀起江湖风波。在李安的表现下,这些恩怨情仇成为了背景,老一辈的大侠李慕白与俞秀莲之间欲说还羞的爱情才让人感到压抑之处,与他们相应的是敢作敢为的玉娇龙与罗小虎之间烈焰版的爱情,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感情选择,不同的人生走向,将一段江湖恩怨展开除了别样的精彩,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文关怀。而且,两辈人对于感情的抉择,几乎与社会一个社会上不同辈分人之间的感情冲突都是一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就具有了普适性,说是武侠,其实美国人看得懂,欧洲人也看得懂。
《邪不压正》在传统文化与民族情绪之间纠结来纠结去,李天然与关巧红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两个人在屋脊上走来走去,飘来飘去,一直没有接地气,没有落到实处。蓝青峰与李天然之间的父子关系,同样是拧巴的。人物之间的感情都飘来飘去,难怪无法感人了。
 那么,在宏大主题的格局的表现上呢?
那么,在宏大主题的格局的表现上呢?
说起民国题材的武侠片,首选还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眼镜王最早想要拍摄叶问的电影,结果被甄子丹抢了先,于是只好另起灶炉,在格局上升级,讲的故事不再只是叶问的故事,而是加入了北派宗师宫二先生的故事。然后,整个故事也变成了大陆拳术,如何流向香港的完整经历,史诗一样呈现出了民国武术的变迁过程。北派的宫二先生,一路向南,遇到了南派的叶问,两人一番切磋,南北合流,并双双走向香港,并定居下来。整个江湖,在大陆泯灭,风吹云散,流向了香港,保存了一鳞半爪。这是一部哀婉而决绝的武侠悲歌,王家卫拍出了大格局。
《邪不压正》就缺少这种大格局,所谓的快意与放纵,不过是姜文的个人意气,并没有撑起影片的风骨。反而在“报师恩”与“民族矛盾”的夹缝中,左右不是,不知所以。
 那么,对民国风情的再现上呢?
那么,对民国风情的再现上呢?
同样的民国武侠片,同样是廖凡出演的《师父》,反倒是很好地展现了民国武林的基本风貌。再加上《箭士柳白猿》,两部片的导演恰恰都是徐浩峰。实际上,徐浩峰不喜欢“江湖”这个概念,他更喜欢的是“武林”这个词。的确,古时的“江湖”与“武林”是两个领域。“江湖”代表的由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辈组成的,是下里巴人的世界,不入流;而“武林”才是一个正经拳师镖师组成的中上层社会组成社会。今天的“江湖”概念,更多的是金庸古龙借用了古江湖的概念,虚拟出来一个的不存在的社会空间。姜文也不在意这个,而是把今天的江湖的概念直接放到了影片之中。徐浩峰的武林其实与姜文的江湖是一样的。但是,徐浩峰本着个人情怀,在尽最大努力地还原出了民国江湖的模样,讲出了当时的武人的生活面貌。只是,徐浩峰没有深入探讨在热兵器的冲击下,在机器工业的大发展下,传统武学的窘境问题,他只是努力去还原一个早已被架空了的社会。就像张北海在努力还原一个已经消失了的老北平。徐浩峰与张北海做得都不错,姜文则过于任性,他的着力点也不在于此。但是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天知道!
同样是徐浩峰的原著,陈凯歌的《道士下山》其实是有些被妖魔化了的影片,它的地位原应该更好一些。这部片,其实是借了一个小道士的眼光,串出了“世间情”(范伟段)与“江湖情”(张震段),讲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民国世界。这个视角也更接近与张北海《侠隐》的视角,用的主人公一个人传出了一个人情社会。可惜姜文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小说改的拧巴了。
 最后,来做比一下肖斯塔科维奇吧。
最后,来做比一下肖斯塔科维奇吧。
只看一遍《邪不压正》不过瘾,但是去了第二遍的话,反倒会看出更多的bug,也是尴尬。为了简单一点,还是借用一个人物来做比一下,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下这部片。这个人,就是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一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作曲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情绪,不去了解作曲家的话,只听作品,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活的非常率性非常豁达的人。但实际上,作品与人物之间,完全是割裂的。现实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其一生在斯大林极权暴政的恐怖阴影中战战兢兢地艰难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活着一生都在等待着随时到来的枪决。
肖斯塔科维奇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的作品充满了热情洋溢,就像他本人看起来的那样,看似放荡不羁,实则承受着巨大的不堪与苦痛。
 《邪不压正》中的李天然同样如此,看似他活的潇洒自如,放荡不羁,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而且在如何杀掉杀师仇人的抉择上,也身不由己,奈何不得。热情洋溢的压抑感,是解读《邪不压正》的密码。
《邪不压正》中的李天然同样如此,看似他活的潇洒自如,放荡不羁,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而且在如何杀掉杀师仇人的抉择上,也身不由己,奈何不得。热情洋溢的压抑感,是解读《邪不压正》的密码。
《邪不压正》中,姜文在开场配乐就用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号爵士组曲》,等于一开场就彰显给观众电影的基调了,优美、热烈奔放又不失庄严,旋律轻盈明快,就像电影里用的那些黑色幽默。然后,在欢快的旋律背后,再考虑肖斯塔科维奇被压迫、痛苦的一生,这样再结合到李天然的身上,对于这个人物形象的理解就有些豁然开朗了,哈姆雷特式性格也一下跃出银幕,扑面而来。
OK!写的好累,都是旁证,该说的都说完了,至于《邪不压正》究竟怎么会更好有些,还是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