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众生相
《我不是药神》是近期最火爆的一部电影了。有多火看数据:7月1日小规模点映,就以仅仅7.5%的排片拿下当日票房榜亚军,7月3日的点映更是一举夺冠。对影片的整体质量,豆瓣网友给出了平均9分的成绩,这可是近年来华语电影的最高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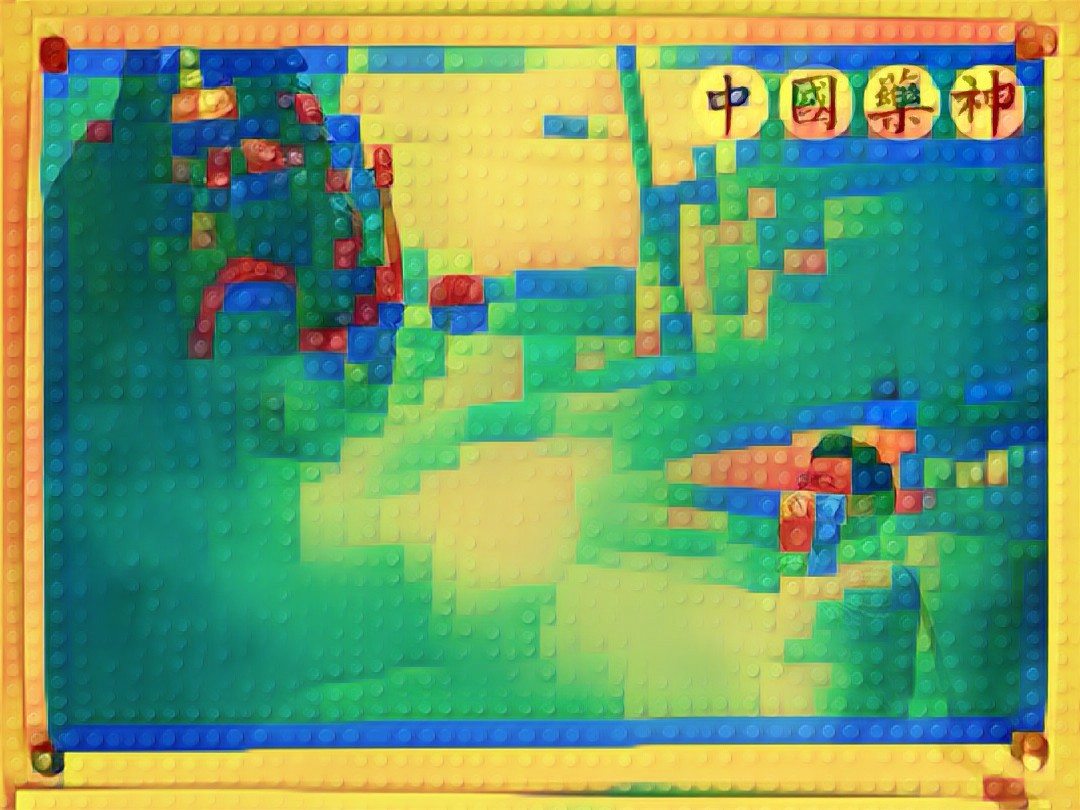 那么,它为什么能拿下口碑票房的双丰收?依我看,除了成熟的视听技巧,选题独到是首要原因。影片取材于当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
那么,它为什么能拿下口碑票房的双丰收?依我看,除了成熟的视听技巧,选题独到是首要原因。影片取材于当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
身患慢粒白血病的陆勇,因为吃不起昂贵的进口药,便冒险用便宜的印度仿制药替代治疗,也取得了相似的疗效。于是,他开始帮助没有渠道的病友从印度代购。由于印度仿制药涉及侵犯知识产权,无法在国内销售,这种代购的性质被视为走私,销售也定性为售卖假药。
虽然陆勇的行为帮助了很多生命垂危的患者,但还是被警方起诉并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1千多名慢粒白血病患者联名上书为陆勇求情,案件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关注,最终陆勇案以检方撤诉而宣告结束。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坎,而昂贵的医疗费用,则令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因病致穷是病患家庭的真实写照。因此,从片方选择这个题材开始,就注定了该片会成为引发全民关注和讨论的现象级作品。
影片中,徐峥扮演男一号程勇(现实中的陆勇),影片讲述了他从一个药贩子成长为“中国药神”的传奇故事。据说陆勇一开始对人物形象的改编并不赞同,因为他希望屏幕上的自己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但在观看成片后被其感动而与片方握手言和,接受了这个有瑕疵的“自己”。
 程勇的人生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是个loser,他经营着一家印度保健品小店,因为销售冷清经常付不起房租;为了孩子的监护权与妻子闹得不可开交;老父亲入院却交不起手术费,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到了老吕。
程勇的人生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是个loser,他经营着一家印度保健品小店,因为销售冷清经常付不起房租;为了孩子的监护权与妻子闹得不可开交;老父亲入院却交不起手术费,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到了老吕。
老吕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买不起昂贵的“格列宁”(现实中为格列卫,一种针对慢粒白血病的特效靶向药),他希望程勇帮助自己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由于印度没有药物的专利权保护,格列宁的仿制药价格仅为正版的几十分之一。程勇为了利益放手一搏,结果不仅成功的打通了格列宁的进货渠道,还出乎意料接触到当地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群体,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即使加价数倍,仍然供不应求。
程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也被当地的患者视作救世主,好像这成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但真正的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出现,使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全,并断然放弃了追随自己的朋友和无数等药救命的患者,将药品的经营权转给了更加贪心的张长林,撒手离去。我们无法指责程勇,因为他已经想到了自己的下场——因为走私和贩卖假药而锒铛入狱,他只是在自保。
真正触动程勇的是老吕的离世。张长林破坏了原有的渠道,老吕等病友再次陷入绝望,长期的断药使病情加速恶化。程勇此时已开设了自己的纺织工厂,生活无忧,但为了朋友他再次踏上印度之旅。可惜此时老吕的病情已到晚期,药物也无法控制了。
 老吕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而程勇开始重操旧业,他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但病友的期盼和良知的驱使使他觉醒,这一次程勇甚至用倒贴的价格卖药。在印度当局逐步取缔仿制药,国内病友将无药可吃的情况下,他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时间赛跑。他拿到了全国各地患者的名单,开始面向全国发药,每个月的补贴费用高达几十万,他也知道自己终将入狱,但义无反顾,何等悲壮!
老吕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而程勇开始重操旧业,他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但病友的期盼和良知的驱使使他觉醒,这一次程勇甚至用倒贴的价格卖药。在印度当局逐步取缔仿制药,国内病友将无药可吃的情况下,他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时间赛跑。他拿到了全国各地患者的名单,开始面向全国发药,每个月的补贴费用高达几十万,他也知道自己终将入狱,但义无反顾,何等悲壮!
影片描写程勇的内心转变用了非常隐喻的手法。程勇为了老吕再次回到印度的那个下午,当他走出药店时,突然间室外烟雾缭绕,面目狰狞的佛像一尊尊的从他眼前经过,诡异的音乐响起。导演用这样的视听语言表达了人物此时心境转变和精神的升华,这是程勇的决绝:就像之前在教堂调侃刘牧师一样,他的内心独白正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影片中唯一的反派是药企,药企的代表被简单的描述为唯利是图、漠视生命,这也是本片的一个瑕疵。
传统的癌症治疗无非手术和放化疗,但患者都苦不堪言,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靶向药物格列卫不仅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神药,还是间质瘤这种对放化疗不敏感的罕见癌症的特效药,给无数患者带去了希望。这小小的毫不起眼的药片,竟然将慢粒白血病人的5年生存率从原来的不到30%一下子提高到将近90%!这是人类对抗癌症的划时代胜利,格列卫被称为“杀死魔鬼的银色子弹”。 但是新药的研发时间长耗资巨大,上市后专利保护期也较短,药企要收回成本才能继续投入研发,从而形成正向循环。药品的定价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药企不应为老百姓看不起病背黑锅,而仿制药因为忽视了知识产权,也不具有推广实施的基础。当然,如何平衡医疗费用与患者的经济能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不能指望一部电影能提出有效方法。
在影片的末尾,程勇出狱时,小舅子曹警官告诉他格列宁已经被列入医保目录,格列宁的价格也有所降低,患者再不必购买仿制药,这是多方努力的结果,程勇应为之欣慰。
影片中的大众群体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同舟共济,彼此维护着人性的善良和温暖。黄毛抢了程勇的药,可他没有独享,分给了周围那些没有钱的病友;警察为了追查仿制药的源头,挨个询问时,没有一名患者为了自身脱罪而出卖朋友;老人对警察的倾述令人动容;曹警官为“药神”精神所感动,消极办案;就连伪院士张长林被捕后也够义气,宁可把罪责全部揽自己身上,也坚决不愿说出程勇的名字。
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在生死面前,人们都返璞归真,展现了人性至纯至真的一面。
《我不是潘金莲》大胆触碰上访题材,《芳华》讲述革命老兵的故事,《我不是药神》直面医疗改革,这些现实主义题材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阵清流。或许他们不够完美,在电影的技术上还有瑕疵,但这是中国电影人的勇敢担当,他们的一小步,可能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