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红薯
可能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引起的,每当我看到踏着秋色远道赶来的家人,解开粗布包裹,亮出还沾着点儿泥土的紫红番薯,便禁不住感慨万千。心头有些“他乡遇故知”的动情。张家口的番薯和玉米、黄糕、莜面一样,是一种生长期紧促的“急庄稼”。因为它全身是红皮儿的,人们又叫它红薯,红苕。
 大年刚刚过去,院子里向阳的角上,便铺起厚厚一方细碎半干的马粪和牛粪,粪窝里埋进年前精选出来的,大个儿的红薯作母体,起秧发苗。八月天里急忙忙收了玉米,锃光瓦亮的麦茬还遗留在田地里,镢头便从茬缝间掘出窝儿,墙角边密匝匝地簇拥起来的,二尺多高的薯苗,被剪成半尺长的茎节,一根根地埋进窝儿里,注进一碗清凉的井水,苗儿就在田野上落住根了。
大年刚刚过去,院子里向阳的角上,便铺起厚厚一方细碎半干的马粪和牛粪,粪窝里埋进年前精选出来的,大个儿的红薯作母体,起秧发苗。八月天里急忙忙收了玉米,锃光瓦亮的麦茬还遗留在田地里,镢头便从茬缝间掘出窝儿,墙角边密匝匝地簇拥起来的,二尺多高的薯苗,被剪成半尺长的茎节,一根根地埋进窝儿里,注进一碗清凉的井水,苗儿就在田野上落住根了。
当一行行麦茬,在来去飘忽的风雨里干霉腐烂、渐渐隐灭时,薯苗儿便悄悄地扯长绿蔓,巴掌形的叶儿开始覆盖地表,整个田垄由黄转绿,在悠扬秋风里转换的很快。仓颉造字真形象,将暑字略加变化,上方加盖个草字头便形迹近“薯”,似乎巧妙地概括出,这东西在暑天疯长的自然景象。薯叶封地太严,阳光漏不进去,叶下许多无名小草,硬是活活给捂死了。
 那贴地生长的蔓儿,容易扎下不定的根须。庄稼人担心它到处抽拔地气,随意生叶开花,分散了总根处的凝聚力。于是在它生长最旺势的时候,必须要翻一次蔓。爹蹲在田畦里,以那总根系为中心,一根根地抽拽那远远延伸的蔓儿。当把蔓儿全都拢在手里,爹猫起半腰,像绾起那一长缕美女乌发似的,把蔓儿绾成一团云鬓儿,便一撒手扔在地上。强行绾鬓只为收束住散漫的地气。
那贴地生长的蔓儿,容易扎下不定的根须。庄稼人担心它到处抽拔地气,随意生叶开花,分散了总根处的凝聚力。于是在它生长最旺势的时候,必须要翻一次蔓。爹蹲在田畦里,以那总根系为中心,一根根地抽拽那远远延伸的蔓儿。当把蔓儿全都拢在手里,爹猫起半腰,像绾起那一长缕美女乌发似的,把蔓儿绾成一团云鬓儿,便一撒手扔在地上。强行绾鬓只为收束住散漫的地气。
夜深了,万物成熟于空中,地表,而红薯则是亢奋于泥土之中,胖大结实的块头,硬是将沉重的黄土层拱起一个龟背,挤出错开指头宽的裂缝,土地大约被它挤疼了,疼得不由自主地咧开了嘴巴,薯儿那亮亮的红色,就从土缝儿里朝外窥探,透过地上半歪的绿鬓儿,窥视蓝天白云,窥视日月星辰,在湿润的土层里睁开的是惊讶的、生疏的眸子,从地缝儿里嘘出了陌生的鲜活气息。
 秋霜浇醉了枫叶那样,染红的大树梢柿子,同时也就催熟了土里的红薯。不经霜的红薯是不能吃的,勉强挖出来,如嚼硬木块而硌牙,如食青果而酸涩。一旦经霜,立即就若梨若枣,甜脆爽口。霜天万里,寒粉敷地,杀败了天下浩荡的绿色,封埋在黄土里的红薯,怎么一下就有味了呢?莫非是叶儿和蔓儿里,有什么秘密成分被严霜强逼入土?天候和地气对粮食果蔬的影响十分精确。
秋霜浇醉了枫叶那样,染红的大树梢柿子,同时也就催熟了土里的红薯。不经霜的红薯是不能吃的,勉强挖出来,如嚼硬木块而硌牙,如食青果而酸涩。一旦经霜,立即就若梨若枣,甜脆爽口。霜天万里,寒粉敷地,杀败了天下浩荡的绿色,封埋在黄土里的红薯,怎么一下就有味了呢?莫非是叶儿和蔓儿里,有什么秘密成分被严霜强逼入土?天候和地气对粮食果蔬的影响十分精确。
薯块的香味很像那刚刚炒熟出锅的板栗,青瓷小碟里有绿油油的凉拌蒿子杆儿。大碗擎起,大口吸溜,食之不足驱寒而耐饥,贪嘴过量也绝不伤脾胃,这在农家是既节俭又实惠的一流美食了。三十几户的小村庄正逢刚刚揭锅的早炊时间,甜美的香味,在黄叶飘坠的村巷里弥漫开来。有如秋江里一叶小舟似的,悠悠然荡入了半痴半醉、出神入化的境界,这就是农村最后一抹秋色。
 红薯生长期短,贮藏期却很长,而且搁置越久越甜脆。熟之于秋冬之交,贮存也忌热忌寒。在数九天里,放在地窖半中腰,或拐进去的地窨子里。地窨子位于封冻层,与地下水水平之间,在这里最恒温。那时我个小,一个人便踩在“嘎吱”作响的梯子上,秉烛上下,随吃随取,十分方便。若是保存得法,红薯可与翌年结下的新薯接住茬。生活上节省的人家,四季都会有鲜艳硕大的红薯,待宾客,赠亲朋。
红薯生长期短,贮藏期却很长,而且搁置越久越甜脆。熟之于秋冬之交,贮存也忌热忌寒。在数九天里,放在地窖半中腰,或拐进去的地窨子里。地窨子位于封冻层,与地下水水平之间,在这里最恒温。那时我个小,一个人便踩在“嘎吱”作响的梯子上,秉烛上下,随吃随取,十分方便。若是保存得法,红薯可与翌年结下的新薯接住茬。生活上节省的人家,四季都会有鲜艳硕大的红薯,待宾客,赠亲朋。
我听娘说,在她小时候粮食奇缺,许多粮站一度用四斤红薯,顶替过一斤粮食。个儿大的红薯一个就有四斤重,就算一天水米不进,吃一个红薯,又顶饿又解渴。困难时期的人们,就靠红薯延续着生命。红薯属于蔬菜和粮食之间的过渡,硬要取代主食的地位,不太可能。天地造物,最讲究搭配合理,运用得宜。不论丰年还是歉岁,将红薯视为口粮的搭配,那它绝对是上品。
不管多少,都是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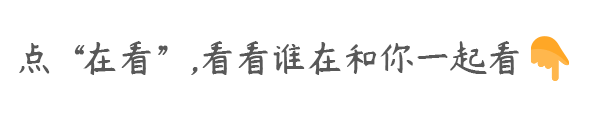 举报/反馈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