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 自由人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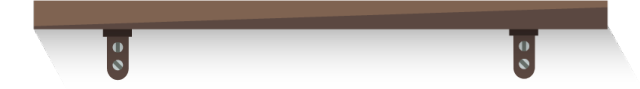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斋里,梅菲斯特向他讲起了上帝创造天地的历史——
“天使唱诗班没完没了的赞美已开始令他生厌;可是,他毕竟不是值得他们的赞美吗?他没有给他们带来永久的欢乐吗?获得一种不应得到的赞美,或者说,受到被他折磨的人的尊重,不是更有趣吗?他窃喜,并决定上演一出大戏。
炽热的星云毫无目标地在宇宙中旋转;经历了数不清的年代后,它终于开始成形,中心的云团甩开了行星,行星冷却了,沸腾的海水掀起巨浪又顷刻落下,燃烧的山脉重峦叠嶂,成片的炽热的雨水从黑暗的云团而来,淹没了光秃而又坚固的地壳。而后,生命的第一颗种子在海洋深处诞生了,它在能结果实的温暖地带快速成长为大片大片的森林;在这里,巨大的蕨类植物在潮湿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在繁殖着,厮打着,蚕食着,并消失着。随着剧情的展开,从这些怪物中,人诞生了;它能思想,知善恶,并痛苦地渴望崇拜。而且人发现,在这个疯狂的畸形的世界上,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在不可更改的死亡判决到来之前,所有的东西都不惜一切代价,去奋力抓住几个短暂的生命时刻。于是,人说,‘有一个我们只能领悟的目的,而且它是善的;因为我们必须崇拜某种东西,而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值得崇拜的。’人不再奋力争夺什么了,它断定上帝是想让人通过努力从混乱中产生和谐。当他遵循上帝从他的食肉猛兽的祖先那里传递过来的本能时,他称那些本能为罪,并请求上帝原谅他。但是,在他描绘出一种会让上帝平息愤怒的神圣蓝图前,他怀疑自己能否真正被原谅。因为看到现在的情况变坏了,他就让其变得更糟,以便将来的情况可以变得更好。他感谢上帝给予其力量,使其甚至能放弃曾经可能得到的欢乐。上帝微笑了;当他看见人类在克制和崇拜中变得完美时,便向天空发射了另一个大阳,这个太阳冲撞进了人的太阳;最后,一切都又回到了星云状态。”
“‘是的’,他轻声说道,‘这是一幕好戏;我要让它再次上演。’”

科学呈现给我们并让我们相信其存在的世界也大体如此,但甚至比这更无目的,更无意义。假如终究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从此以后必须找到一个家。人是诸多原因的产物,而这些原因并没有预见它们将要产生的结果;他的起源,他的成长,他的希望与恐惧,他的爱与信念,都只是原子偶然排列的结果:任何火,任何英雄行为,任何强度的思想与情感,都不能保护个体生命于来世;人类世世代代的所有劳动,所有的奉献,所有令人鼓舞的事物,人类天才所有如日中天的光辉,都注定要归寂于太阳系的大范围的毁灭之中;而且人类成就的整个殿堂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埋藏于宇宙毁灭后的残骸之下。所有这些,若不是完全无可辩驳的,也是近乎确定的,从而没有任何拒绝相信它们的哲学能有希望继续存在。从此以后,唯有在这些事实的框架内,唯有在牢固的不灭的绝望的基础上,人类的心灵家园才能安全地建立起来。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残酷的世界里,像人这样无力的生物如何能让其抱负依旧焕发光辉呢?神奇的是,在她长期而又多次匆匆穿越太空深处的循环往复中,全能而又盲目的大自然最终娩出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仍旧听命于她的统治,但天生能看,知善恶,并有能力判断其不会思考的母亲的所有作品。死亡,是父母控制的标志与图章;尽管免不了一死,但在其短暂的生命岁月中,人还是可以自由地去考察,去批评,去认识,并在想象中去创造。在他所熟悉的这个世界里,这种自由只属于他;而且,相比于统治其肉体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高傲之处就体现于此。
像我们一样,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野蛮人也会感受到自身的无力的压抑感。但因为他尊重这种力量胜过尊重其自己身上的一切,所以甘愿拜倒在自己的诸神面前,而不去研究那些神是否值得他崇拜。他长期忍受暴行与折磨,长期忍受侮辱等及以人献祭,并指望以此平息爱猜嫉的诸神;这是可悲的,也是非常可怕的。确实,颤抖的信仰者认为,当他已自愿献出最珍贵的东西时,它们的嗜血欲就一定会被平息,而且它们不会再有更多的要求。摩洛神教——此类教义通常可以被这样称呼——本质上就是奴隶的那种卑躬屈膝式的谦卑,奴隶甚至在内心深处也不敢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即他的主人不值得奉承。由于理想的独立性仍未被承认,大自然的力量可以自愿地被人崇拜,并受到一种无限的尊重,尽管它可以胡乱地将痛苦施加于人。
但逐渐地,随着道德变得更勇敢,理想世界的要求开始被人感觉到了;而且,崇拜,假如没有停止的话,那也一定被给予了另一类神而非野蛮人所创造的那些神。尽管人们感觉到了理想世界的要求,有些人仍会有意拒绝它们,因为他们还在强调单纯的自然力量是值得崇拜的。这就是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时反复灌输的态度:神的力量和知识得到了展示,但是神的美德却没有得到任何暗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的态度,他们把道德建立在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并认为生存下来的人一定是最有适应能力的人。但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对与人的道德感如此抵触的一种答案并不满意,他们将采纳那种我们习惯于认为其具有明确的宗教性质的立场,并认为通过某种隐秘的方式,事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实际上是和谐的。因而,人创造了全能的、尽善的上帝,创造了是与应当的神秘统一。

但事实世界毕竟不是善的,而且在使我们的判断服从于它时,有一种奴性成份必须清除,以净化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凡事都通过把人尽可能从非人的大自然的力量的专横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人的尊严,是明智的做法。当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的力量总体上是不好的时,具有善恶知识的人只是世界中的一个无助的原子;而且假如他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就将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应该崇拜大自然的力量,还是应该崇拜美德呢?我们的上帝应该存在并且是恶的,还是应该被看作我们自己的道德感的产物呢?
回答这个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会对我们的全部道德产生深远的影响。卡莱尔、尼采及军国主义的信条已使我们适应了对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个怀有敌意的宇宙时没有坚持自己的理想:它自身就是对恶的一种府伏性的屈从,或者说,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献祭于摩洛神。假如力量确实要得到尊重,那就不如让我们尊重那些拒绝错误的“事实识别”的人的力量,因为这种“事实识别”没有认识到事实时常是不好的。让我们承认,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中,有许多事情会通过其他方式变得更好;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我们确实在坚守且必须坚守的理想并未在物质领域得以实现。让我们保持对真的尊重,对美的尊重,对生活不允许我们获得的完美之理想的尊重,尽管在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会得到无意识的宇宙的认同。假如大自然的力量就像其看起来那样是邪恶的,那就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抵制它。
人的真正自由就体现于此:下决心只崇拜我们自己对美好事物的爱所创造的上帝,只尊重激发我们最佳时刻的洞见的天堂。在行为中,在欲望中,我们必须长期屈从于各种外部力量的专横,但在思想中,在抱负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摆脱了我们的同胞,我们摆脱了我们的身体无力地匍匐于其上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星球,甚至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摆脱了死亡的暴政,那么,让我们记住能使我们持久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的那种信念的能量,而在行为上,让我们往下走入事实世界,并始终保持那样一种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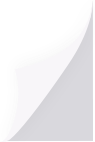
当事实与理想的对立首次变得充分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叛精神,即一种对诸神的极度憎恨的精神,对于维护自由似乎是必要的。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蔑视一个怀有敌意的宇宙,始终记住这个宇宙是恶的,始终积极主动地憎恨这种恶,不回避自然力量的伤害欲所能创造的痛苦,似乎是所有不肯在无法避免的东西面前低头的那些人的责任。但是,愤怒仍然是一种奴役,它强迫我们的思想专注于一个恶的世界;而且,在反叛由之产生的那种强度的欲望中,有一种明智的人必须加以克服的骄横。愤怒是我们的思想的屈从,但不是我们的欲望的屈从;智慧就是斯多葛派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在我们的欲望而非我们的思想的屈从中发现的。从我们的欲望的屈从中产生了顺从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的自由中产生了整个艺术与哲学世界以及对美的憧憬;而我们最终就是通过这种对美的憧憬并征服这个难以对付的世界的。但是,唯有对于自由的思考以及未背负热望重担的思想来说,对美的憧憬才是可能的;而且因此唯有当不再要求生活给予我们受制于时间变化的任何个人的善时,自由才会出现。
尽管自我克制的必要性证明了恶的存在,然而基督教在鼓吹它时已经显示出一种智慧,此种智慧超出普罗泰戈拉的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渴望得到的事物中,有一些尽管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真正美好的东西;然而另外一些,作为人们热切渴望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纯化的理想的一部分。被抛弃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这个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与未被抑制的热情所料想的相比,极少是错误的。而且,宗教信条,通过提供一个证明它绝非错误的理由,已成为纯化我们的希望的手段;这种净化是通过发现许多朴素的真理而做到的。
但在顺从中,有另外一种善的成份:即便真实的善,当它们不可获得时,我们也不应该自寻苦恼地期望得到。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要作出巨大的自我克制。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获得的;当人们用一种热情意志的全部力量去期待一个善的东西而又不可能获得时,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信的。然而,通过死亡,通过疾病,通过贫穷,或通过负责任的声音,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为我们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且不管我们所渴望的事物可以多么美好,命运可能仍然会禁止它们。当不幸来临时,我们的勇气,部分说来,就在于毫无怨言地忍受希望的毁灭,即把我们的思想从徒劳的遗憾中转移出来。对力量的这种程度的屈从,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正确的:它恰恰是通往智慧的门径。
但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自我克制来建立一个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殿堂。种种萦绕心头的殿堂预兆出现在想象的王国中,出现在音乐中,出现在建筑中,出现在无忧无虑的理性王国中,出现在抒情诗那金色晚霞的魅力中;在这些地方,美在照耀并发出夺目的光,它远离悲伤的边缘,远离对变化的恐惧,远离事实世界的失败与醒悟,在沉思这些事物时,天堂幻景将我们的心中自动形成,并立即提供一种判断我们未被周围世界的试金石;同时,它还提供一种灵感,而我们借助这种灵感,对任何能够用作这个神圣殿意的石料之物进行改造以使其适合我们的需要。

若不是因为有了那些罕见的生而无罪的灵魂,在我们能进入那殿堂之前,将有一个黑暗的洞穴要穿越。洞穴的门是绝望,而其地板则是用诸多被遗弃的希望的墓碑铺就的;在那里,自我必须消失:在那里,对未加抑制的欲望的热切与贪婪必须被消灭,因为唯有如此,灵魂才能从命运的帝国中解放出来。但是,走出洞穴后,自我克制的大门将再次通往智慧之光而经由这种光亮的辐射,一种新的洞见,一种新的欢乐,一种新的温情,向前照耀着,并让朝圣者的心感到愉悦。
一旦我们不再抱怨无力反叛,学会让自己听命于外部的命运统治,也学会认识非人的世界不值得我们的崇拜,我们最终就有可能改变并重塑这个无意识的宇宙,并在想象的熔炉里改造它,以至于一个闪耀着金光的新景象将取代旧的泥土偶像。在世界所有千变万化的事实中,比如在视觉形态的树木、山脉及云中,在人的生命的事件中,甚至在死亡的真正的无限影响力中,富有想象力的理想主义的洞见能够发现其自己的思想首次创造出来的美的倒影。通过这种方式,心灵断言它对无思想的自然力有一种微妙的支配力。它所处理的物质越邪恶,未经管束的欲望就越感到挫败,在引诱不情感的岩石放弃其隐藏的珍宝时它所取得的成就就越大,在迫使相反的力量壮大其成功场面时它所取得的胜利就越值得自豪。在所有艺术中,悲剧是最自豪、最成功的,因为它把其辉煌的城堡建立在敌国的最中心,建立在其最高山脉的最顶端。从其固若金汤的瞭望塔上看,他的军营和军火库,他的纵队和堡垒,全都暴露无遗。在城墙内,自由的生活在延续,与此同时,死亡、痛苦及绝望的兵团以及命运女神暴君的所有卑贱的指挥官,为那个无所畏惧的城市的自治居民提供新的美景。那些神圣的城墙是幸福的,那可眼观八方的高塔上的居住者更是幸福无比。荣誉属于那些勇敢的战士,他们历经数不清的战争岁月为我们保存了无价的自由遗产,并使不甘屈服者的家园未被渎圣的入侵者玷污。


但是,悲剧的美,确实只是使得一种时时处处以或多或少显而易见的形态呈现在生活中的性质变得可见了。在死亡的场景中,在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耐久中,在一种已然消逝的过去的不可改变中,都有一种神圣性,一种不可抑制的敬畏,一种对存在之辽阔、深沉及其无尽的神秘的感受:在那种感受中,受害者被一些悲伤的捆绑物束缚于世界中,就像为某种奇怪的痛苦的结合所束缚一样。在这些洞见时刻,我们失去了对短时欲望的所有热切,失去了为了不重要的目标而做的所有斗争和努力,失去了对琐碎之物的所有关心;从表面看,那些琐碎之物构成了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在被人的友好情谊的闪烁之光所照亮的狭窄木筏周围,我们看到了黑暗的海洋,并在其翻滚的波涛上颠簸了一小会儿,一阵令人冷得发抖的狂风,从广袤的外部夜空而来,突然中断了我们的避难。出现在不友好的力量中间的人的所有孤独,都集中在个体的灵魂上:这个灵魂必须单独去斗争,并使用其所能调度的勇气,来对抗一个毫不关心其希望与恐惧的宇宙所带来的全部重压。在与黑暗的力量的斗争中,胜利就在于真正受洗后归入光荣的英雄行列,真正进入人类存在的压倒一切的美。从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可怕相遇中,克制、智慧及仁慈诞生了;而随着它们的诞生,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让不可抗拒的力量进入灵魂最深处的圣殿,并感受它们、认识它们,就等于征服它们:这些不抗拒的力量,包括死亡、变化、过去的不可更改性,以及人在面对宇宙从空虚到空虚的盲目而又匆匆的运转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而我们则似乎是这些力量的傀儡。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过去具有如此神秘的力量。它静止而又无声的画面之美有如晚秋那着了魔的纯净;在那个时节,尽管树叶一吹就落,但它们仍在天空的衬托下散发出夺目的金色光辉。过去并不变化或斗争;像邓肯一样,经历了生命的一阵阵狂热之后,它安然睡着了。热切与贪婪,琐碎与无常,都逐渐消失了;曾经美丽而又永恒的东西,像夜晚的星星一样,在它们当中闪闪发光。对于配不上它的灵魂,它的美是不可忍受的;但对于已经征服了命运的灵魂,它是打开宗教之门的钥匙。
表而上看,相比于大自然的力量,人的生命只是一种不起眼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与死亡,因为它们比他在其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强大,也因为他的所有思想都是关于它们所吞噬的东西的。尽管它们是强大的,但以强大的方式去思考它们,并感受它们那种不带情感的壮观,则是更强大的,而且,这样的思想将使我们成为自由人;我们不再以东方式的屈从在不可避免的东西面前卑躬屈膝,但我们吸收了它,并使其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争取个人幸福而作的斗争,驱逐对短时欲望的所有热切之心,用激情拥抱永恒的事物——这就是解放 ,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而且,这种解放是通过对命运的沉思而达到的,因为命运自身已臣服于让一切都在时间的净化之火中得到了涤清的心灵。
通过所有纽带中最强的那一根即共同命运的纽带与自己的同胞联合起来,自由人发现一种新的憧憬始终与他相伴;这种憧憬使日常任务沐浴在爱的光辉中。人的生命是一次穿越黑夜的长征,被看不见的敌兵包围着,被疲倦与痛苦折磨着,最终走向一个极少有人能希望达到且无人会在那儿长时间逗留的目标。在行军途中,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他们为具有无穷威力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捕获。我们能够用来帮助他们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而且用以决定其幸福或痛苦的时间也是如此。愿我们把阳光洒在他们前进的小径上,通过同情的安慰减轻他们的悲伤,为他们提供永不让人疲劳的情感所具有的那种纯粹的欢乐,增强他们的正在减弱的勇气,并在他们感到绝望时反复向他们灌输信念。让我们不要用爱抱怨的天平来衡量他们的优点与缺点,而让我们只想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悲伤,他们的困难,或许还有他们的盲目;这些东西制造了他们的生活中的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在同一种黑暗中与我们一同受苦的人,是同一出悲剧中与我们相伴的人。此后,当他们的生命走向终结时,当他们的善行与恶行因为过去的不朽而成为永恒时,愿我们看到,他们之受苦,他们之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任何行为而导致的。但是,无论在何处,只要神圣的火花在他们的心中点燃,我们就要给他们以鼓励,给他们以同情,给他们以其中洋溢着很大勇气的豪言壮语。

人的生命是短暂而无力的;对他及其同类来说,那缓慢却又一定会到来的死亡将会是残酷的、黑暗的。无视善与恶,不顾所造成的毁灭,具有无限毁灭力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出现。对于人类来说,今天注定要失去最亲爱的人,而明天自己却又穿越黑暗的大门。然而,在灾难来临之前,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在于拥有高贵的思想:一种可以使所剩无几的来日变得有尊严的高贵思想:鄙弃命运女神的奴隶所拥有的那种懦弱的恐惧;崇拜用自己的双手所建立起来的圣坛;不对偶然性的帝国感到恐慌,让心灵从统治肉体生活的任性专制中解放出来;以一种令人自豪的方式蔑视种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力量忍心在短时间内让其知识与缺陷像一个疲倦而又顽强的阿特拉斯一样,单独地支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被他的理想所改变,尽管有种无意识的力量在践踏着它。
来源:[英]伯特兰·罗素 著,《神秘主义与逻辑及其他论文》,贾可春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第46-57页。
责任编辑 | 沈炎霞、龚发云
你可能还会喜欢
荐稿邮箱:lize_philosophy@126.com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丽泽哲学苑-